生活圆桌(99)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布丁 施武 李方 田七)
163新来的老年人
文 布丁 图 陈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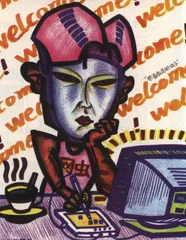
在网上能干什么呢?有家公司推出了e-busiuess的概念。在网上还能干什么呢?有本外国杂志说“e-life”。
既然能在网上生活,当然能在网上搞文学,于是就有名词叫“网络文学”。
这样的文学作品是什么样子呢?某女人,很无聊,夜间上网,进入聊天室,她把自己装扮成个男人,跟网上的一个小姑娘聊天,两人越聊越热乎,第二天,第三天,两个人都要聊上一阵儿,如你所料,那个网上的小姑娘不是小姑娘,而是个大男人。第四天,有个无聊男人来找无聊女人,见无聊女人挺有的聊,就要求跟那个小姑娘见面,“小姑娘”一看,自己装女人骗到了男人,很高兴,立刻答应见面。
故事往下就很俗套,装女人的男人找来个小姑娘,要她做替身,无聊女人也想看看自己骗来的“小姑娘”是什么样,就跟着无聊男人一起去赴约,至于以后怎么样,就看你喜欢喜剧呢还是愿意玩点儿伤感,随便编吧。
网络文学给性幻想狂提供了很多方便(文学就给性幻想狂提供过方便),当然,这不是说凡是网络文学都是性幻想者的作品。你的文学品位怎么样?可以去参加最近组织的一个网络文学大赛,有一位老作家,就担任评选委员会的工作,这位老作家曾经写过一本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至于说“163新来的老年人”不是指他,而是指“文学”这个缺乏生命力的老人。
说文学缺乏生命力,不是说文学没有用。网络需要一批神神叨叨的人去支撑,而搞文学的人大多神神叨叨,他们能把个不毛之地说成是世外桃源,“语言是存在的家,文学是语言的家,网络是文学的家”,像这样神神叨叨的话,只有搞过文学的人才能说得出来,才能说得出口。就像当过诗人的人才能挑战微软霸权一样。
网络是个好东西,从技术层面看,我们该做的事是让它更完美,让它更有用,而不是向它瞎抒情,你要是有点儿性幻想,搞搞文学就行了,没必要对网络施以意淫。
冬日黄昏与科学
施武
某人失恋了,愁眉苦脸的。大家一起吃饭时,见他蔫头耷脑地喝闷酒,我自然觉得他是受了伤的心情,直想说点什么宽慰的话,又觉得酸兮兮的不好开口,弄得我言不由衷绕来绕去地搅得气氛很不对头。
“其实,你完全误解了这种事”,甲可能见我太笨,说,“所有的失恋事件都与感情无关,你不要以为他的愁眉苦脸是因为伤心欲绝,那是一种困惑不解,是在知识上对那个姑娘之所以离开他的原因感到好奇,是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在作祟。所以,这不是感情事件”。还说这是地道的心理学。
此话一出,在我的失声大笑中,那个失恋的家伙居然连声称是,一副茅塞顿开的样儿。
这事已经过去了,再见到失恋的人时,他倒是不愁眉苦脸了,可是却真的换了一张困惑不解的堕落嘴脸。其实,甲说的话根本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逻辑,当不得真,难道那呆子竟连隔壁阿二都不如,我到宁愿认为他这番装腔作势是“隔壁阿二不曾偷”的自欺欺人。
不管那算不算地道的心理学,我都抵制。这是对科学的一种矛盾心情,科学是帮了我们不少忙,可是它一来帮感情的忙,我就打心眼里讨厌。甲这样使用科学态度,换了另一种情况,比如人没了感情,美国的生物科学家会给你一粒小药丸,你就能孝敬父母、热爱妻小、珍重朋友,过了些日子当你的感情用完了,没关系,再吃一粒小药丸。原理他们是有的,我不想知道,总之是科学的。
我害怕这样的科学,这种对抗来源于冬日黄昏的街景。在夏天,满街的人都好象犹犹豫豫不知道去哪儿的无聊,我也懒得做饭,老是去个餐馆瞎吃。一到冬天,黄昏时,所有的路人都在赶路去他所要去的地方,那地方一定有一盏灯火,一定有人,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很基本的故事。这时的感觉很踏实,虽然得费事做饭。所以,尽管我在给女儿织毛衣的时候,人家给我算账说,除了买毛线的钱,我用那个时间来工作能值好几件毛衣,我还是想织。这些都是被科学发展挤压得退缩到一个角落的生活浪漫,我不想都交给科学。在这种科学计算的面前我选择忠实于不科学的自我感觉,爱对不对。
男人思考,女人发呆
文 李方
我家门口新开一间茶馆,幌子上写“下棋打牌,聊天发呆”。这是我头一次看见有人正儿八经把发呆当个项目,心里很欢喜。
一般认为发呆是一种很没有追求的表现,“饱了犯困,饿了发呆”,这种人该着下岗,但女人除外。似乎很多女人不讳言自己是发呆爱好者,有的女明星索性把它填写在“个人爱好”一栏里。发呆是女人的专利。若是男人,应该叫“思考”。反正都是没事儿坐那儿两眼发直胡思乱想,处于感官完全与外界不交流的状态。但是思考多高级呀,发呆则显得脑容量有点不够。在这件事情上男女不太平等。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是男人的自嘲。女人呢,可能她们一发呆,发笑的没准是上帝的前妻。上帝是个男的,而思考是男人的游戏,他们不会有理解发呆的智商。我就没有这种智商,因此,当我的前女友跟我说“你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发会儿呆吗”,我完全不能理解其实她正准备跟我吹灯。一个女诗人把发呆描写得相当冠冕堂皇:爱人,今夜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想想心事。我读着一激灵,心想她可比我前女友还虚伪,没准那位“爱人”还蒙在鼓里呢。
当然男人里边也有职业发呆者,比如和尚,但他们有更好听的名目,像坐忘啦,入定啦,什么的。
不公平主要在于,我们认定发呆就是游手好闲。主流观念,不论是30年前还是现在,都对闲着深恶痛绝,要求人们必须雄赳赳气昂昂地工作和生活,仿佛一放松,不但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就连“休闲”,也得安排得对得起钱包对得起肚皮对得起服务员小姐,才算有那么点意思。发呆不但有病,而且有罪,因为发呆扩大不了内需拉动不了消费,排不了国家的忧解不了政府的难。发呆何益?
我们这是怎么啦?
因此,当我看见那间茶馆经营“发呆”的时候,忍不住心里欢喜,比看见谁在报纸上爽了一把还欢喜。总算有人为“呆民”们做件实事了。不像有些同行,拿“茶艺”把你宰得跟生鱼片似的,还跟你说那叫高雅。
但茶馆仍不能免雅,在忙着发呆的茶客里边,我就见过这么一桌男女,泡着30块钱一壶的茶,续了40多遍水,谈着几千万的融资项目,煞有介事,声震屋瓦。烦得我开始满墙找字儿,看看“莫谈国事”的旁边,有没有“莫谈生意”。
大舌头知本家
文 田七 图 陈希
“知识经济”一词的发明权属于美国,但我想“知本家”的归属肯定是中国人,由三位知名的IT批评家著作的《知本家风暴》是“知本家”概念诞生的宣言。
人民大学杨杜解释说“知识经济”的游戏规则是:知识雇佣资本。这两年我们谈的特别多的风险投资中那个拿着钱的风险投资者不是最重要的,讲发财故事的人最最重要,那是一种智能。“知本家”的意思是拥有知识的人终于翻身作主,扬眉吐气了一回。虽然联想集团的杨元庆说,对中国这个产业经济比重还很大的国家来说,也许连知识经济的门槛都还没有迈进。
围绕《知本家风暴》一书召开了一个“知本家风暴和风暴中的知本家”讨论会,一批雄心勃勃的IT核心批评家和周边记者表达了参与知识经济的强烈愿望。虽然“知本家”理论创立者目前获得的更多是思维的快乐。但是“安于清贫,沉湎理论”早不是IT理论界的态度了,“知本家”理论也面临一个“经济化”、“商品化”的问题。
既然做网站的是知本家,掌握IT舆论权威的专家、记者是不是知本家呢?他们什么时候能开着“宝马”车来讨论“知本家”的问题?
联想汉卡发明人倪光南和四通打字机发明人王缉志被认为是老一代的知本家,如今都在联想和四通公司外“闲赋”,他们是吃了亏的知本家还是掉了队的知本家呢?王缉志说,打个比方就像你下象棋,如果有一天下棋的时候(对方)把一个棋子给偷了,这就不符合游戏规则。这样输就不输在你,而输在对方没有照游戏规则下。
新生代的知本家态度不一样。
搜狐公司张朝阳说他搞的公司与房地产公司、餐馆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知识经济、高科技不是仅属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东西。网易公司的丁磊更诚恳:我不是知本家,我是一个工程师。金山公司雷军说:经常有某个公司的经理或什么人挟款潜逃,公司合伙人常常因钱产生龃龉的时候,公司对资金的忠诚、对员工的忠诚、对客户的忠诚显得尤其重要。说“知本”的时候,是不是更要注意“资本”呢。
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王小东,他说:我们IT业的产品走向世界了吗?我们现在走向世界的产品都是打工妹的产品。IT的产品正好反过来了,老看着中国这块市场,老喊着打击盗版,老想挣中国这块钱,真没出息。印度就能打出去,我们打不出去却在这边称自己是英雄,你什么英雄呢?你没有能力把我带出去,想来想去就挣我们打工妹的那点辛苦钱,再把这一部分转到你的腰包里去,这算什么英雄呢?
最有趣的声音说:“知本家”?听起来像一个大舌头的东北人说“资本家”,“知”、“资”不分。
(本栏编辑: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