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技术:钢铁战士是这样炼成的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胡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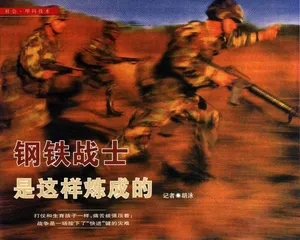
虚构成了非虚构
非虚构成了虚构
我参加军训的时候,我们的班长常挂嘴边的一个词是“钢铁战士”。这位班长觉得他很了解战争,因为他看过那么多部战争片。
他可以用一颗抛出的手榴弹炸毁坦克,他可以跑得比子弹还快。没有人能够杀死他,因为战争片就是这么表现的。只有斯皮尔伯格似乎不这么想。
《拯救大兵瑞恩》打破了影坛的战争神话。此片一出,没有哪个男孩还能够再坐在电影院里幻想战争是一桩光荣之举,在战场上牺牲是一件体面而充满尊严感的事情(在充分实现人生的价值之后幸福地长眠)。在这部电影中,士兵不是从容赴死,而是血肉横飞,求生无门。
刻画钢铁战士的影片太多了,以至于《拯救大兵瑞恩》成了珍品。
公正地说,战争题材片近年越来越具有写实风格—已经远远超越了在男女主角脸上抹几块黑、衣服上划几道口的阶段。我们见识了《血战台儿庄》的惨烈和《晚钟》的沉重。我们从《猎鹿人》、《野战排》中领略到战争是一场玩笑,一局赌博,而不是一种洗礼和升华。
半个世纪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因为害怕影响士气,坚持要好莱坞保证战场的整齐与清洁。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虚构作品都被虚构了。《拯救大兵瑞恩》当然也是一部虚构作品,而且免不了好莱坞的俗套—许多场景安排都出于编剧塑造人物的需要。核心人物被汤姆·汉克斯演来得心应手,甚至片尾还高扬了“做一个好人”的道德主题。可是,在表现战争的真相、战场的残酷方面,斯皮尔伯格毫不含糊。当我在影院里观看此片时,头25分钟之后,我非常想叫放映员暂停,因为我的脑袋似乎也被斯皮尔伯格的排枪打飞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皮尔伯格的大作虽然是虚构的,却比海湾战争的实况录像显得真实得多。这些录像常常由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亲自解说,你在他指点之下看到的是一场干净的战争。不论是美军士兵还是伊拉克平民都没有伤亡。友军的火力未伤及任何人,每一枚“爱国者”导弹都成功地拦截了每一枚“飞毛腿”导弹—“成功率为百分之百”,施将军在战争开始后两周说。
其实“爱国者”的拦截成功率仅为10%,而被友军打死的人占美军阵亡总数的25%。伊拉克平民被无辜击中,伊拉克士兵惨遭活埋,而阵亡的148名美军士兵的死法,大部分都不宜上电视。所有这一切都未在录像带中出现,也很少受到新闻曝光。五角大楼控制了媒体,录像带时代的战争沾染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诗情。非虚构作品成了虚构。
斯皮尔伯格把《拯救大兵瑞恩》称为反战片。它是反战的,但它没有质疑人们总得打一些不得不打的仗这一前提。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就是不得不打仗,这种局面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不得不打的,汤姆·汉克斯饰演的上尉是那种不得不照上司命令行事的人。没有人发表演说,也没有人高谈民主与和平,每人心里想的都是回家。与此同时,仗不得不打。
打仗和生育孩子一样,痛苦被强压着。德国巴伐利亚一座教堂的墙上,刻满了数不清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男人的名单—再往下看,是更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死者的名字,就好像此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们怎么能够代代这样打下去,上一次战争中的副官变成这一次战争中的将军?难道他们患了遗忘症?
有时人们的确忘记了过去。看看印、巴的核弹竞赛。看看最近结束的“沙漠之狐”行动,美国人在要求重放施瓦茨科普夫的录像。
斯皮尔伯格在提醒世人。战争是一场按下了“快进”键的灾难,它屠杀的不是好人,也不是坏蛋,而是那些不走运的人。
从军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冒险
无庸置疑,杀人技术取得了飞速的进步,战争的屠杀规模日益缩小。你大可以说海湾战争中美国不过损失了148名士兵,和过去的大战在人员伤亡上简直无法相提并论。这或许是因为海湾战争是一场高技术战争,有人把它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信息战”。
在海湾战争中,远程操作武器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扮演了重要的战地角色。天空中布满了无人驾驶飞行器,这些远程操作的、没有飞行员的飞机可以跟踪伊拉克部队、探测导弹发射点、查明雷区,以及测算炸弹的摧毁力。美军空战82分部使用这种飞机在基地周围巡逻,德国扫雷兵也动用了可进行远程操作的巡逻艇。将来,持武器之手会长得更长:1987年,美国《军事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预测,“从生理学的意义上,士兵可以在需要时真的变成3英里高、20英里宽……我们希望能创造出变样的未来战士,他们在机器人或遥控飞机的护卫下出发迎敌”。威廉·米切尔对此评论说:“哥利亚(意即巨人)被重新创造了。”
就像手臂长的拳击手与手臂较短的对手相比更不容易被击中下巴一样,具有远程操作武器装备的“电子士兵”可以安全地守在后方,而避免了前线作战的危险。指挥官们非常乐意看到这种局面出现,但请注意,他们的考虑更多地不是出自减少士兵伤亡,而是提高战争效率。曼纽埃尔·德兰达在《智能机器时代的战争》一书中写道:
“几个世纪以来,军事指挥官们一直在梦想从战场中剔除人类因素。当腓特烈大帝在18世纪集结军队时,他不具备把人的躯体完全从战斗空间中消除的技术,但他确实做到了消除人的意志。他将自己的军队变成了一台运转良好、像钟表一样精确的机器,其组成部件是机器人般的士兵。腓特烈的战士没有任何个人主观意志可言。”
如果士兵能够自做主张,临阵脱逃或投降,他们就处于将军的控制之外;而将军们却希望控制一切。这样看来,一队能够英勇作战的机器人战士最合将军之意,他们能够控制下属的每一个行动,如同腓特烈利用畏惧控制其军队一样。一个机器人战士永远不会对上司的命令提出质疑,而这正是军训时的第一要求。
这样的战争会赋予将军以绝对的控制权,好处是人的生命会在机器人战场上得到保存。拥有最好技术和最多机器人的一方将取得胜利。谁的科技更发达、谁的财力更雄厚,谁就将称霸天下。在过去的战争中,牺牲人力常常是一种便宜得多的做法,今天依然如此。未来的将军们恐怕不得不把这一点计入战争方程式。
然而,程序员们能够准确地预测到一个机器人士兵在战场上遇见的各种情况吗?如果计算机系统连系鞋带这样的简单动作都应付不来(尽管它在棋盘上击败了世界冠军),又怎能期望他们在复杂的战场上进退自如、发挥作用呢?阿道夫·冯·柴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名德军上尉,在《战役领袖》中写道:每个士兵都应该清楚,战争如万花筒一般充满变化、突发事件和混乱局面。战场上的问题是无法用数学公式或预先设定的规则加以解决的。”
因此,战斗机器人面临的技术挑战是巨大的,但计算机控制的武器则可行得多。“爱国者”导弹的名噪一时,显示了计算机控制的武器已成为现代战争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它可靠吗?谁来就开火作出决定—人还是计算机?责任落在谁的肩头?
无论腓特烈及其追随者们想得多么美妙,人的因素不可能从战场中完全剔除。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职业军人特性已开始过时。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政治军事学高级研究员约瑟夫·科林斯在1998年秋季号的《华盛顿季刊》上哀叹,颂扬集体、自我牺牲、克己奉公和不怕吃苦受伤的勇气等美德在美军中已越来越不被看重。
信息时代对军事文化和组织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影响:第一,许多军人的职业专长越来越与技术有关,明天的军队将需要比今天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军人。从军将更像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冒险。越来越多的男女军人对作为传统军人美德的精髓的尚武精神将感到陌生。第二,在今天流动性很大的就业市场上,对等级分明的大型机构的忠诚将成为非同寻常的特质,从而使年轻的士兵更难形成同所在军种之间的牢固联系。
军事文化—武装部队中有主流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哲学思想、惯常做法和传统—正受到冲击,对战争的认识也在改变。在此背景下,斯皮尔伯格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拯救大兵瑞恩》让你尽可能真实地感受战争。假如说你还能在影院的座位上坐牢的话—没有像战场上某些人那样逃之夭夭—那也许是因为你意识到,在其他人真枪实弹地拼斗的情况下,你至少能做一件事:观看他们怎样战胜磨难。 海湾战争军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