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车站》:新现实主义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卞智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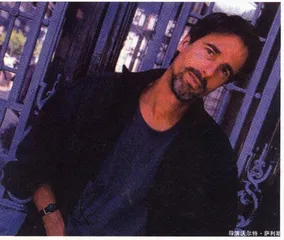
导演沃尔特·萨利斯
在全球范围内,低成本的艺术片总能 找到影院放映,但一般也就那么几个地方。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它们是一种奢侈品,它们是思考再思考的结果,它们不提供娱乐和感动。
需要有人为此辩解。《中央车站》在1998年2月的柏林电影节上荣获金熊奖,到年底在美国发行。它的合作制片人之一,美国传奇式的制片人亚瑟·考恩(其影片五次获得奥斯卡奖,最好的一部是《善恶分明的花园》)说:“这不是一部‘小众’电影,应该把它归入主流电影。它是一个知识分子做的,但它的情感可以打动每一位普通人。把它列为一部从国外来的、有趣的、奇异的艺术片,这无疑是发行商的自杀行为。”
这是一个擦皮鞋的小男孩和一个在里约热内卢机场代人写信的老太太的故事。两人认识不久,小男孩的母亲去世了,老太太极不情愿地收养了他,使他避开了充满危险的街头生活。但在接下来帮小男孩寻找父亲的旅途中,两个角色越米越接近一个富有人性和热情的巴西。
导演沃尔特·萨利斯同时是一位纪录片工作者,他对镜头的把握使观众很轻易地成为这趟旅程中亲密的伙伴。影片开始时,多拉和约瑟在火车站相遇,周围充满了各种各样、极度混杂的声音,然而画面却是单色的。随着二人越来越远离那危险的、自我幽闭的里约热内卢,影片的视觉世界便越来越开放。萨利斯说:“这是为了把多拉正在经历的事情传达给观众。她生活在一个狭窄封闭的现实空间,但是当小男孩决定寻找自己的父亲时,一块完全不同的凋色板进来了,黄色,红色,蓝色,绿色。音响越来越清晰,镜头换了——你得到一个宽广的、富有透视感的视野。”直到最后,当你被情感的力量彻底压倒时,也许你的视野会变得模糊起来。
这位生于巴西、长于法国的导演试图在影片中找到一种“内在的、有机的生活”。他做纪录片的经验帮助了他。为了寻找约瑟的扮演者,他走遍巴西,先后找了1500个小男孩试镜。直到有一天,当他坐在里约热内卢机场的候机厅内时,一个10岁的小男孩拉拉他的袖子,问他要零钱。这个小孩身上混杂着街头顽童的狡猾和萨利斯所要寻求的天真无邪。“影片不断被这种我们预想不到的机遇塑造着。”萨利斯说。
萨利斯声明自己愿意和现实保持一种紧凑的关系。他们在一个住有朝圣者的小村拍了10天戏之后,收拾行囊,和那些在戏中担任临时演员的村民们道别。渐渐地,全村人都出来为他们送行。有人开始唱影片中的一首歌曲,那是请求朝圣者保护的一首歌。很快,全村的人都加入进来,萨利斯和剧组成员热泪盈眶。“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正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制作电影,”萨利斯说,“没有这部电影就不会看到这样一种人际关系。”
萨利斯和亚瑟·考恩的说法其实完全一致:诉求于观众的情感,而不仅仅是以技巧打动批评家。萨利斯把《中央车站》称作“新现实主义”作品,这在目前低成本、小制作的严肃电影中,的确形成了一种风气。它们要以情动人,但和老套的“催泪剂”绝无瓜葛;不排斥技巧和编造,但绝不脱离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而且它们和纪录片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点姻亲关系——在镜头风格上,更重要的是在观念和意识上——这使得影片真实、富有人文精神和现实意义。这一点最能对比出中国影片的普遍弱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一个纪录片运动,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我们对电影的理解常常会缺少很重要的一块内容。 影视新现实主义电影中央车站剧情片法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