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世纪:21世纪国际问题的中心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罗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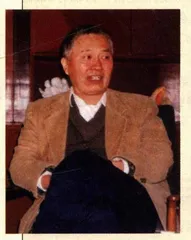
陈小鲁简历
197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武官系。曾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武官处官员、国防副武官,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研究员,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研究员等职务,现任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世纪末,我们听到许多下世纪全球如何发展的观点。你曾提到的,美国重要的经济学作者莱斯特·瑟罗(Lester C.Thurow)的观点确实十分引人注目,他说:“资本主义的永恒真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实际收入增加——似乎正在消失。新技术和新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正在把经济体制推入新的方向。它们正在制造新的赛局和新的规则……”这种说法,是否确实预示着下一个世纪将要发生的事情会与本世纪有本质的不同?作为一个国际战略问题专家,你的看法如何?
陈:冷战结束之前,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主题和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是战争与革命,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产生了两大对立的阵营。虽然这些事件的最终动机是经济,但是都掩盖在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外衣之下,是以它们的婢女的身份出现。而21世纪的经济问题将抛弃一切外衣,以女皇的姿态直接登上国际舞台。
冷战之后,世界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世界经济一体化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自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变化和冲突无不和其紧密相连。
1989年以后,原来分属两个阵营的两个市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其中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那时,我们已经改革开放了10年,较早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市场,苏联东欧瓦解,只是使我们的进入加速。当然,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有许多保留,比如金融这一块,但东欧和苏联的经济制度则在一夜之间与国际市场完全接轨。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市场中的所有资源,在一夜之间挤进了另一个市场。这不能不给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市场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原苏联是世界上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它的石油进入世界市场后,世界油价大跌。俄罗斯反而被自己的石油生产所累。这次俄国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就是世界原油价格大跌,俄国的出口外汇大幅度减少,国际收支不能平衡,最后只好宣布国债暂不支付。炒家也好,西方投资者也好,统统陷在里面。美国的对冲基金在东南亚和韩国大赚了一笔之后,在俄国以及后来在拉美都受到重创。不仅如此,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使得经济危机很快扩展,美国和西方各国不得不采取措施救自己。有分析家认为,世界经济现在已经从崩溃的边缘退回来了。今后10年、20年,世界还将处在类似的、由全球经济一体化引起的冲突、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调整和磨合之中。
自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各国发生的经济衰退,实际上是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二战以后,所有想发财的国家都想赚美国人的钱,欧洲人靠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实现了战后恢复。日本通过发两次战争财,而且美国有意使它成为其远东战略基地,把日本的大企业和骨干力量保存和发展起来。到了亚洲的四小龙、四小虎,更是人人都搞出口导向。中国90年代以来对美贸易大幅度增长,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冲突和变化会接连不断。
罗:这种动荡和变化的原因除了你所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外,还有什么?如果说本世纪下半叶各国发展都靠赚美国人的钱,这种情况会不会在下世纪有根本的改观?也就是说,富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给世界经济提供的巨大市场,最终会使这种动荡和冲突减弱吗?
陈: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互为因果。19世纪末,马克思曾把世界上的主要问题归结为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我看来,这个矛盾今天仍然存在,只不过可以换个说法,即生产全球化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全球一体化经济与以各国政府为主的分散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亚洲金融危机中这一矛盾的表现非常充分,而在未来几十年内,这种矛盾将主导国际事务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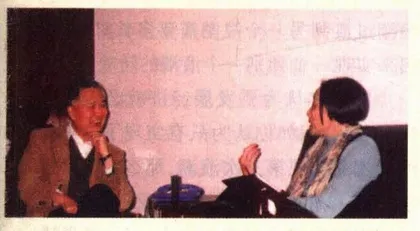
美国人现在最不满意的是日本人老不扩大内需。我们国家前几年出口增长每年达到15%到20%,对GIP增长的贡献将近一半。今年没有这么高了,10月份还出现负增长。所以,我国政府也提出扩大内需,鼓励老百性消费,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的新手段。这个过程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是需要的,对于发达国家同样重要。他们对于发展中国家,不能像对冲基金那样,老是一种掠夺和投机,捞一把就走。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兔子不吃窝边草”。现在全球市场就那么大,哪儿哪儿都成了窝边草。不让草长,只吃,窝边草也吃干净了,怎么行?有人说现在已经进入了减息时代。为什么西方各国都减息?就是要刺激经济,发展内需。西方各国压日本,他也不得不拿出23万亿日元刺激经济的计划。中国前几年老百姓穷,我们急着让老百姓致富,现在富起来,就得让老百姓花钱。否则,经济怎么发展?我们开玩笑,大家都像雷锋,一双袜子穿10年,经济没法发展。
需要调整和磨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手段的进步不仅导致了经济形态变化,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导致了意识形态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在自身发展中已经欠账太多,这些国家的政府今后不能太自私,太妄自尊大。比如美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初,他说风凉话,问题大了,扩展到全亚洲,他也不愿意给钱,等真的冲到他头上,冲到拉美他的后院,而且对冲基金出问题了,他才发现他不能袖手旁观,他只好带头减息。作为一个西方国家政府,一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育市场,创造需求。资本输出也要注重长线投资,要注重保护环境,要给所有的人提供谋生手段。
中国政府也开始注意类似问题。长江中上游天然林木禁伐就是一例,如果不保护环境和资源,建再大的电站和工厂都没有用。但是施行禁伐,政府要拿钱出来,要使上游靠伐木为生的人们有饭吃,让他们变伐树为种树,还要使那个地区的经济不致因禁伐而受到打击。做这种维持全球生态平衡的事情要花钱,有时要花许多钱,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么多钱,发达国家就得帮助他们。
要知道,世界已经变得非常狭小,全球经济已经变得牵一发而动全身,倚身其上的全球政治因此变成了一盘棋。当下一个世纪来临的时候,当全球经济一体化继续在世界各国引发多种冲突和动荡、多种危机和阵痛的时候,最需要各国政治家、企业家、银行家和学者们的,是非同寻常的远见卓识,是充分交流和协商,是妥协基础上的联合行动。需要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尤其是冷战思维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包括某些陈旧的国家主权观念。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这方面的努力。最明显的例子是明年1月1日实行的欧元。参与国都撤销了自己的中央银行,而将这些事情交给现在的荷兰人将来的法国人去做。如果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不放弃原有主权概念中的一些东西,这个事情显然做不成。当然也有国家,比如英国就没有进入。这种事,由于欧洲长期的历史渊源,比较容易做到。但是大家都由此看到一种可能性。毫无疑问,没有这种理想,资源日益紧迫,环境日益恶化,政治冲突日益激烈的世界将一筹莫展。
罗: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又是一个原计划经济国家。虽然改革开放20年使我们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在这个世纪交替的时刻,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国家战略选择?
陈:中国有句老话,叫“多难兴邦”,是说必须有压力。一般说来,所有国家政府的主要成员都是保守的,他们是现存体制产生的领导人,当体制改变的时候,都会降低他们继续领导下去的可能行。这种时候,突发危急的事件才能迫使他们做出痛苦的选择和改变。中国如果没有“文革”这样的大灾难,导致国民经济空前的停滞和倒退,就不会有改革开放20年后的形势。面对世纪交替的动荡变化时期,中国的正确选择是认清形势,即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放弃冷战思维和狭隘国家观念,逐步改革不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管理制度,包括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搬。总之,是顺势而为,而且是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全方位参与。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通病是腐败。中国政府也在重视这个问题,最近媒体上披露的粮食系统亏空2100亿,直接亏损800亿,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还不是拿去盖房子,买汽车了!而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的通病是霸道和贪婪。近年来,国际资本四处出击,在世界各地赚取利润,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偏就短视,认为热钱好用。此外,世界财富极度不平衡是对人类安全最大的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最近有一个讲话,说到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消费了86%的商品和劳务,而20%的穷人,只消费了1.3%。
莱斯特·瑟罗真正有趣的观点是他借用生物学间断性平衡的概念来描述未来的技术、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在旧环境被打破以后,原来处于强势的生物物种,由于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衰弱或灭绝。在这个作者看来,20世纪苏联瓦解了,东欧解体了,所以资本主义胜利了。但是在间段性平衡的时代,技术发展使得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发生本质的变化,资本主义是否还能够保持强势,却还是一个问题。
经过人类一个世纪的努力,科学技术使得生产力走上了新的台阶。今天,我们虽然还要面对马克思一个世纪前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不过我想,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最终会排除一切障碍,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全球经济管理体制。 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