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技术·金融危机·无摩擦的资本主义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胡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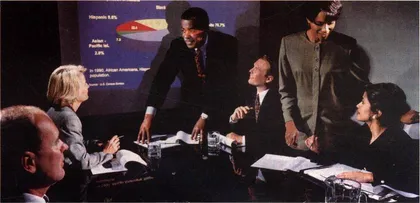
市场每天都在投票
1576年,当头脑敏锐的法国律师让·博丹在他的《共和六书》中首次提出“主权”概念时,他将对金钱、信用和财政政策的控制,列为主权国家的三大支柱之一。但这一支柱从未稳固过。到19世纪末期,在金融市场上居统治地位的不是由政府铸造的硬币或印制的纸币,而是由迅速增长的私营商业银行所创造的信用。为抵消这一势力,主权国家纷纷成立中央银行。及至美国1912年建立联邦储备制度时,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中央银行,用以控制商业银行及其信用。但其实金本位制的存在严格限制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布雷顿森林会议所产生的金汇兑本位制虽然较金本位制有了很大的灵活性,不过仍未能赋予单个国家完全的金融和财政主权。直到1973年,尼克松宣布美元浮动时,上述的主权才得以体现。
有趣的是,浮动汇率实际上给各个国家的政府套上了新的、更沉重的枷锁。它造成了外汇市场的激烈波动,随之产生了大量的“世界金钱”。这些钱不存在于哪个国家中,而是存在于全球市场上。它不是由投资、生产、消费或贸易这样的经济活动所创造出来的,而完全是由外汇交易产生的。金钱的传统定义不外乎衡量标准、储藏价值或交换工具,但这一世界金钱与这些定义毫不相干。与其说它是真实的,不如说它是虚拟的。
但虚拟金钱的力量却再真实不过了。世界金钱的数量太庞大了,它在一国货币市场上的一进一出,比起金融、贸易或投资流动的影响要大得多。一天之中,虚拟金钱的交易量就足以支持整个世界一年的贸易和投资。由于它不为任何经济功能服务,它具有彻底的流动性,而且也正因为如此,它根本不遵循任何经济逻辑或理性。它变化多端,谣言或是突发事件都可能使它“四下逃窜”。
亚洲最近的金融危机就是虚拟金钱一手导演的一出闹剧。起初发生在泰国的挤兑风潮迅速发展成为影响整个世界的金融恶疾。到1997年12月,这出闹剧达到了高潮:一向骄傲的韩国人俯首向国际货币从金组织称臣,乞求6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而韩国的经济在世界上列第11位,甚至就在几个月前,东亚还被舆论目为“奇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第一次出面充当救世主的角色。1995年它拿出500亿美元援助墨西哥,1997年早些时候,又分别向泰国和印度尼四亚倾资170亿美元和230亿美元。这些钱加在一起达1000亿美元,好像有点吓人,不过,猜猜美国最大的3家养老基金的经理们手中M着多少钱?5000亿美元!他们拥有常人无法想象的金融权力—政府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都没有这样的权力。这些金融巨头可以在瞬间之内给任何国家造成经济地震。
生活在主权国家里的人们是否意识到,权力已经发生了转移?它已经离开了政治的大本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政客们仍然在为权力苦苦相搏,但经历了马拉松式的选举上台以后,他们才发现,面对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强大势力,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小得可怜。1996年,一家知名的法国周刊发表了一份题为《全球最有影响的50人》的报告,其中没有一位国家领袖、政府首脑或国会议员入围。与此同时,另一家周刊用突出篇幅报道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比尔·盖茨,他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信息市场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大有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而比尔·盖茨和其他这个世界的新统治者们永远也不会把自己置于选举过程中,或者说,他们参加的是另外一场选举。用今大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之一、金融家乔治·索罗斯的话说:“市场每天都在投票,它们迫使政府采取不得人心但是必不可少的措施。是市场扮演了国家的角色。”新的统治势力凭借的不是核弹头,而是一连串诱人的字眼如自山交换,私有化,货币主义,竞争性,生产率,等等等等。它的口号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一切权力归于市场!”
在所有市场件,金融市场尤其堪称典范,所有的活动都以它为重心。全球化经济成为一国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最终裁决者。而没有新的信息技术,事情本来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
信息本位
信息技术为现代社会的神经中枢—金融市场带来了一场真正的“大爆炸”。它将资本转移的成本几乎降低为零。交易者只需在键盘上轻敲几下,就可以把数以亿计的金钱山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信息的交换成为即刻的,一天24小时从不间断,从地球的一端飞临另一端。全球主要的股票交易所彼此连接、轮流运转,就像一台永动机一样不知疲倦。也许可以说是实时的数据改变了全球经济。它产生了一种比金本位还要严苛的“信息本位”。在某位国家领导人宣布一项政策后几分钟,市场对这一政策的判断就会反映在汇价和股价上。
不妨看一看亚洲金融危机是如何上演的。先是日本官员因害怕日元下跌而放出风来要提高利率,在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外汇投机者中引起恐慌,他们害怕自己的大宗投资受到威胁,因为这些投资是建立在汇率稳定的基础上的。当他们赶忙抛出当地货币时,恐慌感进一步9延。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外国大公司也惊慌失措,争相把当地货币兑换成美元。最终,当地公司也加入了这场大逃亡。随着每个人都挤向出口,泰国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及其他地区货币就难逃噩运了。所有的人都由船的一边跑到了另一边,带来的只能是—船的倾覆。
市场似乎像一个瞎子一样行事。遵循着巫术般的规律,金融市场玩出了新花样,而且越玩越玄妙—我指的是衍生品交易和期货,它们如此复杂,如此多变,没有几位专家能够真正掌握它们。但是这种把戏却吸引了一批年轻的市场信徒:在世界各地,有上千名教育过度、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整日手持电话,双眼紧盯电子屏幕,如痴如醉地向大脑中输入数据和指令。他们是市场的雇员,他们阐释着新的经济理性。这一理性永远正确,其他的理性—特别是社会的或人文的理性—在它面前都必须让位。他们中的佼佼者还能是谁呢?不外是利森、井口俊英、滨中泰男,等等。不是每个人都欣赏这样一些年轻人。法国前总理巴尔就站出来大声疾呼:“不能再听任一群30来岁不负责任的赚钱机器为我们指点江山了!”
摩擦的消失?
另一位说“不”者是亚洲价值的著名卫道士、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他与索罗斯就究竟谁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他指责索罗斯的金融投机类似“强暴”,坚称这种投机活动是“不必要的、无成效的、非道德的”,应该为法律所禁止。
“你不能把这简单地归结为市场力量就算完了。你必须明白,当市场力量与上百万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时,你就得去调查你所说的市场力量到底意味着什么?”马哈蒂尔说。
资本主义以自己的发展史证明了它是一台高效的发明、生产和流通机器。但是其方式—由利润驱动一切—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所总结的,是一种“创造性毁灭”。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均衡概念上的,但在实践中,它的特性却推动它走向不平衡。知名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将此称为“现代保守主义的困境”。保守主义者所崇拜的不加限制的市场恰好破坏了他们所公开鼓吹的价值—稳定、道德、家庭社区、工作、纪律以及延迟的享受。市场辐射一切的能力,贪婪,短期行为,低级趣味的大行其道,欺诈,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态,所有这些都与保守主义的理想相冲突。
甚至出名的资本家都为过度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后果感到震惊。如果说最会赚钱的人也最懂得资本主义的话,没有一个人比索罗斯更熟知当代资本主义。“虽然我在金融市场上发了大财,现在我却对资本主义的完全放任自流感到害怕。市场价值已经蔓延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正在对我们的开放而民主的社会造成威胁。”索罗斯写道:“对个人私利的无限制的追求,会导致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平等和动荡。”
大资本家比尔·盖茨曾经鼓吹说,电脑网络将造就“没有摩擦的资本主义”,因为它为有效的市场和企业提供了机会。他没有索罗斯那份睿智,会想到没有摩擦的资本主义有一天可能破坏资本主义自己的未来。信息革命不是别的,正是创造性毁灭的典范。这种创造性的一个目标是全球化经济,毁灭性的一个没有料到的对象是主权国家。计算机将不受约束的市场变成了一辆庞大战车,碾过一切疆土,削弱了国家的税收和管制权力,破坏了一国利率和汇率的职能,不仅在一国之内,而且在国家之间扩大了贫富差距,降低了劳动标准,损害了环境,使国家无法自己把握其经济命运。计算机对任何人都不负责任,造成了一个没有世界性实体的世界经济。电脑化空间超乎国家控制之外,没有一家权力机构能够对之实行跨国管理。
没有摩擦也许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美好。摩擦保持了经济和文化的地域性,令人们珍惜自己的声誉。摩擦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质感,使大家得以彼此认识。摩擦在远与近之间设定了一条模糊的界线,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加以穿越(埃瑟·戴森语)。
在21世纪,我们还得面对这样那样的摩擦。 金融风暴金融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