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异星人
作者:娜斯(文 / 娜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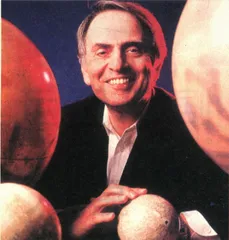
天文学家、科学作家卡尔·萨冈
过去的这一个世纪,是人类的科技文明飞速发展、登上月球、进入太空的时代,科幻作品就在这时代应运而生。尤其是电影这一媒介,使得人类对外太空的幻想维妙维肖地呈现在大银幕,逐渐构造出一套新的神话传说系统,反映着人类的热望,也反映着人类的恐惧。乔治·卢卡斯的帝国三部曲开了星际传说的先河,斯皮尔伯格的《ET外星人》《第三类接触》是人类与外星接触的美丽童话,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奥德赛》则是世纪初兴起的现代风格与未来幻想结合出的一次迷离梦幻(在此片放映的吸毒成风的60年代,可以想象它给予人的那种灵魂出窍式的体验,事实上,据说那时很多年轻人就是要边吸大麻边看这部电影的)。
有没有异星人的问题是科学问题,至于人类对异星人的幻想和塑造,则是文化的一种反映了。回顾20世纪,太空幻想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题目,因为这是我们时代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标志之一。从世纪初的“荒原”隐喻,到世纪末的太空漫步。或许,有一天,地球真的也变成我们曾经抛弃在身后的荒芜村庄中的一个。或许,多少年后,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宇宙村,未来人看到我们今天的神话,也会像我们今天看荷马史诗一样,分不清真假,却纪录着我们的心灵?
而在所谓后现代的今天,科幻话题又有了新层次:太空奇迹已经不像世纪中期时那样令人激动、惊异不已,神话已为游戏取代——对于电脑环境中长大的一代,星际大战的确是可以在面前小小屏幕中为自己操纵的游戏(卖座片《独立日》的很多镜头都让人感到是这种电子游戏被搬上大银幕而已)。在《独立日》片中扮飞行英雄的威尔·史密斯说,在这年头,你的太空人越是露出别着话筒(意指不过是在演戏)越能招徕观众。太空的意念已经不像刚一开始时那样令我们感到彻底的神秘和敬畏了——或者,敬畏不敬畏也没有用?反正,似乎在电脑上,我们才能过瘾地“搅动宇宙”,所以今天的科幻作品,带有更多玩世不恭的色彩。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科技越进步,我们却越难回答了。
记得小时候赶上科技热,看过卡尔·萨冈的书。他以天文学家之身兼科学作家之职,对于人类和人类置身其中的宇宙的关系作了不少既理性又有趣的观察洞见。卡尔·萨冈是获普利策奖的作家,今年又推出了新著《鬼怪作祟的世界:科学作为黑暗中的一盏蜡烛》,讨论我们为何对飞碟和异星人的问题迷恋不已。他的科幻惊险小说《联络》(《Contact》)也正由《阿甘正传》的导演搬上银幕,由女星朱迪·福斯特扮演其中的无线电天文学家,与天外生命取得了联系,等等。因为影视作品中天外来客横飞的缘故吧,卡尔·萨冈又是公认的宇宙学作家,所以《首映》杂志对他进行采访,讨论美国人的“异星人情结”。
首映:到底是什么使得UFO和外星人使我们如此着迷?
萨冈:外星生命的问题是可想见的最深切的哲学和科学问题之一,洞见着我们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不仅如此,它还是一面往往是以相当宗教的方式反映我们的希望和恐惧的绝佳的镜子。
首映:你对那些坚持自己被外星人绑架过的人如何看?
萨冈:它一部分是一种幻觉,一种生动的梦。我们之中25%的人都会有幻觉——这是人的一种特性。还有一种不幸的证据是有些心理治疗家坚持他们的病人的回忆与这些心理治疗家脑中先存的一种理论相符。这很能说明问题。电影和电视也在人们讲述的外星人绑架故事都大同小异上起着作用。外星绑架狂热者的根据之一是:“如果没有真的发生过,”每个人都看过相同的电影,相同的杂志封面,相同的电视节目。
首映:你经常被找去作电影顾问吗?
萨冈:这要看我的坏脾气了。如果我正在坏脾气发作的时候,那我就不会被请去当顾问了(笑)。如果我能保持一段时间不批评电影,那么我就会被请去。
首映:你有什么特别喜爱的科幻电影吗?
萨冈:有。《2001,太空奥德赛》,以及限于其时代的《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
首映:需要什么可以说服你太空中确实有什么?
萨冈:如果我们从另一文明接到一种无线电信息,有内容,明显发自极远的地方,那么我会被说服。如果我们发现后天绝对不可假冒的造物,那么我会被说服。我是准备好被说服的……想象空军知道敌对外星人的存在而保持这一机密令我莞尔,因为现在是削减空军经费的时代,外星人入侵对他们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因为那样他们就可以要求更多的拨款。
首映:回顾过去,异星人还代表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冷战敌方到宗教形象。这些是如何随着时代而变化的?
萨冈:一般来说,要看当时正发生的新闻。典型的例子是奥逊·威尔斯广播火星人正在入侵的《世界之战》(发生于无线电广播兴盛的30年代,听众信以为真,造成了不小的恐慌,是名导演奥逊·威尔斯事业早期的出名事件——译者)。此时希特勒正开始侵略欧洲各国。可以想见人们当时对此的沮丧。在其他国情紧张的时候,如冷战时代,人们也倾向于视异星人不宽容,不友善。与此同时,也有一种感觉就是应该有人站出来,把我们从这种潜在的致命危机中解救出来。这于是又给另一种相反的异星人提供了机会。
首映:你是指好的异星人,比如E.T.——一个善良、可爱、甜蜜的生命。
萨冈:啊,当然了,E.T.是一个婴儿。我们不知道成年的它们是怎样的。
这里说到异星人幻想映射了人类自身文化心理的部分,令我产生了一些联想。中国人基本上不存在一个现代科幻文化的传统,但中国人有武侠世界,作为冷战的另一方,也有我们的“洋鬼子”和“东方大救星”,跟科幻作品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与“他们”,随着时间场所的不同而变化着,被塑造着。然而,从更远的一个角度看,“我们”原来就是“他们”,“他们”原来就是“我们”。在异星人没有真正被发现之前,我们幻想的不论是神是鬼,都产生于我们自身,都可能是我们自己。如果想到我们自身也在他人的幻想中被虚构和误解着,我们可能会更好地读懂我们自己同样筑造过或正在筑造的神话。或者更容易与这样或那样的“异星人”进行沟通、理解,分享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