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法:挥出第一刀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胡泳 梁云程 摄影·董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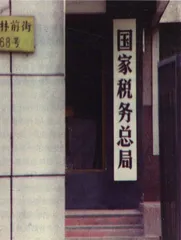
高工坐上审判席
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判厅内,聚满了首都3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和旁听人员,采访和旁听全国首例偷逃个人所得税案的一审判决。云集法庭的记者和群众想必都已意识到,这个案件非同一般,蕴含着太多的象征意义。当天,中央电视台在播发这条法制新闻时,不知为何竟用了“盛况空前”来形容当时的情景。
上午10时,法院开庭,身材微胖的被告双手戴着手铐,由法警押入法庭。整个案件也许正因为被告的身份才显得复杂多歧——入坐被告席的,是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工程爆破公司高级工程师魏宝林。
54岁的魏宝林生活中的最佳位置本不该在这里。他1965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采矿系,后分配到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采矿部从事科研工作,1987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1993年4月调入本院工程爆破公司。他曾参加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研究,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参与符山无底柱采矿法攻关,获全国科技大奖。1994年5月,其姓名和事迹还被编入《当代中国科学家与发明家大辞典》。
在高悬的国徽下,审判长宣读了此案的刑事判决书。法院确认,被告魏宝林于1992年10月至1993年3月,以湖南省冷水江市振兴矿业新技术开发部的名义,分别与湖南、广东、浙江等省的矿务局、水泥厂、铜矿签订研制推广水泥药卷锚杆技术服务协议,并从中收取技术服务费10.5万元。被告得到该款后,未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亦没有扣缴义务人和单位为其代扣代缴上述收入的税款,其偷逃个人收入调节税61278.8元,占应纳税款的100%。
法院认为,被告采取隐匿个人收入的手段、不进行纳税申报而偷逃税款的行为违反了国家税收法规,扰乱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已构成偷税罪。根据被告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1条,判处被告有期徒刑2年,罚款50000元,并须补交全额所偷税款。
颁布已久的税法终于向偷逃“个调税”者开刀问罪了,不过这“第一刀”砍得如此之狠,令所有人震惊。众多旁听者在听到审判结果后无不向被告投去惋惜的目光。
魏宝林的辩护人、北京谢朝华律师事务所的张波律师在结案后说,1994年国家税务机构与地方税务机构分设以来,国内首起由司法部门公开审理判处的个人偷税案发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身上,无论对于魏本人还是他的家庭都是个悲剧。
“魏案”的来龙去脉
1995年6月,西城区地税局和西城区检察院联合成立的京城第一家税务检察室开业不久,就接到一封群众署名举报,反映魏宝林几年来私自在外搞技术服务,单位不知其收入情况,魏本人也未纳过税。
接到举报后,检察室的人员立即展开了调查。他们了解到,魏宝林曾于1992年7月在湖南省冷水江市成立了一个“振兴矿业新技术开发部”,名义上的法人代表是当地一个名叫刘美华的开理发馆的农村女孩,而实际上则是由魏一人负责。检察人员于是决定赴冷水江摸清情况。行前,他们不无顾虑:魏宝林搞的是一种抗塌方的起加固作用的技术服务,全称为“水泥药卷锚杆技术”,这种技术以前在有色金属开采中使用不普遍,不少矿山新近使用此技术后都取得了较好的效益,那么那些受惠于魏宝林技术的厂矿会配合检察官的侦查工作吗?可在调查中,使检察官们感到意外的是,调查对象的不合作是另外一层意义上的。知情者一听说是来调查魏宝林的,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想到的都是:是不是魏工的收入有什么问题?意即收入合不合法,而没有人想到收入是合法的,不合法的是没有交纳个人所得税。
其时正值湖南摄氏40度的高温天气,检察人员住在冷水江市,每天往返奔波于冷水江市与锡矿山矿务局之间,在一座已有道道裂缝的危楼中查看矿山的陈年帐簿,终于从中查出了魏宝林偷税的蛛丝马迹。
8月初,检察官返回北京,初步认定魏宝林偷税金额已达立案标准,于是决定立案。8月31日,魏宝林被逮捕。
紧接着,检察人员又南下广东省凡口铅锌矿水泥厂、江苏省吴县铜矿、浙江亚东铜业集团公司建德铜矿等单位,逐步查清了魏宝森偷税的犯罪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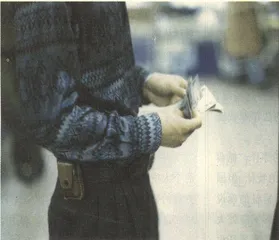
1992年10月24日,魏宝林以振兴开发部的名义与广东凡口铅锌矿水泥厂签订了“水泥药卷锚杆技术转让协议”,厂方共付55000元至魏的个人帐户上。由于振兴开发部没有进行税务登记,魏宝林无法给厂方开出发票平帐,于是他用“冷水江市技术贸易专用发票”盖上振兴开发部的财务专用章和“魏密森”的名章给厂方平帐。魏宝林在被捕后承认,“魏密林”是他的别名,为的是避免签约人与受款人为同一人。
1992年10月22日,魏宝林与江苏吴县铜矿签订了“水泥药卷销固剂技术转让协议”。吴县铜矿同样以“经费”名义,先后分三笔支付魏55000元。其中第一笔15000元直接汇到了魏的个人帐户上,但魏一直未能返回发票给吴县铜矿平帐。为了能开出名正言顺的发票,对其余两笔钱共计40000元,魏采取了另外的方式:1993年2月20日,魏通过吴县铜矿矿长的介绍,接受吴县铜矿下属的“吴县矿业技术开发公司”的聘书,担任挂职人员。魏与开发公司商定,开发公司允许魏以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约,可借用帐户、代开发票,条件是收取10%的管理费。这样,40000元的款项,开发公司扣下4000元管理费,其余归魏所有。
此外,魏宝林还为浙江建德铜矿提供过技术服务,所收取的服务费也未申报纳税。
在侦查期间,魏宝林始终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他一直坚持两点:第一,他是科技人员,业余才搞项目;第二,他用自己的技术服务于社会,收入来源正常,不存在什么违法问题。如果说他一点也不懂应该交税,那倒也冤枉了他。他在与挂靠单位签约、订协议及与服务单位签订协议时,其中都有工商行政、税收、财务等非技术性事务都由对方负责的条款,但他未交一分钱个人所得税却是不容辩驳的事实。
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在掌握了魏宝林偷税的确凿证据后,遂于1995年11月向法院提起公诉。辩护律师张波提出了3条辩护意见:1.魏宝林部分行为不构成偷税罪,主要是与魏签订协议的、单位又与其他单位签了协议,税款理应由这些单位代付,魏所得收入没有交税属漏税行为;2.魏是初犯,身为高级工程师和科研项目带头人曾获多项奖励,宜予从轻处理;3.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执行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法,税率大致定在20%-30%之间,较此前的个人收入调节税60%,有了较大幅度降低,因此应根据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和刑法有关规定,对魏宝林定罪量刑。
西城区法院认为,起诉书中认定的13万多元中的6万多元属于偷税,检察院指控被告偷税罪成立,其余7万多元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被告律师的第一点意见予以采纳,其他辩护意见根据不足,理由不当,不予采纳。
于是魏宝林成为我国第一个因偷逃个人所得税而锒铛入狱的人。
“首案”为何不审“星”?
中国公众对于个人逃税事件并不陌生。数年之前的毛阿敏税案、刘晓庆税案都曾轰动一时。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法院公开审理、舆论曝光的首例个人偷税案的被告,不是“公众人物”或商界大亨,而是一个事业上有所建树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是偶然的吗?
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魏宝林以自己的学识和劳动挣了10万元人民币,却因隐匿不报,不仅连罚带补11万元,还招致两年牢狱之灾。仅仅在两年多前,在新税法实施前夕,当时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鑫还公开对外界承认,中国仅有极少一部分人富得达到了课税标准;现在,不仅有了税,有了税法,还有了因偷税而坐牢的人。
相信很多人对此的感觉就像刘晓庆对当年税案的追忆中所描述的一样:“漏税偷税……长这么大从没有听说过这些新名词,怎么还这么复杂。什么事情都是如此,要不就不存在,要一存在就到顶,春天一过就是冬天,脱了单衣就穿皮袄,没有过渡、认识阶段。”
魏宝林显然还未能及时意识到季节的变换。张波说,魏宝林一案暴露出知识分子重技术轻法律的倾向。他说,知识分子的知识面较宽,更应该积极学法守法。特别是知识分子近年来经济活动趋于频繁,因而更应努力做好自身的“法制建设”。就具体案情而言,他认为,由于法院是不告不理,因此,这起“首案”的被告是位知识分子,可视为巧合。
税务部门的有关官员则强调,这一案件的意义不在于谁成为被告,而在于它显示了税务机关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纳税管理和打击偷逃个人所得税的决心,并希望借此起到震慑作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高级知识分子也不能因其对社会贡献大而逃避法律惩处。对于偷逃个人所得税的行为,将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不管遇到谁,都将一视同仁。
但此案判决后的相当一部分社会舆论却是从另外的角度理解“公平”的。海田在《中华工商时报》上撰文评论说,“公平、公正、公开永远是法制健全的标志。魏某应该受到处罚,其他偷逃个税的行为也应当受到处理,检控魏某的部门是否该解释一下,何以某些‘星’的偷逃至今没有受到公诉?”“选择这个案例向社会表示,偷逃个税系严重罪行,似乎并不典型。”
“首案”不审“星”,这是很多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结。北京丰台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一位女工程师说:“有人唱一首歌就轻而易举得到十几万元,而知识分子出一项成果,少则一两年,多则数十年,伤神费心,含辛茹苦,最终也不过几千元报酬,可因为是一次性收入,也必须照章纳税,这难道是公平的吗?”魏宝林在矿冶研究总院的一位同事王女士也说,歌星、影星偷漏税在报上频频曝光,没有看到谁被判刑,逃税之后往往是没发现就算了,发现了再补上。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头脑挣钱,为社会创造了许多财富,许多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也无暇去挣这些钱,因而,王女士疑问道,对魏的法律制裁能起到多大的警示作用呢?
当然,就像有专家指出的那样,“抓典型”的方式决不是法制国家的特征。但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管理司的官员的确说过,这次魏案的依法处理,是国家查处大案要案、用以改进和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突破口,期望唤起依法纳税的全民意识。无奈的是,许多人从中嗅出的味道却是“柿子专拣软的捏”。在一家合资公司工作的甄先生就直言不讳地说,“不公平在所难免,所以就有所谓‘有办法、有背景’的人和‘没办法、没背景’的人之分。这位魏工显然属于后者。”
这样的反应似乎有违此案审结的初衷。然而,不管怎样,魏案抛出的重磅炸弹还是震动了社会各阶层的耳膜与神经。此前,纳税在众多百姓心目当中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好象那只是一些特殊的高收入者的事情,与己无干;而现在,那些平时仅满足于关注自己的收入是否合法的人开始意识到,合法的收入还必须有一个合法的支出,那就是交纳个人所得税。
也许,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第一案”的被告是一个背景简单的高级工程师,人们才不会有异样的感觉。魏案直截了当地亮出了一个人们早就应该明白但却一直懵懂的命题: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这一命题明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6条。
要相信群众的觉悟
实际上,对于人们所称放过“硕鼠”只抓“小耗子”的微词,税务部门是有所解释的:据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介绍,去年共征收32亿个人所得税,99%是通过各单位实行代扣代缴制度完成的,而对于流动性大的演职人员、个体工商户等高收入阶层,税务机关却难以掌握其实际收入情况,个人所得税的依法征收也难以理想。况且,我国的现金交易体制很多不走帐,极难从帐面上反映出问题。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市去年个人所得税中,有80%以上是工资薪金项目的所得税收,工薪阶层成了上缴大户,相反那些真正的大税源却漏网了。
国家税务总局披露,每年至少有50%的个人所得税流失。为解决这个问题,各方面的建议和说法很多,诸如:改革完善税法,使税收体制尽可能做到统一、实用,公民的纳税环境更为简单方便;建立配套的金融体制,像国外一样,每人分配一个终生不变的税号;加强征管,制定相应措施来收税,而不仅仅是让人们去交税;加大纳税义务及其相关法律的宣传力度;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和舆论工具维护税法的严肃性,查处一批大案要案,等等。
据悉,年内将修改调整个人所得税法。现行的分项、分次、按月的计税办法是否会改为全年一次性分项综合计税办法,是否实行双向申报制度即代扣义务人及纳税义务人均要向税务部门申报个人所得税,所得额的扣除部分是否会增加等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作出调整决定的出发点之一,是增强纳税人主动纳税的意识。个人所得税法颁布16年来,我国普遍采取的是纳税人所在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致使公民纳税意识淡薄,甚至认为个人所得税与其无干,虽然他们也每年都交。双向申报制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但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却也不是有了一本好“经”可念就万事大吉那么简单。
税收是国家或地方政府为行使其职能而向国民或居民征收的资金,这是国家法律所规定的。税收不仅成为国家或地方政府用以维护公共利益的资金,还能够根据累进所得税或遗产税等对收入和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并通过减税和增税手段来调整景气。
可以说,如学者所言,一个不是以税收方式来实现公共利益的国家,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大量存在着偷税现象的国家,不可能有效地实现和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只有征税而纳税人对税收的使用没有监督的权力,也就等于摧毁了税收本身的合法性。
很多人也许都知道,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是英国议会数次强行对美洲殖民地征税。根据用鲜血换来的英国议会制度,并正如洛克所说,财产是和生命及自由分不开的;若没有得到本人同意或他所选举的代表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别人的财产。殖民地人民在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因此,这些征税措施剥夺了殖民地人民的“最基本的英国人的权利。”弗吉尼亚因此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宣布只有该议会才拥有“对本殖民地居民……课加赋税的唯一排他性权力。”但英国仍然一意孤行,最终导致十三州在1776年的第二次大陆会议上发表《独立宣言》,其中明白无误地指出,宣布独立是基于英王侵犯了美国人民的自由,而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
读史可知,税收于国于民都绝非小事。这也就是魏案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案件本身的原因所在。
个人所得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进一步增强税收的透明度,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使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决定个人所得税用于何处,也许,这才是增加公民纳税意识的关键所在。还是那句老话:要相信群众的觉悟。 纳税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