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转会
作者:苗炜转会已成比赛的前哨战
1995年甲A联赛开战之前,各支球队都对这一赛季的目标作出了自己的规划,12支球队呈现一种有意思的状态:上海、广东、大连、广州、北京、辽宁这6支球队都把目标定在前3名,其中更有4支队伍明确表示要夺冠军;而山东、四川、天津、八一、延边、青岛这6支球队都以保级为前提。12支球队一半是高姿态,一半是低调门,高姿态的一半除辽宁之外都有较为强大的财力支援:而低调门的一半大都是财不够大,气就不够粗。
甲A联赛在绿茵场外的确存在着另一番较量,那就是金钱。
上海申花夺得95年甲A联赛冠军,申花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表示,申花的投入也是各俱乐部中最多的。申花队的钱大多花在奖金上。主场胜北京国安后,申花队队员在奖金之外各得到一部“大哥大”;主场击败济南泰山而提前两周登上冠军宝座后,申花获该场比赛奖金18万元,冠军奖金100万元。
由于各俱乐部对投入资金的具体数额大都守口如瓶,因此很难推断资金投入与球队战绩会有怎样的关系。但广东宏远队在购买球员的投资上所表现出的努力和信念却是有目共睹的。1995年初,宏远以100万元购得黎兵、马明宇,而后又引进两名葡萄牙籍外援阿曼杜和丹尼奥,这两名外援的月薪在2000美元左右。这样引进球员之后,广东宏远成为地方色彩较淡的一支球队,受到江西、湖南、湖北的相当一部分球迷的拥戴,同时也成为拥有国脚数量最多的所谓“豪华球队”。
等到95年度联赛战罢,宏远队主教练陈奕明表示,如果当初能把宏远想买的人都买到,那他还是要跟徐根宝掰掰手腕。陈奕明耿耿于怀的便是济南泰山的3员大将宿茂臻、邢锐、唐晓程未能转会宏远。
就像许多粗俗的小品一样,扮演精明而略显霸道的商人总要拖一副广东腔。在中国足协公布的1996年球员转会的第一批名单中,唯一的一名国脚韩金铭仍是打算投奔宏远队。而由于广州松日队、深圳队升入甲A,广东拥有了4支甲A球队,这使得其他各支球队都有了一层对广东集团购买力的担忧,这种担忧更多是来自球迷。
1995年甲A联赛尚未战罢,北京就风传深圳队开价80万购买高峰,不少球迷表示,如果高峰要转会,那他们将发起募捐挽留高峰。这种情绪自然容易理解,但他们对金钱、对购买力、对投资观念的理解却不够深入。
事实上,单就各俱乐部的经济后援而言,北京国安是无人可望其项背。最热衷于买球员的宏远集团去年固定资产为13亿人民币,而国安实业总公司的固定资产在18亿元。北京国安足球队的另一个名号是中信俱乐部,也就是国安总公司所属的中信集团,这是一家更庞大的买卖。
北京国安队在1995年初似乎对买球员没有兴趣,而联赛战罢,球队从1994年的第8名打到了第2名,他们将采用什么措施来实现争到第一的目标自然得到人们的关注。国安领队杨群以一句“火候不到不揭锅”来遮掩国安队的投资意向,但渐渐透露出的消息让人感到一种更强的霸气。国安队要买5个球员,这是中国足协规定的最高限量,而这5个人都披国字号战袍,他们是延边现代汽车队的李红军、四川全兴队的魏群,辽宁队的于明、姜峰,上海申花队的申思。
国安队主教练金志扬在展望96年甲A联赛时表示,去年联赛的战绩已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各支球队在新赛季中的实力主要取决于在转会中购得什么样的球员。
球员转会的确是甲A搏杀的前哨战,然而,这战斗中似乎火力侦察太多,短兵相接少。
转会怎么会“转”不起来
如果我们真把转会看作是一场战斗,那就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游戏规则”,也就是中国足协的球员转会细则。我们可能熟悉这样一个典故——第22条军规,在中国足协的球员转会细则中,第22条规定同样是一个逻辑上的“黑色幽默”。
这一条规则这么写:“运动员转会后与俱乐部签订工作合同,所有待遇应与俱乐部其他运动员相当。在此之前,接受运动员的俱乐部不得在转会费之外,以工资、户口、住房等引诱运动员转会,此为不正当行为,违反者将受到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的处分。”
如果按照这条规则来对待转会,那么转会的意义就是剩余劳动力输出。职业球员的含义就是以踢球为职业,球员如果把获取个人的最大收益作为一项准则是无可厚非的。显然,中国足协的这项规定是为了平衡各俱乐部的实力,而没有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去看待球员的利益。
纸面上是这样说,实际上没有哪个俱乐部与他们想要的球员接触时不许以高薪,不考虑他生活中的种种顾虑。而违背这项原则的行为可以是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球员所属俱乐部以工资、户口、住房来挽留自己的队员。据报道,延边队李红军欲加盟国安,延边队便要留住他,李红军的父亲提出的条件就是要一套住房,把李的女友的户口从图门市调入延边。
职业球员的收入本应只有年薪这干净爽快的一条,而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户口、住房也算是待遇中很重要的内容,这两样东西不该成为推动转会市场的工具,却能成为不让球员转会的武器,中国足协的“第22条军规”就在此形成悖论。
第23条规则则更为荒唐,该项规定是球员转入联赛名次低于原俱乐部的球队,其在新俱乐部中的工资和奖金不得高于原俱乐部的水平(可以有地区差价),违者将吊销比赛许可证。显然,这条规定更明确地禁止了球员对利益的要求。那么,申思的情况是如何呢?他在上海申花队打不上主力不是因为水平问题,而是他的技术特点不适合球队的战术要求,提出转会合情合理。但在上海市有关领导的干预下,他转入了甲B的上海豫园队,他的工资和奖金是不是比在申花队时少了呢?如果真按这第23条规则办事,那么拿冠军的球员就甭想转会了,因为他第二年必须留在原队才能保证不降低工资。
有时候,制定规则的人就是这样头脑简单,根本不去考虑这规则执行起来是多么不可能,不过,他们知道这规则的执行情况检查起来也不大可能。
但是,有两条新规则却执行贯彻的很不错。辽宁队的降级本可能使球队成为今年球员市场中最大的供货商,但1995年底的足球工作会议规定,在原培养单位职业队或半职业球队服役未满4年的球员以及当年联赛降级球队队员,俱乐部有权禁止他们转会。这样,庄毅、于明、姜峰就不大可能离开辽宁队了。
1996年新年前夕,在昆明参加国家队集训的姜峰仍表示希望能效力于国安队。而辽宁方面已表示,不允许姜峰等人转会,国安则试图以借调的方式让姜峰先到北京踢一年球。当年,在意大利谋生的巴蒂斯图塔在佛罗伦萨队降人乙级后继续为该队效力,帮助球队用一个赛季打回甲级,人们纷纷赞扬巴蒂斯图塔舍弃个人名利的义气。现在,姜峰、于明、庄毅都必须向这位阿根廷球星学习了。
或许,只能等到中国球员人才辈出之时,各俱乐部都腰包鼓起来之日,转会才可能形成动态中的平衡。而改革的决策者应该为转会的市场规范立下更合理的条目,如果一个球员与俱乐部的合同已经到期,而俱乐部却据有不能让他走的尚方宝剑,那么,那份合同还有什么意义?确定雇佣关系的合同还有什么法律效用?
转会制还有什么问题
中国足协某些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规定的确限制了球员转会,但对中国足球的发展而言,还是起到了稳定的作用。对于职业化程度较低的足球俱乐部来说,转会制是一剂略显霸道的虎狼之药,需要人们好好消受一番。足协的某些细则无疑起一些缓冲之用,使药性不那么强劲。
然而,一味温和缓解也不是办法,职业化要让各俱乐部尽快形成良性循环,在经济实力与球队战斗力上都趋向平均的态势。而这些具体办法要由各俱乐部自己拿出来。
1995年初受转会制威胁最大的济南泰山队在今年却军心稳定,因为他们在去年联赛中保持了良好的状态,并夺得足协杯冠军,球队正处于上升期。但并不是所有的球队都能“稳如泰山”。
联赛后较为动荡的是八一队,主教练换了,队中两名主力郝海东、王涛都萌生转会之意。八一队是甲A球队中最为特殊的一支,既不像大连队之有万达集团为靠山,又不像天津队之有韩国三星赞助,但他们却保持着最好的后备力量。这样一支球队该如何在球市中具备竞争力实在是个问题。
转会之所以如此敏感,如此牵动人心,实在是因为各球队在经济实力上存在较大的差别,既然足球改革的决策者已限制了市场的冲击力,下一步的工作自然是完善俱乐部,缩小贫富差异。
而在今年转会期出现的两件事情对于中国足球也具某些更长远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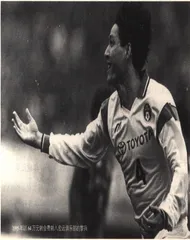
1995年以64万元转会费转入宏远俱乐部的黎兵
一是大连队引进外援。据悉,大连万达队招募的3名瑞典球员极具实力,但在价格上略显昂贵,俱乐部与瑞典方面一直进行讨价还价。职业联赛进行了两年,但洋球员的水平已让不少球迷对引进外援失去信心,能否引进高水平外援从而促进本土球员战术水平的提高,该是各球队多加考虑的事了。
二是高洪波意欲离开国安。这多少反映出目前各球队训练体制的问题,高洪波在新加坡是走训制,球员自己掌握的时间充裕些,能更好的照顾家庭。而他在北京大多数时间都要在队中集训。或许现在的球员的确不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搞走训时机不成熟,但总把球员关在宿舍里也不是永久性的办法。 中超足球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