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丢钱,再丢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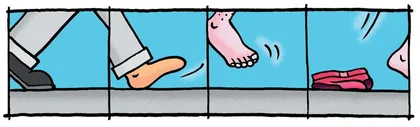
中国文人常以“百无一用”自谦,其实他们个个都身怀一种百里挑一并且百发百中的绝技,就是把个人的私事变成大家的公事,道行高的,甚至能上升为国事,例如郁达夫的《毁家诗记》。
“诗记”中有《贺新郎》一词,下阕是:“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据作者注,1937年8、9月左右,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乘他与王映霞不和之机,某次饭后,使王失身于许。“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郁达夫其实有充分理由把“家仇”上升为“国仇”——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富阳,郁母陆氏因拒日军苦役躲入鹳山,12月31日冻饿而死;1939年11月23日,长兄郁曼陀在上海寓所门前遭特务枪杀,成为抗战中“司法界为国牺牲的第一人”。然而,不论王映霞红杏出墙是真是假,“诗记”里的这段话以及屡呼王映霞为“姬”、“下堂妾”,令时人及后世对作者颇有微词,多指其对女人不够厚道,“达夫无行”或“心理变态”。与此同时,把“先逐寇,再驱雉”盛赞为“猛虎舔创”之后心理升华而至民族大义者,亦不乏其人。我个人的看法是,红杏出墙,除了母系社会,这事儿搁在任何年代任何时代背景,基本上都是一桩私事。家丑是家丑,国仇是国仇,不可轻易混为一谈。许绍棣虽在政治上与郁达夫有过节,毕竟不是日寇。故“先逐寇,再驱雉”之间很难建立起伦理道德上的必然逻辑关联,除非作者能像论证“朋友奸淫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那样,对“若无日寇侵华,许绍棣就断无充当第三者的机会”也做出同样充分的论证。
作为一个半新半旧的文人,一个怀疑自己不幸戴了绿帽的浪漫主义作家,诗怎样写,话怎么说,都可以理解。比较难以理解的是后人不断为《贺新郎》所加之新注:“最终的矛头所指并非王映霞,而是那位曾经呈请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他又恰好是在抗日战乱中闯入郁达夫私生活的第三者,于是这个人在郁达夫心目中就成为反动派和一切卑劣行为的典型⋯⋯声明不要稿费,只要十册书,另外要以他的名义分寄给蒋介石、叶楚伧、于右任、邵力子、柳亚子等,更可说明他发表《毁家诗纪》的目的是为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拆。”(郁风:《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
1937年8、9月左右,郁达夫在福建做官,故许绍棣“在抗日战乱中闯入”之说虽觉勉强,却终非空穴来风,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拆”之语,就有些言不由衷了。什么是一个作家禀其道德力量和崇高天职向社会发出的“控诉”?我认为左拉玩的那种才算,向着不公平的司法制度开火,检验了《人权宣言》,最终推动了民主和法制进程。《毁家诗纪》的“爱人不见了,向社会去喊冤”与这种结果相比,显然相距甚远。
最近一个为《贺新郎》加注的是作家龙应台。年初她在广州遭遇小偷,事后撰文《一个警察的背后》:“广东一亿多人口,只有13万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问题⋯⋯知道了这个数据,对中国警察便不忍苛责,可是,这是现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一连串不依不饶的追问之后,又从“户口制度和城乡差距的问题严重恶化”上升到“国家的根本政治”,最后更引读者来信指“只要腐败依然存在,只要贫富分化还在加剧,只要体制不变,一切仍将继续”。
普通人丢了东西,搓火,骂人,然后该干嘛干嘛;知识分子丢了东西,尤其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丢了东西,却不可白丢,至少也得让普通人付出挑战自己常识的代价。我也有在广州遭遇小偷的不幸遭遇,但实在没有上升到“国家根本政治”的本事。我的常识只有这样两项:一、计划经济时代虽不至于路不拾遗,但广州的小偷肯定没现在多;二、警力比广州充足,“户口制度和城乡差距的问题”没中国严重的地方如纽约或法兰克福,随地小便虽基本已断,却从来也不曾断过随地小偷。偷人和偷东西这两种勾当,好像都不以制度的意志为转移。
就像郁达夫当年在《悼胞兄曼陀》一文中对“家丑和国仇”关系所做的准确阐述那样,类似的道理其实已讲得再清楚不过:“那个街口不必是在广州老城,也可以是罗马喷泉、莫斯科红场、华沙广场、法兰克福火车站大道,以那样大方不设防的架势,往任何一个城市中心一站,对于那个城市里活跃于灰色空间的人而言,怎么说都是一种挑衅或邀请。所以我的遭窃绝不足以被解释为‘中国特色’。”卿本佳人,奈何技痒?“先逐寇,再驱雉”者,可谓“先丢人,再丢份”,后一种,岂非“先丢钱,再丢人”乎?■ 读书郁达夫王映霞丢人许绍棣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