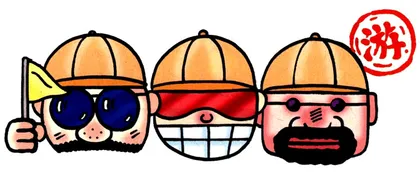游客观点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步难。纵有千难万险,出门的一大好处,就是能以游客的身份乱讲话,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就像30年代游苏的罗曼·罗兰以及70年代在中国做游客的罗兰·巴特和拉康那样。
一个人做回游客并不难,难的是在任何不规定的时间和任何不规定的地点都能保持游客的身份并表达符合这一身份的观点。90年代中,北京某杂志邀得在京或不在京的有识之士一批,各撰美文一篇,以胡同、四合院为题,天昏地暗,风花雪月地各诉衷情。王朔最后发言,他大煞风景地说(大意),打小在胡同里长大,却丝毫也没有诸位的浪漫情怀。胡同及两侧的四合院,又脏又臭,最不可忍者,厕所也,天寒地冻,北风呼啸,也不得不披星戴月,提着裤子跑到街上寻公厕而蹲之。像这种令人咬牙切齿的所在,若不以推土机一夜间全部推倒了事,不足以平民愤。而在苏州“一条市井气息浓郁的街道上”生活过18年的苏童,后来也跟游客们抬过类似的杠。他表示,绝不会从旅游的角度赞成保留苏州小街上的棚户区。那些留恋小桥流水的人,让他们用一下苏州老城居民家里的马桶,大概就不敢发表那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了。
若要两头都不得罪,照我看,目前技术上惟一的楷模,就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整成上海“新天地”的那种“范儿”——让外国人(外地人)相信那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上海,同时令上海人觉得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外国。遗憾的是,迄今未见如上海“新天地”般的成功个案,近来倒是有个别不住在中国的国人在观念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代表作是我在《读书》月刊上读到的《美国郊区的“诗意”与隐私霸权》一文。作者是1988年去国旅美的中国学者王教授。王教授在美国郊区住了十年,对那种地方既恨之入骨,更忧心忡忡:“最大的感觉是,郊区的文化和居住环境,是完全洗尽,脱去了人味。人之为人,很大趣味在于能嗅到邻里的人气。美国郊区的‘文化’则强调远离政治的隐私。”即使干净整洁,也是整洁到“刺眼”,让人“难受”。“这一难受,你紧接着就会纳闷,住在这些房屋里的人都在干什么,忙什么,怎么并不见人呢?”好不容易憋到星期天,人是见着了,但是人家洗车除草,热爱劳动,更让王教授生气:“人人一天到晚对一地鸡毛的小事进行协商讨价,家政重如泰山,而国事、天下事充耳不闻……这种锱铢必较的‘谋生计’民主,其实在一天天瓦解真正的、公共参与的民主。”
长期在美国郊区卧底,时刻保持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游客心态,已属不易,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念念不忘以故国神游的姿态来为自己抹一回“印度神油”:“近年,中国人新建小区,拟想中常有美国郊区的楷模和欧陆经典。但在西方,反对、批判郊区生存模式的言论和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在物质完美的社区中,公共政治意识的隐退,私人空间的膨胀,会把人逼向死角,形成社群生活的萎缩。”作为一个广州郊区的住户,我不太明白住在美国郊区何以导致不关心政治。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表明,收入与投票率成正比。投票率最高者年收入在50000至75000美元之间,达69%~74%。美国中产家庭占总人口80%,年收入约25000至100000美元。不关心政治的倒是包括华人(相当部分住唐人街,即张爱玲“中国人欣赏拥拥挤挤,人声嘈杂的街市或气味相投的邻居”)在内的亚裔。人口普查局7月底称,全美亚裔选民登记率为3.4%,实际投票率只有31.2%,比起前几年来不升反降。
王教授可能并不认为票选总统是“真正的、公共参与的民主”,而投票之踊跃与否也不能作为“关心政治”的指标,同理,若不站在“游客观点”的高度,王教授的忧国忧民,无非也就是一在国内东家长西家短惯了的中国人居美后通常的不适应。不过这并不妨碍我把他们视为林语堂高度赞赏过的那种“真正的旅行家”:“旅行的要点在于无责任、无定时……一个好的旅行家决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从何处而来。”王教授们显然已经忘了他们来的那个地方的历史,至少是1988年之前的。1980年之前,我一直住外滩的一座老房子里,七十二家房客,“人气”(尤其在公共厕所和公共厨房)之丰厚,王教授嗅之,绝对High翻,与此同时,因“人气”丰厚而无限膨胀的公共意识,令私人空间隐退到几乎不存在,尤其是“文革”期间,把所有人都逼向死角。从小我就发过毒誓,长大后打死也不住这种鬼地方。20多年后,除了节假日偶遭邻人的麻将及卡拉OK滋扰,童年的愿望算是基本实现,但是话说回来,游客观点和“在地者”之间的冲突,要害是旅游业附加值不高,最起码与工业园或开发区相比。只占全市GDP比例8.5%的苏州旅游经济若能如工业那样占到GDP50%以上并且直接令当地市民受惠,我相信苏州人民并不介意(至少在旅游旺季)使用马桶,甚至不介意穿着古装在街上闲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