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选择看戏,还是选择思考 记
作者:马戎戎(文 / 马戎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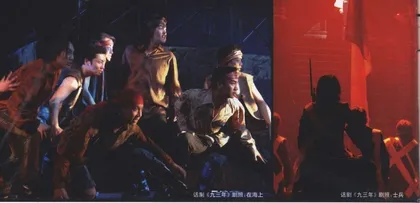
话剧《九三年》剧照:在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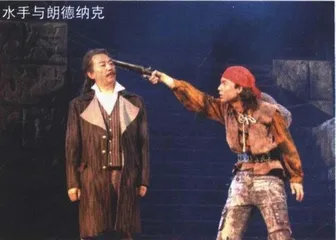
水手与朗德纳克
对一个仅仅是来看“戏”的普通观众来说,2004年4月23日国家话剧院为中法文化年推出的《九三年》未必见得好看。
作为雨果的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的重点不是赚人眼泪的故事,而是对革命和暴力的反思。读小说的人,无法不被雨果的语言之美和对法国大革命尖锐的剖析所打动。而对于把它改编成话剧的人来说,如何既保留雨果的思想又不使全剧变成诗歌朗诵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或许就是《九三年》在改编成大众娱乐形式的几率上远远低于《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的原因。作为话剧《九三年》的编剧,曹路生将剧情集中在郭文、西穆尔登和朗德纳克三人的矛盾冲突上,保留了原著音乐般诗化的语言,全剧充斥着大段大段韵律感很强的台词,最长的一段独白达到8分钟。这种处理尽管与原著的浪漫主义风格一脉相承,但无论是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在孔雀街小酒馆里大段大段的时事辩论,还是朗德纳克和西穆尔登对革命前途的探讨,都要求观众具备一种在当下极为可贵的品质:耐心。
另一方面,略显空旷的舞台调度和相对平实生活化的肢体语言,也使大剧场里的观众感受不到习惯感受的“震撼”。尽管曾经多次涉足影视剧的导演汪遵熹将一些电影手法融进了话剧当中,比如全剧伊始,一群扭曲、伸张的人体,从梯阶上缓缓翻滚下来。演员们的四臂幅度渐渐增大,体现了人们从压抑痛苦到奋起抗争,逐步进入亢奋,最后出现狂欢,渲染了1793年那个革命年月人们精神与肉体上的躁热和骚动。在战斗中,士兵们冲锋或倒下,均以电影慢镜头似的形体动作来体现,肢体语言的张力尽在其间。但在全剧中这样有意味的片段毕竟太少,在海淀剧院的广阔舞台上,20多人的场面并未能体现出意图中的宏大,削弱了《九三年》宏阔激昂的时代感。作为一个特意坐到第一排的观众,我失望地放弃了再次感受那种紧逼灵魂的震撼力和忘我的情感投入,只是非常冷静地体味着台词的优美和随处闪烁的哲学光芒:“比天平更高一级的还有七弦琴”,“只要有墨水,就有污点”。
不过,这种冷静正中导演下怀。曾经导演过《我所认识的鬼子兵》、《伐子都》的导演汪遵熹认为,大段大段的台词,固然会今一些观众认为乏味,但更会使一些真正的观众来思考,来品味,他并不要求观众回报给这出戏廉价的眼泪,只希望观众能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思考雨果和《九三年》提出的问题:在暴力革命中,人性的位置在哪里?他说:“我觉得审美愉悦不但是感官的愉悦,也是思考的愉悦,而中国观众目前缺少的就是思考的愉悦。”
对思考和严肃命题的重提,或许是《九三年》最大的价值所在。作为单纯的戏剧,《九三年》未免显得平淡;但对于《九三年》提出严肃命题的责任感和勇气,我们应该保持敬意。不过,观众的权利体现在可以自由选择:选择看戏,还是选择思考。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或许应该给《九三年》打上一句广告语:《九三年》——给爱思考的人的礼物。
汪遵熹:中国观众缺少思考的愉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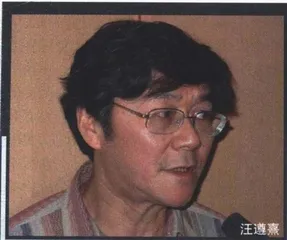
话剧《九三年》剧照:士兵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都说《九三年》是目前“新主流戏剧”的一部成功之作,你怎样理解“新主流戏剧”,“新”在什么地方,“主流”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汪遵熹:“新主流”其实是媒体创造出来的词。《九三年》被称为“新主流”,可能是因为这部话剧是根据经典小说改编的,主题也很严肃,不像流行戏剧或是时尚戏剧更多的还是一种商品的感觉。而是更注重文学性、思想性。至于“新”,是因为我们这个戏并没有完全按照传统的方式去处理,因为毕竟要考虑到今天观众的审美角度。小说是雨果在100多年前写的,表现的又是200多年前的事,如果完全按照传统去处理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在二度创作的时候还是努力希望今天的观众能够接受。
至于“主流”,是因为话剧本身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在我的感受里,戏剧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如果说得夸张一点,应该是人和上帝的对话。但是现在的戏剧,品位越来越往下降。我想在《九三年》里传达一种对革命和生命的思考。革命和人性处在一种悖论状态的时候,人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雨果的伟大就在于他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革命和人性的悖论。这个题目其实现在很多思想家哲学家都在探讨。平等、博爱好像离人们越来越远了,面对经济、政治上的压力,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什么叫自由,什么叫平等,什么叫博爱,这个问题法国大革命没有解决。而这部戏主要也是在这里进行探索思考。
三联生活周刊:据说你为了排这部戏,请了法国历史和法国文学的专家来做报告。那么您认为,在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九三年》这本小说和所处的时代?
汪遵熹:我们请了很传统的搞法国文学的教授,也请了像孔庆东这样思想比较解放的教授,大家需要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各种各样的帮助。
今天应该怎样看这本书,这个时代,是个很大的题目。孔庆东博士也提到这个问题,在今天演这个戏有什么样的意义。那我想就是全球化的压迫使人们越来越感到不自由,越来越感到缺乏平等和博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重新来看待法国大革命,也许革命本身是很幼稚的,很冲动的,但确实是很伟大的,因为它颠覆了一个时代,进入了新的时期。正是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世界各国的革命。东欧解体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观点,出现了许多对革命和暴力的质疑。我希望观众看到这个戏,能够重新对这些问题产生兴趣,我也希望这个戏能够让大家回头来看原著,看看《九三年》究竟是什么样的,雨果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
另外就是我现在感到随着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精神状态越来越贫乏,人的这种状态不好。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读经典作品,大家都喜欢看连环画、卡通、球赛、拳击,静不下心来,内心很空虚。当然我知道物质生活丰富是好事,但是我们不能丢弃思考。我希望大家还是能看一些严肃的、思想性的东西。否则是很可怕的。一本书当然无法回答这么多问题,但它至少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以前排过的话剧中许多都来自文学作品,而且你一直都坚持“戏剧的内核是文学”。在目前的戏剧界,你的看法似乎有些保守。
汪遵熹:这些年,我们对戏剧形式做了很多探讨,搞了很多形式上的突破,或是以后现代的形式进行肢解,或是借鉴了很多别的形式:多媒体啊,舞蹈啊,杂耍啊。这都无可非议,因为多元么。但是丢掉了戏剧的根本:文学。文学是戏剧的根本,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好的戏剧要求扎实的文学根底,要求语言的魅力。我觉得现在人们看戏对语言的关心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戏剧和别的艺术形式的很大的区别就在于语言,语言的魅力是无穷的。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文学和戏剧毕竟是两种载体,很多人在看完你的戏后认为你过于注重戏剧冲突,没能表现出那种宏阔的时代感。而你采用了一些比如现场换景的手法也让人对这部戏有一种间离感,无法迅速地参与进去。
汪遵熹:把一个长篇小说改成两小时的戏剧会丢失许多东西。但我们不想把他搞成一个简装本或连环画,这样会丢失得更多。我们丢掉了法国大革命的详细描述和雨果的很多政论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无法在舞台上还原的。我们更强调了革命暴力和人性冲突的这条线,以依弗朗莎和孩子的这条线带出了郭文、西穆尔登、朗德纳克这三个人。在他们的故事中,我们保留了雨果的风格,用了大段的辩论。所以,这次戏为什么看得很吃力呢,就是因为这些大段的台词辩论,包括这种整体的文学性。我们努力把小说的精髓保留,想让观众看完了以后说,雨果很有意思,同时想回去看原著。
至于我采用了在戏剧进程中转换布景的方式,这也是考虑观众在审美中的要求,不想因为技术问题影响观众的思考。我觉得审美愉悦不但是感官的愉悦,也是思考的愉悦,而中国观众目前缺少的就是思考的愉悦。但是我认为我这场戏应该使观众在满足视觉、听觉的同时满足思考的愉悦。我不要求观众跟着我的戏掉眼泪,不要求观众想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的戏里连爱情都没有,所有的人都在谈革命。除非你是个政治性极强的人,否则我想更多的观众是相对理性的。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你希望观众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观看、思考《九三年》?
汪遵熹: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在感官和理性上都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