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哈斯事件:旧传统与新历史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吴耀东
库哈斯的央视新大楼,还有“鸟巢”与“水立方”,以及先前的国家大剧院,这一批建筑的出现,我更乐意将其称为“事件”。为什么说“事件”?是因为它已经脱离了建筑领域而进入大众关注的话题。
比较而言,国家大剧院争议最大,从积极的角度看,大家突然发现,原来建筑还可以这样做。结果带来的好处就是,现在有了库哈斯的大楼,还有奥林匹克的新建筑。我们现在对这些建筑的评论,客观说,还是局限于几张效果图,是对形象的评论。这些建筑只有当它们真正建成以后,设计师的梦想是否真正变成了美丽的现实,我们才可能得出答案。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的事实在于,以这些建筑为代表,北京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新的历史。
从建筑的角度想库哈斯的设计,这么一座像小型城市的建筑体,要面对的问题可能都是过去未曾面对过的问题。比如防火规范,还有结构规范等等,都是挑战。而正是建造这幢大楼所面对的各项挑战,最终会带来这个国家的进步。
看上去是我们这些评委选出了三个方案,然后有关决策者又三选一,决定了央视新大楼。但事实上,评委也是生活在现在的中国,他们的意识与现在的普通中国人是同步的,因此你不能说是几个人开始了新历史,而应当说这个国家开始了自己的巨变。
刘开济
一个城市是一代一代长期建造起来的,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巴西的新首都是一次性地平地而起,可是他们也会随着生产生活变革而变革。我们现在的新北京面积是古都的若干倍,我们应该考虑历史有延续性,还要随着时代而变革。新城可以不受老城的限制,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要有反映时代的作品,同样比较新的作品不要盖在古都附近。威尼斯、巴黎都有很好的实践,在CBD盖一个库哈斯的作品是可以的。
张锦秋
库哈斯的作品建在新城可以,如果建在天安门广场我就要反对。我刚才说过要有城市设计的观点。国家大剧院的方案我就反对,不能孤立地说它好还是不好,看他的位置,在哪里为哪个环境服务。我不能容忍国家大剧院这种天外来客。我批评在该保护协调地段进行破坏,但不等于说新区就永远不能用其他的风格,古都要“新旧分治”,旧城有旧城的保护协调原则,在新城区有新城区的规划。巴黎、罗马就做得很好,过去北京做得不够好,但不能因为过去做得不好而妨碍现在在新城区里放手创造。
我不认为“现代的”就是“西方的”,中国需要现代的东西,为什么“现代”的一定是西方的?其实首都已经盖了那么多的高楼,搞了很多的国际招标,有几栋是真正大师的杰作?很少,贝聿铭做过,还有谁?不太多,这次的评委之一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陈刚说,北京真正大师的作品太少了。中国要有一些真正的大师级作品,对建筑界有些促进。
其实建筑惟一的出路就是创新,创新不意味着套用外国某一个具体的形式作法,在新的条件下做出的东西可能都是创新。
我不喜欢拔高和夸大。要现代化,但不能对全国的建筑都用奥运场馆来做大家的榜样,以家庭为例,我相信家庭客厅里摆两件工艺品在那里很好,但是到处都摆就没有生活气息了。国家也是一样,城市性质、规模不同,建筑项目就要有自己适当的位置和特色,不能说奥运场馆就是全国建筑的发展方向,这几个建筑都是国家级的很特殊的,在这上面花点钱未尝不可,但是不能都这样。
严迅奇
对大建筑,一般人的接受度与专业人士的选择,无论在国外还是在香港地区,都是有一定差距的。在中国内地当然也一样,不过我发现,北京的接受度比其他国家反而要高一些,比如“鸟巢”、“水立方”与库哈斯,当然这与它们不在老城区有关。与故宫、天安门那些代表我们传统的建筑比较,这些新建筑当然就代表新历史了。在同一座城市里,你说故宫与央视的新大楼有没有冲突?当然有冲突,这是进步必然付出的代价。我思考的结论是,建筑彼此的不协调,不一定是坏事,可能是好事,有了不协调,才可能讨论新的路标、新的发展,这是进步的动力所在。不协调,也不是互相不尊重,也可能互相尊重的。
我也思考为什么这些建筑作品入选,我的结论是:建筑是一种表达,对中国未来新形象有一种希望蕴含在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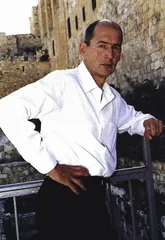
库哈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