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哈斯来中国以前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施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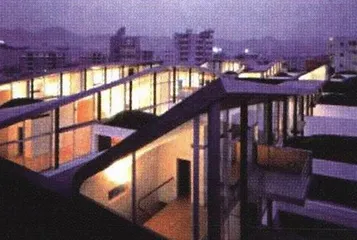

库哈斯作品

库哈斯为在纽约新张的Prada店做的设计
解构建筑师
1988年3月在伦敦泰特美术馆举办了第一次解构主义学术研讨会,同年6月在纽约大都会现代美术馆举办解构主义建筑七人展,参加展览的有富兰克·盖瑞、楚米、有库哈斯的师傅艾森曼,经常与库哈斯合作的哈迪德,当然还有库哈斯。解构主义建筑从此名声大作。
解构主义以共时性观点强调理性和随机性的对立统一,共时性的观点在设计上就可以不对历史踪迹的记忆做出反映。解构理论在建筑理论上的影响,产生了对“历史建筑代表历史进程”的怀疑,以及对建筑秩序的(关于形状、色彩、比例、尺度)的摆脱,除了城市本身的限制,建筑在具体处理上可以极度自由放任。
这些解构主义建筑师也各行其是,库哈斯习惯于搬弄大的板块,把这种大板块旋转、倒置、全然无视地心引力,再给它们分别涂上不同的鲜艳色彩。但是他自认是没有风格的建筑师,因为他关心的不是建筑,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筑实现的生活。
库哈斯1944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1963年他选择的职业是为报社做专栏记者兼业余剧作家。1968年他到伦敦上了建筑协会学院,简称AA,这是英国最好的建筑学院,入学时候正是五月风暴的革命期。
建筑学院毕业后,他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学业,而后到纽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做访问学者,那里的主持人是后来“解构七人展”之一员艾森曼。库哈斯从那时起研究曼哈顿,他发现这里拥塞着城市生活中最多样最复杂的片断,片断之间可以有联系,也可以是互不相干,甚至是对立的。这种城市形态与任何关于城市的理想都不符合。他认为这是当代经济体现的强大活力,展示了对生活的异化能量。纽约的种种神奇是否展示了大都会城市的一种未来摹本?这不仅是对建筑或一个城市的研究,而且是对当代生活的研究。正因为此,他花大量时间研究城市现象,以至普里茨克奖评委会认为他的著作可以和他的建筑媲美。
思想家
所以在进入建筑领域后,库哈斯维持了一段长时间的理论研究,等到他第一次必须实际建造一个建筑时,他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位思想家。
在探究曼哈顿规划和背后策略的研究中,他以一种近乎颠狂的状态漫游纽约,试图寻找另一种秩序。他认为纽约体现了当代大都市的特殊文化,其主题包括科技炼金术的幻想,曼哈顿的建筑就是这种炼金术的实验;自由的幻想,就是在想像中创造各种并置的意义,并融合其中互不相容的歧义;欲望的幻想,针对的是激情和感官享乐的再创造。整个城市成为人造经验的工厂,在这里,真实和自然荡然无存。曼哈顿就是这种文化实验场。大都会奋力达到一种完全由人杜撰的神话,因此它在极大程度上与人的欲念相一致。他在这里寻找到的秩序被他称之为“淤塞文化”——拥挤淤塞不仅是指物体的,更重要是内容,它们都以某种形式聚合叠置在一起。只有在这种淤塞文化里,曼哈顿的疯狂建筑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由于尺度的巨大,建筑内部与外形之间的距离变大,所以外部跟内部没有了明显关系,建筑的形象根本不能反映里面的生活,所以介于建筑内外之间的人性关系也就没有了。内部各部分的关系也一样,各空间都自治和独立;在巨大建筑里电梯就被他赋予了非常的功效。在第四届圣保罗“艺术/城市计划”上,库哈斯自己做建筑后选择的地点是一栋公寓,这个公寓有世界最大垂直型贫民窟之称,4000多人挤在这27层的建筑里。如此高的居住密度正是库哈斯选择它的原因,他的计划就是恢复其中失修的电梯功能。库哈斯一直将电梯视为在建筑内建立联系促进社会功能转化的功效,建筑师的作用就要随之改变。
这还只是暗示了一个潜在的“大”理论,1995年他与人合作出版的《小、中、大、超大》一书明确地论述“大”的属性。这是一本文集,包括对OMA 崛起过程的描述和对作品的追述,还有评论文章,诗歌、图表、绘画、摄影、日记等等,通过种种途径研究关于社会、建筑和都市发展。像一部大都市的百科全书。此外,人们还热衷于谈论这本书的重量,它总共1345页,重达6磅。
O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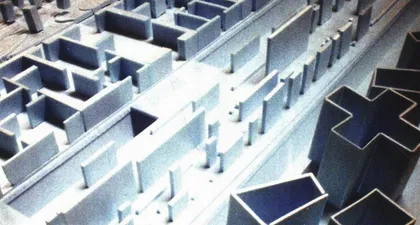
2000年库哈斯获得普利茨克建筑奖。图为库哈斯为洛杉矶艺术博物馆设计方案,但因为资金问题,一直没有正式兴建
1975年他和两个同伴在伦敦成立了“大都会建筑办公室”(OMA),从它的命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库哈斯延续着他对现代大都会生活和建筑之间关系的关注,并要在实践中继续他的宣言。
1978年他对曼哈顿的研究成果《癫疯纽约》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库哈斯名声大作。同时OMA迁到鹿特丹。库哈斯通过一系列实际的设计和规划方案进入对欧洲城市的研究,赢得了许多国际大奖,并且以“库哈斯和公共建筑空间”成为纽约现代艺术馆1995年回顾展的主题。
1987年以后,OMA业务中的国际合作项目让库哈斯开始面临亚洲城市,他在这里发现,在西方被想象而没能实现的巨构建筑在新加坡、日本被实现着,这种建筑上的相似其实是思想克隆所导致的城市意识的同化运动。他认为在这种合作中,建筑根本不是不同文化交流的结果,也不是投资和回报谈判的结果。全球化把真实的建筑虚幻化了,以致这些建筑根本无法在建筑的意义上被理解。如新加坡,在库哈斯眼中,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理念的产物,因而成了一种缺乏真实感、没有质量的城市,但他显然也只能认可这种冷酷的力量。
考察研究了从美国到欧洲的城市,亚洲新兴城市逼迫库哈斯思考全球化导致的城市趋同现象,他认为以这种现象在亚洲的巨大规模来看,它一定意味着什么,于是提出了“广普城市”的概念。在对“广普城市”的探讨中,首先遇到的是城市的“个性”价值是什么?如果它可以被当作对历史遗产分享的形式,注定是要消失的,因为:一方面由于人口膨胀它不足以为那么多人分享,个性还吸引了观光客的加入,更增加了它被滥用。历史就如同一个活物,越被滥用就越丢失意义。另一方面,当今消费社会所制造的东西和那些来自历史环境的个性基本没有关联,而“广普城市”是对现实需求的反映,也是对满足需求能力的反映。尽管这样的城市是肤浅的、不需要维持的,旧了还可以重建。库哈斯针对亚洲城市提出“消失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破坏和建设的交替周期,这个过程,不再是那种添加细部来调整城市空间,而是完全根据现时需要。这就是广普城市的伟大原则——用现实主义打破理想主义。
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
有评论说相比那些为传统城市的损坏而哀叹的批评者,库哈斯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另一个角度上看,也可以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的积极态度。
1975年,柏林举办的一次城市建设国际展览会上,库哈斯认为,在二次大战中几乎被完全炸毁的柏林,50年代为建设柏林又拆除了很多历史建筑,再没有什么可以保护或修复的了。如同它曾经的辉煌一样,它被毁坏的结果也是历史记忆,成熟的历史态度就不能无视这样的历史记忆,也不能用赝品来修改它。他认为,有目共睹,在现有的城市中,整体形象已经被割裂,而且可利用来继续发展的余地也极为有限,新建筑都是见缝插针,你根本不能指望哪个建筑受控于传统城市的形式,也不能指望什么样的建筑能对城市整体形象担当审美的义务。他认为,一切都只能服从于这个城市本身的逻辑,如同《癫疯纽约》书中插图所比拟的,城市中的建筑代表的都是些欲望妖怪,城市就是欲望的约会。不管是传统城市的形态,还是现代主义的理性规划,都已经被现实的城市所背离。城市已经变成了无数零碎的、不确定的、混乱的、没有秩序的、不美的,多元的细节。既然如此,库哈斯的姿态就是服从城市的现状,进而参与到城市的未来。
《小、中、大、超大》一书的序言里,库哈斯把建筑定义为“全能与无能的危险混合物”,建筑师的设计过程就是“一场混沌的冒险”。因为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规模扩大,城市更新频率的增长,这是建筑师不得不面对的真实。建筑师于是不能在任何一种乌托邦意义上来搭救城市。既然人类一定要脱离地面,建筑所能做的就是让空中的生活更有意思,或更有活力。尤其是提出了“广普城市”的概念后,创造有个性的建筑再也不是建筑师工作的出发点,顶多可能是个结果。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选自《世界建筑》以及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建筑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