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基”看舞曲兴衰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袁越 林逸聪)

迪斯科音乐的最佳代表“比基”乐队

《周末狂热》曾经风靡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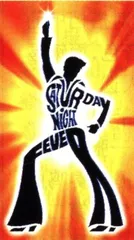

莫里斯·吉布生前经常光顾的餐厅,这个座位还为他留着
今年1月12日,著名的“比基”(Bee Gees)乐队贝司手兼键盘手莫里斯·吉布(Maurice Gibb)死于肠梗阻手术后引起的心力衰竭,享年53岁。虽说“比基”乐队是曾经风靡一时的迪斯科音乐的最佳代表,而迪斯科又是最早引进中国的欧美乐种,可“比基”乐队在中国的名气却很小,大部分关于欧美音乐史的文章都很少提及他们,很多欧美歌迷大概直到今天才知道他们的大名。如果莫里斯早死10年,恐怕骂他们的要比纪念他们的更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其实“比基”乐队并不是靠迪斯科起家的。乐队的三名成员是亲兄弟,大哥名叫巴里·吉布(Barry Gibb),莫里斯和罗宾(Robin)是孪生兄弟。三人出生于英国,却在澳大利亚长大。三兄弟很小的时候就上台表演,年纪轻轻就成了澳大利亚歌坛偶像。“披头士”乐队的走红给了三人很大的刺激,他们立志要做“披头士”,开始唱起了摇滚,莫里斯的贝司就是跟保罗·麦卡特尼学的。
除了“披头士”以外,他们的音乐口味受美国影响也很深,当时美国正流行一首名叫《旧金山》的歌,歌颂源于旧金山的嬉皮士风潮。三兄弟便照猫画虎,写了一首名叫《马萨诸塞》(Massachusettes)的歌,告诫那些从东部移民旧金山的嬉皮士们:还是回家吧,马萨诸塞仍然是你们的故乡,那里有你们心爱的姑娘。这首歌是典型的民歌摇滚风格,加了很多弦乐,节奏缓慢,特别讲究和声。三兄弟从小就在一起唱歌,唱和声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依靠这首旋律优美的歌曲,“比基”乐队红了起来。
大概是因为西洋音乐体系对和声的重视,欧美流行音乐中讲究和声的乐队特别多。反观中国,不知是因为国乐不重视和声,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中国流行音乐大多数是依靠歌手单打独斗,很少能听到优美的和声。笔者所能想到的比较注重和声的乐队只有一支女子乐队“黑鸭子”和一支以演唱西北民歌著称的男声乐队“野孩子”。这个问题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再说“比基”乐队。60年代末期,由于一些个人原因,“比基”乐队解散了。也就在这时候,欧美乐坛发生了很大变化,红了10年的摇滚乐渐露颓势,而迪斯科却悄然兴起。说起来,这种节奏单一而又迪斯科音乐的最佳代表“比基”乐队强烈的跳舞音乐起源于黑人和同性恋人群(尤其是男同性恋),他们喜欢去舞厅跳舞,可一来摇滚乐并不适合伴舞,二来没有乐队肯去同性恋舞厅演唱,他们便请来DJ现场打碟。这股完全来自民间的跳舞风潮刚好和当时许多乐迷的心态不谋而合,因为美国的老百姓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好好跳过舞了。《滚石》杂志的一位资深乐评人回忆说,那时他们去参加任何派对,甚至包括本来应该疯狂一下的“鬼节”派对,都是大家戴着面具围坐在一起听唱片。因为摇滚乐是用来“听”的,不是用来跟着“跳”的。当时占领话语权的乐评人也和唱片公司一起力捧那些个性鲜明的“艺术家”,对所有以纯娱乐为目的的音乐嗤之以鼻。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迪斯科火了起来。迪斯科以音乐为主,大都没什么歌词,却在节奏上极尽煽情之能事,为的是把看客们拉进舞池。他们被60年代那些充满哲理的摇滚乐倒了胃口,很容易地被迪斯科俘虏了,整夜整夜地泡在迪斯科舞厅里“醉生梦死”。
早年的迪斯科乐队大都没什么名气,直到“比基”出现,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77年,“比基”乐队出版了一张名为《周末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双唱片,其中的单曲《活着》(Stayin’ Alive)迅速登上榜首。这张唱片以及同名电影的热卖标志着迪斯科时代的第一个超级明星终于闪亮登场了。和以往的迪斯科唱片不同的是,这张唱片中的歌曲都是有歌词的,而且水平还相当不错。他们原本是唱摇滚乐出身,有很扎实的音乐功底,写出来的旋律都非常优美。他们的音乐虽然是模仿黑人的节奏,但他们的演唱却完全是“白”的,带有他们标志性的优美和声。尤其是哥哥巴里的高音,尖细而又温柔,很符合同性恋们的口味,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声音。和两位哥哥比起来,很早就秃头了的莫里斯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但你只要仔细听一听《活着》开始的那段著名的引子,就会明白他的作用真的是不可低估的。
这张唱片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共卖出了4亿张的天文数字,成为历史上卖得最多的电影原声唱片。“比基”的名气达到了最高点。可好景不长,70年代末期,一些摇滚电台和摇滚杂志等媒体发起了一场打击迪斯科的运动。许多著名乐评人纷纷以笔为剑,加入了这场诋毁迪斯科的“歼灭战”。“朋克”音乐也在此时问世,并迅速加入到反迪斯科的阵营中。受此影响,加之迪斯科本身存在的一些毛病,使得这股风靡全世界的音乐风潮在兴旺了短短几年后就销声匿迹了。“比基”出版的那张热门唱片此时却仿佛变成了他们的耻辱柱,把他们永远地和“恶俗”的迪斯科钉在了一起。从此以后,乐队的演唱生涯就再也没有大的起色了。
其实,70年代的这场摇滚和舞曲之争并不是惟一的一次。80年代美国乐坛流行适合慢舞的“节奏和布鲁斯”,于是90年代初期出现了愤世嫉俗的“垃圾乐”,再次把“没有文化”的舞曲痛殴了一顿。如果莫里斯在那个时候去世,有关他的纪念文章恐怕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可是,老百姓们天生喜欢跳舞,跳舞音乐每隔一段就会来一次复兴。代替90年代初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另类”音乐的恰恰是更加机械的电子舞曲热,一大批DJ 成了明星,进舞厅欣赏DJ打碟又成了时髦的事情。“摇滚界”当然又不甘心了,去年年底,《滚石》杂志就迫不及待地宣布摇滚乐又“复兴”了,新一轮竞赛又开始了。
其实两者的竞争并不完全是“伴舞音乐”和“聆听音乐”之间的较量,其背后引申出的有关“艺术”和“娱乐”、“精神”和“肉体”,以及‘低俗“和”高雅“的对立,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今天我们纪念莫里斯·吉布,真应该借此机会想一想:做音乐到底是为了什么?
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的崭新诠释
林逸聪
由DG公司2002年10月出版发行的杜梅(Augustin Dumay)与皮雷斯(Maria Jo?o Pires)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全集新录音最近在中图公司各门市部上市(CD编号471 495-2,3张)。DG公司在1995年之前这套奏鸣曲的黄金销售是梅纽因、肯普夫版(CD编号415 647-2,4张),1995年推出克雷默、阿格里希版(CD编号447058-2,3张)后,1999年推出穆特、奥金斯版(CD编号457 619-2,4张)。而这一版杜梅与皮雷斯的组合已经构成了一个新黄金搭档,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在此前,贝多芬这套奏鸣曲相对权威的版本是格吕米欧与哈斯姬儿1956~1957年的录音(Philips,CD编号442 625-2,5张)和谢霖与海布勒1978~1979年的录音(CD 编号446 521、441 524-2,廉价小双张两套)。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对搭档中的小提琴演奏家都具极美丽的音色,而钢琴演奏家都是弹莫扎特的最佳人选。
杜梅与皮雷斯的合作开始于1991年。1992年他们在DG公司发行第一张室内乐唱片——布拉姆斯的3首小提琴奏鸣曲(CD编号435 800-2);1995年发行第二张室内乐——德彪西、弗兰克的小提琴奏鸣曲及拉威尔的《茨冈》等小品(CD编号445 880-2);1996年又与我国年轻的大提琴演奏家王健组成钢琴三重奏团,录制了第一张三重奏——布拉姆斯的两首三重奏(CD编号447 055-2)。这三张唱片均获得乐评界极高的评介。而在此之前,皮雷斯1989年与DG公司签约后以三年时间录制的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全集(CD编号431760-2,6张)一发行就以崭新的诠释引人关注,当年的《企鹅唱片指南》对她的评介是“在强烈的情感与自然的表达之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杜梅原与法国ERATO,随后是EMI公司签约,转到DG 公司最著名的一个录音是与萨尔茨堡乐团合作的莫扎特第三、四、五小提琴协奏曲(CD编号457 645-2)。
杜梅与皮雷斯合作的重要性在于两个极强烈个性的平衡力。室内乐的魅力在演奏家之间通过乐器对话产生的力与趣味,两个同样个性强烈的人在演奏室内乐的搭档中的平衡常常特别困难。格吕米欧与哈斯姬尔被公认是最好的一对,但格吕米欧与哈斯姬尔比,相对又比较温和。
杜梅与皮雷斯从年龄上,杜梅比皮雷斯小5岁。杜梅的演奏集中了先后三位大师——谢霖、格吕米欧与米尔斯坦的真传,而皮雷斯1970年在贝多芬钢琴比赛中获大奖后,70年代中期曾把家搬到无电、无自来水的农场隐居,自己种庄稼,抚养4个孩子。4年后出山,成为了阿格里希之后最重要的女钢琴家之一。在演奏上两人都极强调情感表达与亮丽音色,在对话上就构成了极强烈碰撞,这种碰撞使奏鸣形态增加了很多可听性。
杜梅与皮雷斯在录完德彪西、弗兰克、拉威尔之后,1997年12月起开始录贝多芬的这套奏鸣曲——从《春天奏鸣曲》开头。有意思的是其录制过程——1997年先录了第五、第七、第八;2001年录了第一与第四;2002年先录第九,再录第二、第十,最后是7月录完第三、第六。与格吕米欧和谢霖版不同的是,杜梅的诠释强调了贝多芬的斗争性,这就强化了这些奏鸣曲的力度,解决了传统诠释类似《春天奏鸣曲》过于抒情、过于甜腻的问题。在这套唱片发行的说明书中有著名乐评人迈克尔·丘奇(Michael Church)对杜梅与皮雷斯的专访。皮雷斯在谈及她对这10首奏鸣曲的理解时,认为前五首涉及外部世界,后五首是对内部世界的内省,第九是“对现实世界的斗争”,第十也就是“进入了超越肉体的精神世界”。也就是说,在第五,对外部世界的情感投入与抒情达到极限之后,是一步步通过内省使自己的精神从肉体中蜕壳的过程。在第六、第七、第八中,充满了内省与肉体重力的挣扎,经过第九,热情已化尽,于是一个明净的世界得以呈现。根据这种解读,杜梅与皮雷斯这样排列这十首奏鸣曲:第一张唱片:第一、第二、第四、第三;第二张唱片;第八、第五、第九;第三张唱片:第十、第六、第七。这三张唱片中要是挑一张,我一定选择第三张——这张唱片中不仅充分展现了第十那种精神超越之后的美丽意境,排在最后的第七也演绎得精彩万分。
这套唱片中值得注意的是杜梅的表现,他对贝多芬的精神气质的把握达到了入木三分,在表现上,就是那种爆发的力度与柔韧的美丽抒情达到了极好的统一。这也是他的《春天》和《克莱采》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以皮雷斯的说法,杜梅是一个对音色表现极为苛刻的人,他会以一个乐句为单位,从意象到思想,探寻最美的声音表述。在两人的合作中,杜梅显然构成了诠释的中心。其实,自从听过他的那张莫扎特协奏曲之后,我已经相信了他的老师米尔斯坦所说的,米尔斯坦预言他是20世纪到21世纪最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