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人民财富的再分配
作者:李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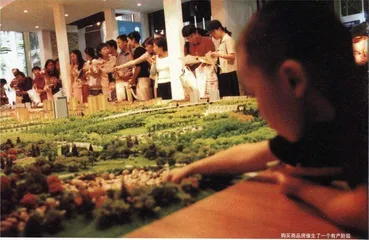
购买商品房催生了一个有产阶层 (罗建 摄)
最大宗的国有资产
“目前国内的房地产总数为38000多家,但真正开发的可能只有几千家,原因是什么?”9月13日,一位在北京有三个项目的地产公司副总接受采访时说:“第一,没有资金;第二,没有地块,土地是房地产产品的最主要原料,没有地,开发商无米下锅,只好干等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们,一半以上的精力是耗在拿地方面的。”今年5月9日,国土资源部发布了第11号令《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7月1日后,所有经营性土地将全部实行拍卖、招标、挂牌;土地有偿使用的制度有了更为详细的实施细则。这位开发商告诉记者,如何拿地以及11号令之后的房价涨跌问题,都成为了地产商们最热门的话题。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今年7月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曾说:“中国人民脚下的土地是价值25万亿元人民币,是最大宗的国有资产。”
“这应该是一个估算,是全部土地包括耕地、建筑用地价值的测算,但毫无疑问的是,土地资产要占到全部国有资产70%以上。”9月12日于振国对记者说。于振国是国土资源部经济研究院经济政策法规研究室副研究员,他向记者解释,“中国土地分为两类所有权,一类是国家所有,一类是农民集体所有。国家直接所有的是城市土地,而对于农民集体土地,法律规定可由政府代表的国家行使征地的权力,但前提是要为了公共利益。因此也可以简化称为中国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
“50年代国务院下面有一个‘内政部’管理国土,尽管刚刚解放,城市里还存在私有土地,但那时就定下了土地的‘三无’性质:无偿、无限期、无流通。”国土资源部经济研究院政策法规室的副主任程绪平说,“此后30年,这个界限一直没有突破。”
土地是资源,但不是资产,更不是资本。“而另一方面,近年来这种国有资产也在大量流失,这也是个天文数字,只要看一下反腐记录,每一名贪官几乎都要牵涉土地和房地产。”
从第一锤到492亿
在地产界人士中,刘佳胜是一个不会被忘记的人物,1987年12月1日,刘佳胜在深圳敲下了中国土地拍卖的第一锤。
现在已经任深圳发展计划局局长的刘佳胜回忆说:“我们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当时最缺的是资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区突破了土地不能买卖的规定,最早尝试了向外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改革,那时仅仅在鹏城罗湖的不到1平方公里的片区里一下就收取了近亿港元的土地使用费。可一说拍卖土地可不得了,有人说这是违反宪法,有人说我们要搞资本主义,甚至说是卖国行为。因为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上确实写着: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为了改革能顺利进行,我们为这个改革之举在《资本论》中去找理论根据。”拍卖会最终如期在深圳会堂举行,共有44家企业参与,一块面积为8588.25平方米的土地以525万元被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购得,平均每平方米地价611.3元,使用期50年。这块地现在盖了东乐花园住宅区。
廖永鉴是当时的副拍卖官,时任市政府基建办综合处副处长,“我们专门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去香港考察观摩他们的土地拍卖。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刘绍钧和梁振英陪着我们看,给我们讲解,就连拍卖用的槌子也是他们从英国定做了送给我们的。1987年,多数香港人对普通话还不熟悉,为了方便参与拍卖的境外人士,我们采取了‘双语’,刘佳胜讲普通话,我说广东话。当时因为担心违宪,土地拍卖趁着全国市长学习班在深圳举办的时间进行,这个想法得到了国家体改委、广东省领导的支持。为了稳妥,我们当时不叫土地拍卖,而叫土地使用权拍卖。我们聚在一起时说:无论成败,我们都会是历史人物——成功了,我们是历史的见证人;失败了,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了。”
当时在北京土地局工作的张瑜,现在已是土地估价师协会的副会长,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深圳的问题是全国性的,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城市规模加速发展,需要扩张和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建厂需要买土地。于是80年代初政府就开始研究土地有偿转让的问题。”作为当时改革的参与者,张瑜告诉记者,最开始的试点是在抚顺展开的,“那是1984、1985年,开始征收土地有偿使用费,但一年下来也就征到两三千万元,缺口很大;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举一个例子,北京70年代末建西直门立交桥花了1个亿,一个城市的建设维护费一年也就几千万,能够上亿就算很了不起了。钱收不上来,因为关系是错位的,国有企业的地由政府划拨的,同样利润也上交,再让它交也交不上来,一平方米也就一毛两毛;另一方面,土地要有偿必须突波《宪法》第10条,从这意义上说,深圳是一个判例法”。
4个月后,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草案,将原来宪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删去,规定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同年还出台的还有《土地管理法》,进一步确认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此后土地改革进入了第一个阶段。”程绪平说,“这一阶段持续了8年。”在这一阶段,土地的出让仍要通过行政审批,中央、省、市、县四级按地块大小拥有不同的决策权。“同时我国实行的是低地价政策,虽然涉及的土地税费有十余种,但主要的三项——土地出让金、土地增值税和土地使用费并不高。”于振国介绍说。但伴随着政策的解冻,房地产泡沫也出现了,“土地可以换钱,政府就加大供给,而且地方政府尤其积极,不能批大的,就50亩、50亩的零打碎敲分期分批,可是来得容易烂得也快,北海、海南的一大批烂尾楼就出现了”。
从1996年开始国家开始做大量调研,认为土地供给过剩,调整政策,1998年修改《土地管理法》,确定了总量控制、占补平衡、用土管理、保护耕地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统一供地,政府成立国土交易中心,统一收购、储备、出让,垄断一级市场,政府按10年一个周期,提出用地规划,按计划供给。”程绪平说,“1998年以后政府逐渐取消协议出让土地的形式,把买卖摆到桌面上。2001年国土资源部启动阳光工程,颁布《划拨用地目录》,给行政划拨划定界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交通、教育、卫生、民航、铁路、水利、电力、邮政、通信、城市基础设施,今年5月颁布11号令,所有经营性的土地都要拍卖、招标、挂牌。”依据记者从国土资源部得到的数据,去年全国各地土地成交价格有492亿元人民币。
行政管理与财产管理
土地是财富之母,李嘉诚在总结自己的地产生涯时说,“地段!地段!地段!”国家作为所有者的代表,在出让土地的同时也进行了一次财富的再分配。
“比如说我们很多城市像摊大饼,无限制地向外扩张,但高楼大厦间还有很多村庄,这就是城中村现象。”程绪平说,原因是什么?我们每年城市的新增用地大都来自农村,因为征用耕地的价格很便宜,依据记者手中的资料,以耕地占用税为例,最高为15元/平方米,最低仅为1元/平方米,而且十余年都没有变过。“耕地开发为高楼,但村子的动迁又没人愿意做,农民的地被廉价征走,但并没有进城当工人,也没有了职业,这就不仅仅是规划的问题了。”
英岛律师事务所律师邓泽敏曾接手大量购房的法律纠纷,他本人也是北京国际商品房博览会法律顾问。“法律规定,购房后60天内,开发商应该将业主材料报政府房屋管理部门备案,然后发房产证,但事实上很少有准时的,我接触的一个案子,竟然拖到了1000天。”邓泽敏说,在购房中业主的财产权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邓泽敏代理的相当一部分案子属于面积纠纷,“这是业主们最关心的问题,有一个案子,业主对面积怀疑,想另请一个测绘队,而我劝他们放弃这种做法,因为如果结论不一,打官司时,也无法断定谁对谁错,而房地产商的测绘数据是不向业主和律师公开的;另一项主要纠纷是环境,去年宣武区有一个项目叫瑞莲家园,计划是5座塔楼,但最后只盖了一座,另外4座转给了另一家开发商,原先说的有7000平方米绿地,最后只剩下3棵树;这样的官司也很难打,因为当初合同都没有签进去,很少有开发商会签,即使是法律规定的《物业管理公约》,因为这为今后物业费涨价留了口子。”邓曾经接受委托,拟了一份6页的《补充协议》去谈判,但最后只写进去了7条,“还是一些废话,比如以上条款要属实,现在房地产还是卖方市场,像204条根本不可能实现。而业主实现了财产权,但这又是缺乏透明的财产权。”
很多开发商也在抱怨,“土地两年未开发,政府就要收回?”“这在美国是使用税收调节的”,于振国说,“而政府目前还没有从对土地的行政管理过渡到财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