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说十年建筑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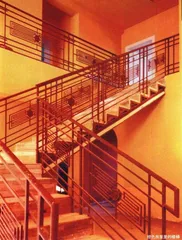
橙色房屋里的楼梯 (任曙林 摄/Fotoe)
建筑理论专家王明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这10年的建筑不能作单体建筑的评论。按凯文·林奇的说法,城市本来就是不断改造的产物,尽管在一定时间内的轮廓可能不变,但细节上的变化从不间断。民用住宅的美更是时间积淀的,而中国10年间巨大的建筑量根本不可能有周密规划的时间量,也没有经历改造的岁月,可能根本还提不上文化意义上的艺术品质。而中国著名住宅建筑专家黄汇先生在1987年曾设计过北京小后仓危房改造工程,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建筑是一件情感的事业。有人说住宅建筑应该放慢一点,我说就得快。这跟人的尊严有关。”
面积
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中心总建筑师赵冠谦在谈到住宅建筑变化时说,这个问题可以参考国家有关建筑设计的规范。他说,70年代就有一个建筑设计的统一标准,1986年国家计委颁布过一个《住宅建筑设计规范》,12年后1999年建设部和国家质量监督局发布了新的《住宅设计规范》,前后对比,其中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在面积上。原来的套间使用面积和单间最小面积标准提高了,而原来一居室45平方米、二居室56平方米、三居室70平方米的最大使用面积标准取消了。
北京华特建筑设计顾问公司副总建筑师孙宗伟说,最大面积的取消当然是因为市场化的结果。规定最大面积完全是因为在福利住房制度下按行政级别、工龄、学历来分配住房,所以要有面积等级与之相应。面积没有了这些约束,完全根据市场需求,很快就膨胀起来,尤其是在北京。南方要理智一些,花哨的东西少一些,比如厅,三十多平方米与使用需求比较接近。北京有六十多平方米的厅,上海就不太会有这样的设计,太冒险,卖不出去。这是不同心态的消费者对建筑的不同影响。清华大学一位建筑师说他看见过有一个单间面积100平方米的厅,二居室面积甚至有190平方米的。但面积也不可能无限扩大,过大的面积形成不了主流市场,那种150~180平方米的套房在90年代末很多,这一部分市场很快会填满,这是国民生产总值规定的。
2001年又有向小面积的回归,像容丰2008等小户型单身公寓。这是结合消费者腰包里的钱而设计的。
户型
50年代的集合式住宅设计中,进门只有一个窄窄的过道,过道两侧是房间的门,80年代就开始把过道加宽,设计为一个小方厅,通常是6~7平方米,并且都是暗的,没有直接采光。赵冠谦先生说,这个厅是根本不能用的,因为四周都是门。再后来就有小明厅。孙宗伟介绍说,90年代初,建筑设计中有一个“小厅大卧”、“大厅小卧”之争,之所以要争论就是因为单位分房制度中的面积限制。在一定面积中,为了让空间丰富一点,合理一点,建筑师就绞尽脑汁在40平方米、60平方米里捣腾。后来就发现有问题了——卧室大没有用,看电视、会客在卧室都不方便,厅曾过渡到10平方米左右。商品房在居室总面积上突破之后,现在厅一般是30~40平方米,开间很多要在4.2米以上,采光面积很充分了,而且餐厅和厅分开了。这也是《住宅设计规范》所要求的。
同样是面积突破之后,对空间的要求就丰富了,最开始是错层,外向空间和卧室等有几步的错落。1995年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李兴钢在设计北京兴涛小区时,设计的错层住宅在当时住宅空间相对简单的市场上得到过从市场到专业界的好评。后来非常时髦的跃层设计也是相对大面积的支持。
赵冠谦先生在解释1999年的《住宅设计规范》时说,这个规范首先要求建筑设计的是考虑居住的舒适度,其中就包括了空间尺度的合理、公私空间的分区,还有户型的可改性。
设备
从当年“卧厅之争”就能看出,厅变成了住宅核心,而后来的核心是厨房、卫生间。孙宗伟认为,这两个空间的变化最大,最本质,新产品最多,技术的提高最大,观念变化最大。有面积卡着的时候,首先卡的就是厨房卫生间,当你的基本面积满足之后,就会发现,整个居室中功能最全的,使用率最高的,最体现生活质量的地方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厨房面积在1999年的规定中是不能小于4平方米,实际上更多的实例是7~8平方米,卫生间在10年前,比较多数的是2平方米,现在最小要达到4平方米。
现在《规范》有要求,厨房要配套、隐蔽、综合,要求所有的管线要综合安置,橱柜后面要留有10公分的空间安置管线。
空调、供暖等设备正处于改变之中,从暖气到集中供暖、分户控温,现在北京的“锋尚”又以“告别空调暖气时代”为卖点,设计了新的控温方式。采光面积的增大,是得益于现在保温材料的更新。北京曾采用外保温层,技术指标不够,在冬天会裂口而失去作用,90年代初就一般采用内保温层,保温效果有限,加上玻璃的质量限制,窗户不可能很大。现在外保温技术基本过关,玻璃可以做双层中空,有很好的隔热性,就可以设计为落地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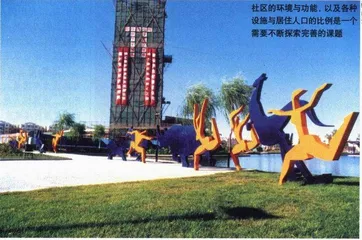
社区的环境与功能,以及各种设施与居住人口的比例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完善的课题 (赵磊 摄)
小区
王明贤说,小区概念是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开始的。那时候二三百户居民组成一个组团,有一个居委会,四五个居委会组成一个小区。真正有对小区建设的要求是从90年代开始。建设部搞过很多计划,从安居工程、康居、小康,到现在绿色生态小区。在全国的建设小区热,建设部每年都有全国性的小区评奖,恩济里小区在1993年是全国金奖,但那时候还只是在满足必要配套设施上,幼儿园、小学、青年公寓、商业、居委会管理、邮局,开门七件事在小区里都能得到解决。
对社区环境,像面积的过分膨胀一样,小区也曾经有中心绿地公园化的过分建设,规模越来越大,设备越来越复杂。孙宗伟在1998年参观过湖州市的一个小区,在中心绿地建了一个好大的水面,甚至可以出租游艇。每到周末时,全城的人都到这里来玩。这样的建设,表面上看起来是绿地休闲面积大了,但却完全失去了小区绿地的功能。现在大家注意到了,这些地面设施首先是为社区而建的,应该以社区内的生活为依据。不仅牵涉到功能,还有费用。草坪,在物业上追加的费用相对要高,也是中看不中用。据统计,一棵成材树的氧的产生量相当于75平方米的草坪,而且树容易养活,后期维护费用低。现在已经有小区在减少草坪,改为种树。
孙宗伟说,原来在有关居住区的规范中,有物业配套、服务半径的要求,比如,幼儿园的服务半径是500米,不能跨越城市道路。由于交通方式的改变,和这些服务设施的经营方式的改变,服务半径的概念也改变了。小区服务的名称曾改为“会所”——这是从香港地区引进的概念——尽量做到功能全,设备好,有酒吧、卡拉OK、游泳池等。而这样的概念现在也在弱化,因为费用。比如游泳池要求温水、循环水,费用要靠来游泳的人支持,仅靠一个小区内游泳的人次支撑不了,那就得靠小区以外的人,那样又失去了小区服务的性质。
李兴钢在1995年开始做兴涛小区时,小区在那时已经形成一种模式,把路、花园设计得曲曲弯弯。李兴钢说,如果说这样的设计有意义,那实际上是在飞机上看到的效果,在居住的尺度上反而失去了环境应有的识别性。整体上的规整才是有效率的,大尺度上越规整越具有识别性,越有效率,跟人的尺度接近的小尺度空间的丰富才是近人的。美国的城市设计名家凯文·林奇认为,城市就是由可认知的符号组成,它的街区、标志物、道路应该容易辨认,才好组成一个完整的形态。
现在小区也是越来越大,李兴钢说,现在5万平方米才能申请为小区,这样的小区沿街面小了,交通受到影响。而且住在一起的人超过了几百户就很难有邻居的经验,尽管在一个社区生活,其实却还是陌生人。
关于小区的概念中,绿色环保是与经济发展、资源利用最密切的紧迫课题。黄汇先生在2000年设计建筑的“北潞春”被评为全国绿色生态小区,建设部给了这个设计规划设计、建筑设计、科技进步多项金奖。她说,这个小区在空气洁净度、绿色屏障、绿地等指标都因为技术投入达到很高的标准。小区所有的水都处理成终水,之所以铺绿地而不种树,是因为地下是空的,全部用来处理小区内部的生活用水。这里原来本是一块洼地,如果填平的话会造成大量土地浪费。她因此采用一层架高的设计,节省了土地,使小区内的垃圾做到了零排放。她强调说,知识投入大不一定费钱,该小区的节能指标比80年代高出50%。
建筑师和社会
建筑师们普遍认为,中国10年的住宅建筑设计主要是功能、技术上的改变,如果说到造型上的改变,基本是市场要求,建筑师的作用其实很有限。
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邵磊说,中国的住宅建筑如果更好地建立文化、政府、消费者等各方面的互动机制,建筑类型、合理性等方面都会有更好改变。他说,在挪威、德国等欧洲国家有很多社会住宅,就是由想买房子的人请建筑师,提出自己的要求,集体合作贷款集资,政府协助来建造。这样的住宅价格上因为减去了开发商的利润而相对降低,而建筑师的设计更有针对性,合理性强,成功率高。选择多,生活质量才高。
而建筑质量的提高是与工业化生产相伴的,在轩盛创业的建筑师黄骅看来,我们现在的土建还是属于手工业。《规范》要求建筑的构件配件要符合标准化、模数化协调标准,就是为了适应建筑的工业化生产。就像生产汽车,流水线决定汽车质量,工人的工作只是拧螺丝。只有工业化生产才能真正提高和保证建筑的质量。
黄骅认为,尽管如此,现在建筑师的作用普遍还不是太大,这从成本上就可以看出来。目前建筑造价一般是每平方米1500元,建筑设计费占造价成本的2%~3%,2%就是30元,这种造价的房子在北京的三环路边上大概卖到每平方米6000元,建筑设计费的30元在这当中只占0.5%。占多大份额,就有多大发言权。决定建筑的是财富、材料、生活、规划,甚至媒体等社会综合力量,所以我们采访的建筑师都很难从建筑本身谈论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