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消亡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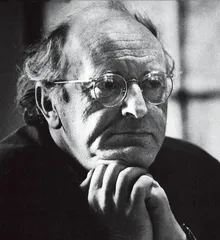 ( 布罗茨基 )
( 布罗茨基 )
无聊的四种类型
科恩说:“过去,人们谈论无聊时就好像是在谈论一种东西、一种物理的对象,而不是一种情绪。它降临到你身上,你避开它,逃离它,或者你驱散它,就像它是一团雾。这并非易事,有时无聊太浓厚了,太沉了。长途旅行时被困在汽车后座,在飞机上没有书或杂志可看,或者在一个正式的社交聚会上坐在一个沉闷的陌生人旁边,驱散无聊的最佳方法是,想象你是在别处,甚至是另一个人,正在做别的事情。
“但突然,这种老实的办法变得不再必要了。由于微博、iPad、黑莓手机、声控导航系统和其他上百种随时随地转移注意力的设备,无聊终于放松了它对我们的控制,那一度能压死人的重量大多成了记忆。连最无聊的相亲也不再无聊了,只要点一下鼠标就能获得自由,立刻改换聊天对象。”
无聊果真如科恩所说,已经消亡了吗?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消亡得最多是诸种无聊中的一种。挪威哲学家拉斯·史文德森著有《无聊的哲学》一书,探讨什么是无聊、何时会感到无聊、为何会感到无聊、为何无聊让人不快、无聊如何让人不快,以及为何意志无法克服无聊的感觉。
拉斯认同马丁·杜勒曼对无聊的分类,他将无聊分为四种:情境性的无聊,当等人的时候、听演讲的时候、坐火车的时候;餍足性的无聊,当人已经厌倦了同一件事情,一切都变得陈腐无趣的时候;存在主义的无聊,当人们感到心里空荡荡,世界毫无色彩的时候;创造性的无聊,当人被迫去做一些全新的事情的时候,这种无聊主要是由结果而非内容来决定的。
 ( 瓦尔特·科恩 )
( 瓦尔特·科恩 )
福楼拜区分了普通的无聊与现代性的无聊,大体上相当于情境性的无聊与存在主义的无聊。在莫拉维亚的小说《沉闷》中,叙述者对比了自己的无聊与父亲的无聊:父亲确实也受到了无聊的折磨,但对他来说,要摆脱这种折磨,只需像快乐的流浪汉那样四处去云游。换句话说,他的无聊是很粗浅的,就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这种无聊只需要新奇的体验便可以减缓。
可见,被科恩认为已经消亡的无聊属于粗浅的、情境性的无聊。而且他所说的人人随时随地都能掏出播放器观看视频,以此打发时间并不能真正地克服最粗浅的无聊。如拉斯所说:“一天看4小时电视的人不一定感觉到或承认无聊,但若非如此,为何他们每天会花掉1/4醒着的时间看电视?休闲提供了大量的剩余时间,显然,几乎没有什么比看电视更能消磨时光的了,晚上长时间地看电视,只可能是为了摆脱多余或难熬的时间。然而,反讽的是,当我们回头反思时,会发现这大把的时光往往是极其空虚的。”
 ( 拉斯·史文德森 )
( 拉斯·史文德森 )
现代人普遍饱受无聊的困扰。无聊是伴随着现代性而突显出来的典型现象,是现代人的专利。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的快乐与愤怒是保持不变的。然而,无聊感看起来却是与日俱增,世界明显变得越来越无聊。拉斯考证说,在英语中,直到18世纪60年代,“无聊”这个词才产生,自那以后,它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教授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写了《无聊:一种心境的文学史》,她以近300页的篇幅论述18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乏味、无聊、厌烦和慵倦的种种场面。德语的“无聊”比英语早出现几十年。法语的“无聊”与意大利语的“无聊”早在13世纪就产生了。
总体说,无聊的先兆指出现在一些小团体中,如贵族与教士阶层,然而,现代性的无聊波及更广,可以说几乎影响到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在《惶然录》里,费尔南多·佩索阿写道:“据说无聊是懒散的人才会染上的病症,它专门侵袭无所事事者。但事实上,这种精神上的不安是更微妙的:它攻击的是天性容易感到乏味的人,对那些工作或装作工作的人也毫不留情。内在生活的圣洁华丽,日常琐事的卑微低劣,这种强烈的对比最让人绝望。无聊如果不是因为游手好闲,将更让人感觉压抑。辛勤度日的人感到无聊,更是世上最坏的事情。无聊的病症并不是因为无事可做而感到乏味,而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痼疾——感到没有事情值得去做。这也意味着要做的事情越多,人越会感觉无聊。”
克尔凯郭尔断言,无聊是万恶之源。这种论断有些夸大其词,但是无聊确实引发了很多罪恶的产生。无聊经常作为一些犯罪的原因而被提出来。对于个人来说,无聊之所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涉及意义的缺失。拉斯强调:“意义必须作为整体来理解,我们在一个总体意义下参与社会,这个总体意义为琐碎的日常生活赋予了价值,它的另一传统名称是文化。许多现代理论家都得出了如下结论:文化已经消失了。”
称颂无聊
科恩在文章的结尾说,如果无聊消亡了,同时我们失去了什么?“也许是创造力。因为当一个人思考问题时,键盘和触摸屏现在取代了想入非非,由于无聊消失了,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去思考问题。”
完全取消无聊或其他一些情绪状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利的。为了试图找出无聊的一些积极因素,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声称,无聊不仅是一些罪恶的根源,同时也是一些罪恶的终结,原因很简单,这些犯罪逐渐变得太无聊了。他以焚烧女巫的行为为例,并且指出,这些现象之所以消失,并不是出于法律、道德或宗教的原因,而仅仅是因为它变得太稀松平常了。
有时候人们会接受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任务,原因很简单:在此过程中能学到一些新东西。从这个角度看,无聊尽管不一定意味着进步,但对人类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一面。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说:“百无聊赖是孵化经验之卵的梦幻之鸟。”
常春藤盟校达特茅斯学院1989年的毕业典礼上,请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做嘉宾。他演讲的题目叫《称颂无聊》。他在演讲中说:“之所以有必要对无聊进行这般详查,是因为它代表了纯粹的、未曾稀释的时间,它闪耀着时间那全部的重复、冗余、单调的光华。”
他也谈到了无聊的普遍性:“创造和革新的另一困境恰恰在于它们的确能赚钱。假若这两者中你能有一技傍身,你很快就会富起来。这看上去似乎不错,但没人比富人更无聊了——这你们大都感同身受吧——因为金钱买来的是时间,而时间循环往复。对贫穷来说,无聊是它的苦难中最残暴的一部分。总之,无论富有抑或贫穷,你们总有一天会被时间的冗余所折磨。”
布罗茨基认为,冗余的时间让人们感到无聊,这是有好处的:“无聊要教给你生活中最宝贵的一课——你们在这里的青青草坪上学不到的一课——关于你们自身之彻底渺小的一课。时间借无聊的声音告诉你们,你是有限的,而且在我看来,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的。这话显然不那么中听,但这种徒劳感、这种甚至存乎于你们那些哪怕是最为纯洁炽烈之行为的渺小感,比起关于那些行为之结果的幻象和相伴而来的自我膨胀却总是要好。因为无聊是时间向你们自己那套世界观的入侵,它从自己的视角打量你们的存在,其最终结果是精确和谦恭。应当注意的是,前者哺育了后者。你们越是知道自己的分量,你们面对同类就越是谦恭和慈悲。”
关于如何对付无聊,布罗茨基提供了一个看起来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当无聊来临,将你自己完全投入无聊,让无聊压榨你,淹没你,直到最深处。总的说来,处理讨嫌之物的规律是,你越快沉底,便越快上浮。无聊是你们开向时间的窗户,一旦这扇窗户被打开了,不要妄图关上它,相反,一把将它推开——要开得大大的。”拉斯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很难照办。因为竭尽全力摆脱无聊是我们的本能,而这个办法完全反其道而行。也许如罗素所说,不要急于去摆脱无聊,“不能忍受无聊的一代人,将是平庸的一代人。不能忍耐无聊,生活就会变成持续的对无聊的逃离”。■ 读书文学无聊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