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刚:没有死亡的剧种,死亡的是文化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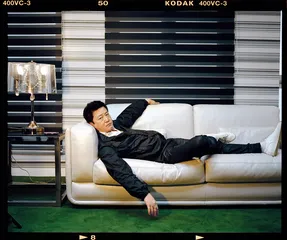 ( 导演赵宝刚 )
( 导演赵宝刚 )
属于导演赵宝刚的关键词有两个:造星,暴脾气。前者毋庸置疑,后者至少在面对记者时,赵宝刚不是这样,一方面他有自己一套强大的逻辑,所有回答都旋绕在那个逻辑里;另一方面他又听任我们摄影记者的摆布,叫躺就躺,叫坐就坐。做过演员的赵宝刚肃然时脸色很“黑”但如果一笑两颊会堆起两个圆团,像小孩子的表情,这种特质让很多演员畏他如虎。
从事电视剧行业30年,自己开办影视投资公司12年,至今编制仍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中国电视剧史上众多辉煌的篇章中都有他的名字,他自己的人生也因这个职业一波三折。
上世纪70年代,16岁的赵宝刚进入北京钢铁厂担任一名翻砂工。“我没有理想,理想就是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他坦白告诉本刊记者,为了离开工厂,他学英语、国画、表演、乐器……因为有人称赞他形象、嗓音均不错,1974年,音乐学院招收“工农兵学员”,厂里不通知他复试。1977年他又报考了音乐学院声乐系,恰好那阵声带出了问题,于是作罢。1978年,准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简章上注明18~22岁,当时他23岁,没敢报名,“但那时候怎么说,就是老实、实诚”。直到1980年进入电影学院在职培训班,艺术大门才算向他打开。
“所谓理想,我认为就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找到自己的偏好,从中获得乐趣了,就觉得自己喜欢了、热爱了。在我看来,年轻的时候干不喜欢的工作,其实是培养你的一种技能,技能越多越有好处。我的价值取向就是干好手头的工作,而当时我在钢厂,不但能干好这个工作,还能干好其他的工作,这就是技能。”他也是比较被动的,职业生涯的每一步,几乎都有不得已然而歪打正着的推动力。
赵宝刚第一步是做演员,《聊斋志异·葛巾》中扮演书生常大用,一集制作费3万元,他说“我印象里拍电视剧就没拿过稿酬”。能找他演就不错了,演完又回到工厂上班。第二部便是《四世同堂》,他的角色是汉奸祈家老二。这么吃重的戏给一个工人演,所有人都在看他的笑话。演完后回到厂里他就甭想出来了,林汝为让他留在了后期做配音,后来又续3个月合同做剧务、剪接,端茶递水外学了很多本事。但当时学习的目的是模糊的,只是惧怕回到工厂。《四世同堂》的创作班底来自北影厂,使得该剧的技术指标高于一般水准。但由于那时只是电视剧起步阶段,赵宝刚认为,从电视语言角度,该剧还是很粗糙的。“遗留在你脑海里的是一种当时观看的感觉,是一种文化氛围记忆了下来。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从鲜嫩走向退化的过程,就像人一样,女孩儿1~19岁都是成长期,20岁之后就进入衰老期,男孩儿1~20岁也是成长期。比如清宫剧、后宫戏,有什么好看的呢?无非一些争权夺势和后宫那点儿烂事。为什么《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能火呢?因为它让皇帝走进社会。”
 ( 电视剧《婚姻保卫战》剧照 )
( 电视剧《婚姻保卫战》剧照 )
他的合同在1984年8月30日到期,如果再解决不了,他就必须到建筑公司上班,多年后赵宝刚记得清楚,林汝为介绍他进入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8月27日拿到了正式调令。当时中心开出“三不”原则:不能演戏,不分房子,不解决家属户口。所以赵宝刚并不是早早立下志愿——成为一个导演,才不去做演员,他被安排做了6年剧务。
“我1985年就成名了,那会儿成名跟现在还不一样,名人少。你想,作为一个知名演员去端茶递烟打杂,现在你去电视制作中心问问,我敢说没人剧务干得有我好。但其实,我就是在这过程中积累经验和人脉。理想就是慢慢形成的一个过程,兴趣是要建立起来的,我不相信怀才不遇,我不相信一个人有着满腹才华,绝顶聪明,结果在这社会上还不能成事儿,那他一定有某一方面的缺陷,比如人缘不好。人缘好,它也是一项技能。”
当剧务期间,他还做其他工作,《便衣警察》的男主角就是他配音,林汝为请他担任该剧副导演,中心领导说:“没门。”他就作为前期副导演去选演员,开拍后再做剧务。“现在好多十几岁的人都想当演员,跑来北京,天天见组,在家坐吃山空、啃老,在我看来,这就是弱智!一个女孩儿在北京的生活成本,一年是6万元,男孩儿是4万~5万元,为什么不去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地,一方面接触社会,获得钱,养活了你自己,另一方面也获得人脉资源的积累。所以大学生一出来先别创业,先好好工作,掌握技能,首先你得养活自己,不能给社会造成负担吧,然后再完成人脉和一点点原始积累,这样寻找创业的机会,才能成事儿。我不相信有才华的人不能成事儿。”
80年代拉赞助已经开始风行,靠着做剧务积攒下的关系,赵宝刚拉来了第一笔赞助,7.5万元,他理想没那么大,只是想当制片主任。报批到当时的生产办公室主任刘沙那里,刘沙说:“我当制片主任,你当导演。”当时中心的副主任郑晓龙和美工冯小刚也想当导演,一部上下集电视剧就有了仨导演,本来把三人名字合为一体,但无论叫郑小刚或是郑宝刚,都会缺一个人,于是名字都上了。那电视剧叫《怯懦的誓言》,赵、冯都有客串,赵宝刚在里面演一个哄骗女文青的画家,台词是当时很时髦的“你可以拒绝我,但不可以拒绝艺术”。赵宝刚得意地说:“这就又要说到人脉了,6年剧务加3年导演,一次就成功。”之后《过把瘾》的全部赞助也是他拉来的,因为立此大功,他也可以充分实施自主权,并在每一次衔接过程中打开社会局面。
其间他在广播学院学习了两年,实习作品就是大名鼎鼎的《渴望》。它被赵宝刚称为“唯一的机会”。初次做室内剧,大家都没有经验,需要在控制室切换,赵宝刚的职务是导播,负责切换的那个人。由于是很多人一起聊剧本,导演鲁晓威拍到20集时出现一些问题,赵宝刚说:“你去弄剧本,我来导。”鲁晓威想了一宿,汇报给领导,同意了。结果,《渴望》拿奖时,大家都去领奖,剩赵宝刚一人在办公室,他心里颇为酸楚,躺下睡着了。
可正是有了《渴望》,才有了《编辑部的故事》让他正式成为导演。由于台词犯忌,在北京台播出6集被叫停,编剧之一的冯小刚写了封信给李瑞环,开头是“瑞环大叔,爱你没商量”。当李瑞环视察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时,冯小刚乍着胆子在会上提起这信,李瑞环评价说:“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非常有特点的一部戏。”性格敏感的赵宝刚说他不喜欢拍《渴望》那种家长里短的故事,虽然那是他最熟悉最擅长的部分,但包饺子生炉子,总会让他回忆起平淡却不向往的胡同生活。他喜欢喜剧,《编辑部的故事》使他掌握了喜剧的分寸感以及镜头的表现力。
从《编辑部的故事》开始,赵宝刚陷入一个魔咒,他上一部戏火了,下一部必然沉寂,《皇城根儿》就是这样。堪称豪华的阵容——王志文、许晴、孙淳、宋佳、葛存壮、尤勇……京味作家陈建功加盟,换来的却是受诟病的剧情。主线两条:老中医的金丹,上门女婿的私生子。原本想把台湾电视剧《情义无价》换成大陆背景,时间设置在新中国成立前,这样架空的一个故事当然没有根基,用一服药做主线也很单薄,故事的悬念设置也有问题。但拍的时候并不觉得,拍完赵宝刚还挺满意,他常讲的一句话是“陶醉在问题中”。说这话时他指的是那些只顾市场不管趣味的人,但也适用于早期的他。
《皇城根儿》的研讨会让他“脸成菜色”,批评之声不断,残酷的批评文章搅乱了他的心态,人们怀疑一个工人是不是称职做导演,从根儿上否定了赵宝刚。《皇城根儿》拍摄于1992年,第二年没有人再找赵宝刚拍戏,他待在家里思考、读理论、看希区柯克、做笔记,决定了今后的方向:在熟悉的生活中做情感戏,这也奠定了他一生的基调。
“我一共拍过20部电视剧,一年一部,我把它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奉命文学’,就是上面要求我们拍的,像《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皇城根儿》;第二个阶段就是为他人,像《过把瘾》、《永不瞑目》这都是;这个时候会有别人来找你拍戏,但也还是一个选择的阶段,坦白说,现在国内大部分导演仍旧处于这个状态。”不管怎样说,《过把瘾》至今仍是赵宝刚最满意的作品之一,也是他的里程碑,“这个故事从时代得来,90年代是感情枯竭的年代,我敢说《过把瘾》是中国第一部纯言情片,它是90年代中期年轻家庭的缩影。以前戏里也有爱情,但不是主要的。我们90%的电视剧,就是一个文化经济的交易过程,它没有考虑过文化传承和文化导演的作用。有些电视剧对文化还有破坏作用。比如后宫戏,它有什么文化?无非是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当然,它可能对人性弱点是有那么个刺激。那么这种戏,你要是讲文化,那么讲出来的都是垃圾,你要是不讲文化,那么就是纯粹针对市场的运作。我是既讲市场又讲文化,我拍电视剧一直都是偏重于文化影响力,同时观察这个社会要什么,我发现无论社会进程到哪一步,爱和美好都是社会所需要的,所以你发现我的作品,都是表达这一话题的,提供给社会爱和美好。我从来不去拍那些个所谓阴暗面的、人性丑恶的,那些个揭旧伤疤血淋淋的东西”。
《过把瘾》中,他有意放弃了一些煽情、刻意的部分,比如方言之死,大雨如注,即便这样,王朔看完后还是不很满意,觉得有点走味,但作为言情剧,《过把瘾》称得上相当克制。在《东边日出西边雨》里,他又拾起了一些被舆论认为不真实的东西。以前这个剧本叫《我本无情》,主人公在街道工厂做灯座,一群工人的恋爱故事。赵宝刚把王志文的身份改为自由职业者,其他人要么是摄影师,要么电台主持人,不见王志文赚钱,就见他生活在树林中的木屋做当代隐士,光线打得极朦胧,瑟瑟黄叶美得不像北京。面对置疑,赵宝刚说:“当时我们拍的那个小洋楼是个实景,不是我搭的景,那个年代那样的建筑就已经存在了。这部戏等于把我认为北京最美的角落都集中在一起了,就是我印象里的北京是这样儿的,现在被糟践成什么样了?十里长街记录着中国的电视文化,各个时代在长安街都能展现,杂乱无章,建筑师是罪人。我们的都市审美取向,红瓦顶、白瓷砖,高档住宅和公厕风格一样,要是我说了算,先把所有生产白瓷砖的厂关闭。”
他在《东边日出西边雨》中的美学追求没有被接受,又坠入了隔一部火一部的怪圈。当赵宝刚成立影视投资公司后,他进入了他口中的第三个阶段:“自主阶段,就是我可以拍我自己喜欢的作品,像《像雾像雨又像风》、《别了,温哥华》、《给我一支烟》、《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到现在这一系列的,可以说我是目前最自由的导演,因为我自己投资自己拍摄自己发行。”无论这些戏收视如何,赚钱与否,他都无怨无悔,因为完全按照个人意图行事。
他要求自己每部戏要提炼出一个主题:“没有会死亡的剧种,死亡的是文化,就看你能不能往剧种里面注入鲜嫩的质感,这点是最重要的。我不怕赔钱,反正是我自己的公司。”这种拍戏方式让公司有一阵很不稳定,在地下碟市走得很火的《给我一支烟》经过反复修改,多年后才得以在电视台播出,那部戏的主角是个“三陪”小姐。他说:“我今天的《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北京青年》这个系列能够出来,就是因为有《给我一支烟》。有了前三四年的积淀,需要有个垫底的片子来尝试自己的观点,对现代文化有强烈的冲击。”很多人讲他超前,赵宝刚说,外国有《茶花女》,中国有《日出》,我们不超前,大大地落后了。
《奋斗》的本子在制片公司手中转过一圈,没有人敢接。“我没看过本子,听到这个名字就决定接,因为这两个字正好有我想表达的精神。那个剧本很一般,石康也说过‘每个字背后都有赵宝刚的影子’,因为都是我手把手地把精神灌输进去的。石康号称他看过3600本书,我说我看过36本书就可以打败他,因为我还有20年的导演经验。”赵宝刚说他想借电视剧颠覆传统观念里的“艰苦奋斗”。“毛主席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为什么要艰苦呢?你是个卖油条的,今天卖出100根,明天卖出101根,用快乐的心情卖出油条,那就是快乐的奋斗。有人说没见陆涛奋斗啊,不可能每个人都当董事长,在我看来,人要学习三个能力:认知社会的能力,认知自我的能力,和社会与人交往的能力。你用5年,积攒人脉,然后有了小小的积蓄,这时候就可以寻找第一个创业的机会,那么找到之后,再用5年,你就可以成功了。世界上有些苦难是不必承受的,在我看来,那些吃了多少多少年苦的,再创业成功的,那都是弱智。”
“为什么提出‘80后’?1979年9月14日,国家颁布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家庭的组成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过去是没有的。我一直很关注家庭的变化,像我接下来这部《婚姻保卫战》讲的是追求妇女解放的现代妇女,追求到什么程度是个头,在追求的同时会丧失什么。剧里面有个妇女解放委员会,简称‘妇解’,那男人就是丈夫那一边还有个‘夫权维护’,这两个组织就形成了一个对立,那么就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厮杀。”过去赵宝刚很排斥家庭伦理剧,有人找他拍《中国式离婚》,一想到要陷入阴郁情绪里几个月,他立刻拒绝了。现在重回婚姻戏,是因为他找到把婚姻拍得好玩而不是苦情的办法。《婚姻保卫战》原先的剧本叫《家庭煮夫》,讲述男人回归家庭,他认为格局太小,必须扩大到两性关系。
“到现在为止,最赚钱的片子应该就是《婚姻保卫战》,卖出了我这个公司有史以来的最高价。”目前,赵宝刚的公司有1个亿资本,“今年就花了357万元买了个剧本,算起来今天光是投资在剧本上面的钱就已经600多万元了。那么,基本上我公司的利润还是保持着每年200万元的递增。王珞丹、文章他们,以前也就5000元一集,现在也都8万~12万元不等了。现在电视剧行业要保住持续期,演员的片酬在涨,剧本的价格也在涨,那么剧本就相当于一个大牌演员,再加上导演,就占到了制作费的1/3。成本一增加,那么你的盈利空间就被压缩,市场越来越混乱,因为大家的审美标准不一样。”
赵宝刚说:“做文化的人还是要讲一点文化。”■
(实习记者童亮对本文亦有贡献)(文 / 孟静) 剧种给我一支烟过把瘾皇城根儿婚姻保卫战爱情电视剧渴望剧情电视剧赵宝刚影视编辑部的故事中国电视剧喜剧电视剧死亡没有电影文化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