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哲学家一样思考
作者:薛巍 ( 尼采
)
( 尼采
)
哲学方法的超时代性
看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人或许都不想成为哲学家,因为历史上有那么多哲学家死于非命: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据说为了证明他是神,跳进爱特拿火山口,被活活地烧焦了;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判饮鸩而死;英国哲学家培根有一次往一只鸡肚子里塞满雪做冷冻实验,结果受寒患了肺炎,因此死去;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被瑞典的克丽斯婷娜女王请求亲临她的宫廷,每天早晨5点给她讲课,不习惯早起、体质孱弱的笛卡儿尔因此病逝。
显然想成为哲学家,必须得相当奋不顾身。那么,能不能不做哲学家,只吸收一些对我们有用的哲学思想呢?英国人尼古拉斯·费恩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他说:“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最不朽的贡献是他们发明或发现的思维工具、方法、进路,这些往往比他们构建,或他们使用这些工具去破除的理论或体系更经久不衰。”
这种观点我们并不陌生,类似于冯友兰先生1957年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具体的东西具有时代性,抽象的东西则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中世纪的一位修士、奥卡姆的威廉认为运动并不存在,它只是物体重新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他的运动理论也许很奇怪,但是他留下了一个今天的哲学家们仍在使用的原则:在寻求一种现象的解释时,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泰勒斯错误地认为,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但在用更少、更简单的东西解释万物的存在时,他引入了还原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科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卢克莱修的空间理论已经被超越了,但他做思想实验的方法今天仍然有用。
费恩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哲学系。他在《尼采的锤子:哲学大师的25种思维工具》一书的25章中介绍了24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因为前期和后期思想方法迥异,一人占了两章)发现或发明的方法:卢克莱修的矛,培根的鸡,休谟的叉子,卢梭的契约,康德的眼镜,边沁的计算……有人戏言,费恩遗漏了苏格拉底的公鸡——他临死前说:“我欠拯救者阿斯克列比亚斯一只公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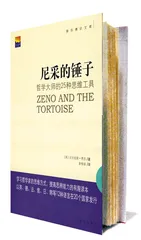 ( 《尼采的锤子:哲学大师的25种思维工具》 )
( 《尼采的锤子:哲学大师的25种思维工具》 )
书中的内容集中于古代和近代,在现代比较有影响的结构主义、现象学方法则不见踪影,但这已经足以让费恩部分实现他的目标:不仅说明伟大哲学家想出了什么,而且演示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从而启发人们像哲学家那样思考。另外,抽象和具体、方法和内容并不是割裂的,领会哲学家们使用的方法也有助于理解他们的哲学思想。
哲学家们普遍使用的方法是思想实验,这一方法的先驱是古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他出生于公元前94年左右,著有《物性论》一书,于公元前55年自杀而死,罗素说,他的自杀“似乎是患有时时发作的神经病——有些人断言是由恋爱的痛苦,或是由春药的意想不到的作用所致”。生前他设计了一个实验,可以不用游遍宇宙就判断出宇宙是不是无限的。假定宇宙是有尽头的,有人到了那儿,投掷出一支长矛,会发生什么?不外乎两种可能:要么长矛继续往前飞,要么被撞回来。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意味着宇宙的边缘之外仍有东西:阻挡长矛前进的物体或它可以继续往前飞的空间。他因此得出结论说,空间是没有界限的,一定是无限的。
费恩解释说,卢克莱修做的是思想实验,它跟科学家们做的实验不同,它发生于头脑之中,而不是实验室里。跟实验室中的实验相同的是,哲学家们的实验也致力于把我们要考察的东西孤立出来。比如,为了研究手机是否会破坏脑细胞,研究者要记住很多别的因素也会造成这种破坏,像自然的衰老、肿瘤或酗酒。如果他们想证明手机是危险或者无害的,他们就要确保这些因素不会在实验过程中造成超出正常情况的破坏。思想实验,或假定情形,也要将其他变量隔绝开,观察当一种因素变化而其他因素不变时会发生什么。
哲学有什么进步?
虽然在书中介绍的24位哲学家中,现代哲学家只有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5位,以分析哲学家为主,但是费恩即使在论述古代哲学家的章节中,也介绍了一些新近的学术成果。第一章写的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开头却是:“1999年夏,康奈尔大学发布了一项旨在说明爱情真的是药物的研究报告。准确地说,它是血液中由多巴胺、苯乙胺、缩宫素混合成的鸡尾酒,会引起我们称之为爱的感情。研究者说,爱情实际上是化学造成的一种精神失常。这种情况会持续到身体形成对有关物质的免疫,通常的长度刚好够人们相遇、交配、抚养婴儿。这种理论很可疑,如果不说它有辱人格的话。康奈尔大学的结论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事物可以归结到其组成部分,可以用更简单的东西来理解复杂、宏观的过程。这一研究也许早晚会被推翻,但这并非还原论第一次打破我们的幻觉。”这证明一些哲学方法是长盛不衰的。
在《休谟的叉子》一章中,费恩上来便介绍了当代哲学家麦金泰尔的思想:“那些自认为很聪明的人无所事事的时候最喜欢揣测别人的性格。一个很流行的神话是,你能够从一个人的着装方式、他们如何握手、他们笑话什么、他们如何应对危机来判断其真实性格。不管是多么普通的举止,都有人说能够从中看出一个人的本性,从他们怎样点烟,到怎样叠手绢。但麦金泰尔说,判断人的性格很难,我们总希望别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同时又使自己让别人无法预测。根据麦金泰尔的理论,每个人对他人来说都是一个谜有更加深层的原因,它危及的远不只是从人的行为推断性格这一做法,它是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东西都只能证明它自身。一个人怎样应对危机只能揭示他如何应对危机,他怎样叠手绢只能反映他如何叠手绢,再也反映不了别的。”
所谓“休谟的叉子”,是指他认为只有两种有效的推理:跟观念之间的关系有关的演绎推理和跟事实有关的经验推理。这一区分被他用来反对归纳推理的有效性。归纳推理不是演绎推理,因为演绎推理是先天的,不包含矛盾,而归纳推理有可能出现反例。归纳推理也不是经验推理,它以经验为基础,但是它假定未来会跟过去一致,由此推断出关于未来的结论。
费恩把“尼采的锤子”算作一种哲学方法有些牵强,它只是一种修辞。尼采在《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作哲学思考》的引言中写道:“这本小书是一个伟大的战争宣言,至于对偶像的探听底细,这次涉及的不是时代的偶像,而是永恒的偶像。用锤子进行敲打,以便听到,他们用脚站立的基础如何不稳,发出的声音多么沉闷、空洞。”
他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做了清晰的阐述,并努力打破维特根斯坦这位偶像,提出维特根斯坦没有认识到有些思想是存在于语言之前的。“维特根斯坦意识到理性止于行动,解释必须止步于描述,不然它将没完没了。当我们做决定时,我们的选择依据的是我们没有选择的因素。当我们为我们的行动提供理由时,我们不能用一个理由来解释另一个理由,又用下一个理由来解释这个理由,如此以至无穷。早晚我们要停留于一个就是如此或反映我们的存在方式的东西。但我们的语言游戏并非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随意。语言是帮助我们生存的东西,帮助我们成功地行动。它们不断演进,适应我们的需求,考虑另一种游戏是否能够更有效地满足这些需求是有意义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关心这些外在于语言的需要。哲学史的存在表明,我们确实关心这些需要,所以有理由提出,我们的一部分是先于语言的。这是一个经验问题,维特根斯坦会说它不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但是在维特根斯坦1951年去世之后,哲学家们仍取得了进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这种限制当真。”■
(文 / 薛巍) 一样哲学史哲学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