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随笔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几年前,内地出过村上龙《接近无限透明的蓝》,不过那本书错字连篇,装帧粗陋,长了一副盗版模样。
今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购进村上龙14部作品的版权,威震日本书业几十年的重量级畅销作家终于体面地来到中国。
第一本上市的是他的随笔集《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李重民译)。随笔不是村上龙的王牌,他自称“很久以前就不喜欢随笔,也有写不好的原因”。他最不喜欢随笔中的说教,“爱说教的人,除了伟大的宗教家以外,全都是在胡说八道。看看历史就一目了然,伟大的宗教家一个世纪还不到一人,所以也可以说,剩下的说教家伙全都是破烂货”。村上龙的随笔绝无说教,他的特色是态度嚣张,词锋凌厉,想法放肆。他是小说家,不是学者。不是学者就不必为自己的说法寻找妥帖的根据,小说家的败笔是缺乏想象力。村上龙的想象力足够。
他敢说:“在我的心里,毕生在研究的主题已经有五个。那便是‘死刑’、‘战争’、‘独裁者’、‘宗教’、‘性爱’。关于‘战争与性爱’,已经有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好的性爱可以防止战争’。请不要想得太复杂,因为这很单纯。不会做口交的可怜的读者,至少有过一次感觉‘真好啊’而想感谢上帝的性爱经历吧。是情欲和浪漫融合在一起的,最融洽的性爱。经历过那样刻骨铭心的性爱以后,抚摩着女人的头发,还会进行战争吗?”“毕生研究”的主题一句话说干净。这样的研究会把学问家逼死。
传说本·拉登年轻时交过一个美国女朋友,因为他尘根偏短而饱受美国女友的侮辱。和美国女友分手后,他便疯狂地仇恨美国,成了反美的恐怖大王。这个传说可以从反面支持村上龙——“好的性爱可以防止战争”,倒过来说,“恶劣的性爱可以导致战争”。没准儿这个传说就是村上龙编的段子。

“冒犯”是村上龙随笔的动机。他的乐趣大概就在刺激读者,奚落读者,最好让他们火冒三丈,把他的书撕烂。下面这段话,得罪的恐怕不仅仅是日本女人:“女人要获得智慧,我觉得是一种堕落。我希望女人是愚笨的。智慧如此繁复的事,就交给男人去做吧。只要有爱。智慧、教养、常识、道义都不需要。”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出版日本当代通俗小说上,一向很有心得。不过以往似乎很不在乎营销,许多好书甫一问世就沉没在书海里。今年有了点新气象,《日本畅销小说选》(朱川凑人等著,祝子平译,2006年1月第1版)收集的并不是新小说,但簇新包装,明显对市场有所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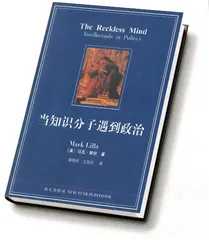
马克·里拉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学问偏重当代欧洲思想和欧洲思想家。几年前他在《纽约书评》杂志评点欧洲六大思想人物,后来将评点扩展成书,再后来——去年年底——这本书有了中译本,书名是《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这里说到的“政治”其实就是暴政。作者选评六大人物:海德格尔、施密特、本雅明、科耶夫、福科、德里达,因为他们身上有污点,曾经与暴政合作或鼓吹暴政。里拉想告诉读者这些污点人物在哪里失足。这些人里有些污名早已坐实,比如海德格尔和施密特,有些作者未必选对,比如本雅明,他是法西斯主义暴政下的牺牲者,怎么能把他和纳粹的同党同路人算进一卦?
即便这本书有大大小小的毛病,它还是本很好玩、很好读的书。以作者的看法,这些思想大师都翻落粪坑,臭味难免。大师蒙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欧洲思想传统里本来就有敌视多元社会的基因;有人说理性精神里的宗教狂热也会导向暴政噩梦;有人说知识分子的自负让自己迷失;有人说文化民族主义(在德国尤其明显)让他们向暴君输诚。作者并不完全同意这些解释。里拉的说明是:人生而欲爱(eros),“爱向往的是善,但也会在无意间沦为‘恶’的帮凶。因为爱会引致癫狂,引致一种难以控制的幸福的癫狂,无论这种爱是对一个人的爱还是对一个观念的爱”。“对智慧的爱也会引致癫狂。”为观念之爱控制、缺乏节制、谦逊、平衡感的思想精英会“头脑发昏”(Reckless Mind,英文原书名),成为暴政之友,暴君之仆。
电影导演李安为他的新片《断臂山》做宣传时,用了一句特别俗套的话:“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臂山。”套用李安的句式,里拉的书可以概括为“每个人(每个思想家)心里都有一个暴君”,问题是不能让这个暴君冲决而出。
被里拉反复抨击的“癫狂”、“清除一切节制的激情”,有一个最恰当的中文译名——“激情燃烧”。■
(文 / 小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