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的报复
作者:薛巍 ( 这幅插画描绘了蒙古大军的战船大部沉没、海面上漂浮着船只残片和死尸的场景 )
( 这幅插画描绘了蒙古大军的战船大部沉没、海面上漂浮着船只残片和死尸的场景 )
伊拉克战争的教训
前《大西洋月刊》记者、美国地缘政治分析师罗伯特·卡普兰曾经是支持伊拉克战争的鹰派,现在他改变了观点,承认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灾难,说伊拉克战争教会了美国的新保守派要注意地形。他在《地理的报复》一书中说,正在为被淘汰、优雅地退场的美国需要综合地考虑历史、地理和战略。主张人道主义干预的人认为,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自由主义的制度,不管是特立尼达的小岛,还是寒冷辽阔的加拿大;不管是多雨的苏格兰,还是阳关灿烂的意大利;不管是热带,还是沙漠。卡普兰对这种简单的想法做了检讨。
美国地理学家迪伯利在《地理为何前所未有地重要》一书中说:“这是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急遽的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对全球秩序真实、严重的威胁。中国的经济在崛起,恐怖主义加剧了,欧洲的统一在退步,非洲的前景恶化了,而美国人的地理知识却很不充分。地理知识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地理学洞见对解决地缘政治问题非常关键,解决文化和经济问题也需要地理知识。”
《纽约客》的戈普尼克说,这两部关于地理学的著作表明,地理历史在复兴:“最开始我们写的历史是种族史——我们部落的神话在这里,你们的在那里,我们的部落得到了上帝的赐福,你们没有。接下来的历史是面孔的历史——领袖和将军、法老和埃米尔的活动、国王和教皇以及苏丹们之间的冲突,历史记录的主要是谁最先戴上皇冠,之后又是谁接过皇冠。接着是位置的历史——某个城市或国家的人一起比其中的某个人创造了更宏大的历史,现代史大多是位置的历史。现代位置历史产生了许多杰作,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写的是中世纪法国一个村庄的故事。在位置历史之外和背后是空间的历史:地形和领土的历史,平原、河流和港口决定了某个地方的社会生活史。”
诗歌形式的空间史非常古老,弥尔顿在《欢乐颂与沉思颂》中吟唱过“仙女,甜蜜的自由”,认为瑞士比法国更自由是有缘由的;孟德斯鸠认为南方人比较淡漠,山地人轻快、桀骜不驯。近年来,空间史有了数据和细节这两种武器,有了解释一切的冲动。
 ( 罗伯特·卡普兰 )
( 罗伯特·卡普兰 )
卡普兰想改造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的地理学,尤其是英国历史学家哈·麦金德的理论。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回顾了欧洲过去1000年的历史,他用地理解释所有的事情。他认为,欧洲的心脏地带不是西欧,而是欧亚平原,历史真正的决定者如匈奴穿过平原往前进军。在历史上,意大利人溃逃,西欧基本挡住了蒙古的游牧部落,因此得以繁荣。最终在这场斗争中幸存的人将控制“世界岛”,即欧亚大陆和非洲。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则认为,最重要的是用庞大的海军控制海洋,要用装了大炮的船对付骑兵手中的弯刀。马汉对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二战”中的指挥方式产生了影响。
地理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在俄国打败了拿破仑,在印度打败了亚历山大,在撒哈拉打败了拉冈比西斯,在越南打败了美国。遥远的距离和陌生的环境妨碍了后勤保障,使部队筋疲力尽,它击沉了西班牙的舰队,帮日本挡住了蒙古人。但地理也并非不可战胜。科尔特斯征召当地叛国者征服了墨西哥,莫卧儿国皇帝阿克巴用炸药瓦解了印度北方的要塞。卡普兰看到了绝对的空间决定论的危险性。为了使地理决定论与时俱进,卡普兰对历史做了全球性的梳理。他提出,地理的力量推动了欧洲从干燥的地中海沿岸向更富饶的北方推进,北方的黄土更肥沃、矿物质含量更高。他说:“在中世纪,光辉灿烂的帝国都在地中海沿岸,文艺复兴便首先在中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繁荣起来。但更冷的大西洋开启了全球海运航线,最终战胜了封闭的地中海沿岸。葡萄牙和西班牙由于其突出的半岛位置,率先成为大西洋贸易的受益者,它们启蒙运动之前的社会由于距离北非太近,最终在海洋竞争中败给了荷兰、法国和英国。就像神圣罗马帝国承接了罗马帝国,在现代,北欧承接了南欧,加洛林王朝主导了欧洲联盟。”王朝的兴盛都被归因于地理位置,这就出现了自相矛盾:一会儿占据突出的半岛位置是优势,接着就成了劣势;一直处于前启蒙时期,是因为离北非太近了。俄国出现专制政府是因为其寒冷的气候和辽阔的面积,照此说来,加拿大应该也会抵制自由的制度,走向专制,所以只能把加拿大人说成隐秘的南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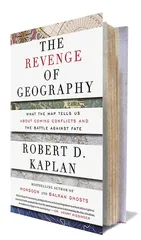 ( 著作《地理的报复》 )
( 著作《地理的报复》 )
文化VS地理
卡普兰的地理概念过于老派,他把地理看作空间、地形和纬度的综合,过去50年间环境科学的进步把他甩在了后面。生态学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历史学家们意识到,战争、经济、国家和文明的命运都受到了全球气候变化、地区气候动荡、地震、物种灭绝等因素的影响,人类与生态系统是不可分离的,只有以环境、土壤和大海为背景才能理解我们自身。卡普兰声称,中国是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而巴西不是,因为中国跟美国处于大致类似的纬度。亚里士多德或斯特雷波或许会认为这一因素是决定性的,但现代地理学者不会关注它。他没有研究地理与文化的关系,地理学者往往把地理视为一种文化建构:有的文化认为海洋是一种障碍,其他文化则认为海洋蕴含着机会;有的文化认为高山令人贫困,有的文化则认为高山是安全屏障;有的文化喜欢寒冷,有的文化喜欢炎热。
戈普尼克说,要认识到,观念跟地理一样推动着历史。1914年的德国如果继续做一个生产效率高、工业化的国家,它就会获胜。但德国需要在非洲获得殖民地,拥有强大的海军这种观念完全是头脑发热。明智的大臣应该对德国皇帝说,就走现在的道路,凭借德国人的生产效率和纪律性,德国就会成为欧洲强国。但德国皇帝和他的将军们痴迷于海军力量的神话、世界岛的威胁和对领土的需求,在西线实施了4年毫无意义的屠杀。还有19世纪英国和俄国的冲突,其实沙皇在巴黎的舞会上跳不了吉格舞,他也没能力拿走印度,但英国人就是放心不下俄国长期的威胁。
近来还出现了另一种版本的空间史,可以称之为制图学转向,其特点是,认为虽然地理很重要,但只有通过我们绘制的地图才能看出地理的重要性。边界落在哪里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还取决于人们认为它应该在哪里。我们只有通过地图才能知道地球的形状,而那些地图是根据权力关系制作的,国家的形状都是争斗的结果,国家间的边境线就像是伤疤,它们是看得见的暴力史。从这种观点中诞生了一个新的领域,叫边境研究,这个学科有它自己的期刊和协会。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边界入门》一书。边界学者认为,划定边界主要是现代社会的举动,古代的帝国和中世纪的国家的边界是流动、灵活的,甚至根本没有,人们居住在灰色地带。民族国家的兴起使边界成为控制公民身心不可或缺的官僚工具。这些边界的划定有的很随意,但它们造就了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
学者在论证地理的决定意义时,总是会谈到技术。现代的生产是对技术的应用,而技术是对地理的否认:坚持认为地球上的限度不是我们的生活的限度。火车、电报或者火箭、网络瓦解了空间和地形,飞机能带我们越过高山,炸弹能令边界消失。新的机器能够更快地杀死更多人,思想权威被疯子扭曲和误用后,给杀戮者那样做的理由,所以阿伦特等人对大屠杀的论述把意识形态和技术置于核心位置。新的空间史有一个优点,它能让历史学家变得更加谦卑。美国的繁荣看上去是美德与干劲的结果,但地理学转向告诉人们,那主要是因为美国人拥有大片肥沃的土地、远离世界岛的居所,一侧跟炎热的大陆接壤,另一侧跟一个寒冷的大陆接壤。但地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观念的力量更强大。戈普尼克写道:“曾经,沿河而下的维京人令欧洲人胆寒,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却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方,发生变化的显然不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地形。英国确实是一个岛,但挡住了希特勒的有水,还有意志。英国从帮派伦理向民主的转变不能用与世隔绝来解释,英国的暴政终结了,但英国并没有往大陆漂移。好的观念一样重要,谈话比高山和季风更能决定我们的生活。”(文 / 薛巍) 地理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