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英国人在中国的美食体验
作者:harps 文/孙欣
文/孙欣
初到成都
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单纯写写中国的生活经验并不能结集成书。在上海时,我听见在公司工作的外国人说话时英语中夹杂着中文词汇。一个英国朋友的弟弟不会西班牙语,但是会点中文,于是在马德里走进一间中国人经营的杂货店问路,结果成功了。中国不再是遥远的异乡,中文也不再是天然的文化屏障。屏障外面的人会好奇屏障里面是什么样,屏障里面的人,尤其是那些文化人,更好奇的则是屏障外面的人会把他们写成什么样、想成什么样。
扶霞·邓洛普来到中国的时候,是个年轻的留学生。留学生的视角和职业记者的视角是很不同的。后者可能太了解身后的世界想要他们看到什么,反而忘记了看得更仔细一点。留学生则是一些还没有完全学会生活的年轻人,一个猛子扎进异乡生活里,因此必须学习这种新生活每一寸每一丝的肌理。很多本地人习以为常的事情,留学生看在眼里却有别样的新奇,值得兴致勃勃地探究一番并记录下来。
中国人对留学生的“异乡记”并不陌生,自80年代起,不少中国人就通过报纸杂志上留学生的文章来了解外国尤其是美国的生活。现在这类文章逐渐被走马观花的游记攻略代替,可能是因为留学生实在不稀罕了,堆山塞海没有几个能写的;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视角的民主化——大量浅薄的、浮光掠影的观察堆积起来,其中自有可用的信息。但是另一个方向的“异乡记”,如《鱼翅与花椒》这样,将中国作为异乡的讲述对象,数量还是很少的。把这种“异乡记”再度引入中国,让中国读者看到外国留学生讲述给本国人看的中国是什么样,就更少了,何况这本书文笔生动活泼,视角宽广细腻,每一页还都带有美味、缠绵、伤感等复杂情绪,让人欣喜之余也几乎心碎。
扶霞的中国留学记始于90年代的成都。那时候留学生只有120来人。去掉四十几个抱团排外的日本人,其他的“意大利人、法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埃塞俄比亚人、波兰人、约旦人、老挝人、加纳人、德国人、丹麦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就彼此热热闹闹地生活在一起”。这正是典型的学生生活的开头: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认识一群彼此陌生的人,从此开始一段半集体生活。学生生活最美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你的生活也丰富了我的生活,今夜的散场是为了明朝的相逢。没有特别难以启齿的爱和恨,也没有特别要保护的隐私。
学生之间的盟约是逃学,在成都这么一个充满着懒洋洋的魅力的城市,留学生们很快就忘记了他们之前制订的学习计划,改成学太极、麻将、气功,外加美食烹饪、聊天喝茶。扶霞学会了早起动动鼻子就找到军屯锅盔当早饭。她承认,她本来就没打算认真学习。她在填写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申请表时,心里想的是成都的美餐——鱼香茄子、豆瓣酱红烧鱼、火爆腰花和花椒的香味。这绝不是说生于牛津上了剑桥的她不是个好学生。她在四川找到了人生里真正想要学习的东西,就迅速沉浸其中,会写一串烹饪术语和罕有菌类的中文,学会了切骨牌片牛舌片、筷子条二粗丝,但还是不会写“银行账户”“网球”。
成都着实没有让扶霞失望。上世纪90年代,什么对外国人来说都是新鲜的,尤其是对扶霞这样一个有着清明双眼和清醒头脑,态度诚实又不失谦恭的女孩子来说。扶霞的父母在牛津市做教师,天南地北的学生都拿她家当过旅馆,她早早就对文化多元尤其是食物的多元有着切身体会,而且颇为自矜自己在食物上勇于尝试的精神。要知道即使是在欧洲,英国人也是有名的口味狭窄、脾胃虚弱。扶霞看到了四川大学老师们在菜市场的日常生活,自行车的筐袋包篮装满了生姜青菜、现杀活鱼。她看到各色各样的小贩,眯眯眼的太婆坐在辣椒花椒袋中间,相貌挺帅可是总是在打盹的卖花人,她也看到午饭后整个城市都陷入了午睡状态:农妇们趴在南瓜和茄子上,卖鱼的靠着墙,办公室里的人们躺在沙发上四仰八叉,像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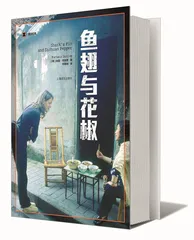 写出中国社会的复杂
写出中国社会的复杂
忠实的场景人物记述是好文学的基本功,可惜很多作者都早忘记了这一点,只写他们想看到的东西,结果是一本书从第三页起就无可避免地流入套路。扶霞写出来的成都、重庆、甘肃农村、福建山区,既诚实又详细,中国人读起来也仿佛呼吸到了那里的空气。
扶霞写得最好的当然是食物的质地和味道。她不是一个天然带着文化优越感走世界的英国人。她老实地承认热闹的菜市场那些残忍的杀生场面给她带来的震撼和厌恶,也老实地承认她接下来就被食物征服了(比如兔脑壳儿的下巴上的肉多么厚实丰富,眼睛那块儿多么柔软,脑髓多么顺滑绵密)。扶霞早已了解大型食品工业和超市将血腥和浪费掩藏起来的伪善,所以她并不认为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顾客和商贩之间明明白白的杀生和厨房里精工细做一点材料都不浪费的烹饪是一种野蛮的行径。她的“川菜第一师”冯锐做的炒鸡杂,新鲜从鸡肚子里剖出来,每样都精心处理过,用慷慨的蒜苗和豆瓣酱来炒。一同上桌的还有一条从缸中活物变成桌上佳肴的鱼,蒸得热腾腾,撒了姜末和葱花。更不用说还有这样生动的描写,不是特意写来讨好猎奇的英国读者的,也不为讨好只爱听夸中国好的中国读者,这是她写给自己的热气腾腾美味氤氲的四川大学那一年,用文字把热闹的风味十足的青春重新呈现出来,所以才特别好看。
《鱼翅与花椒》最精彩的部分是前半部的四川大学的留学生活和烹饪学校的学习。到了后半部,扶霞带着研究采访任务,短时间访问某些省份,仓促成文,就显出了记者写文走马观花的不足。有趣的是,她自己也分明知道这一点而且不甚掩饰。因为美好四川的先入为主,她把自己定位为成都人,并且很可爱地将后来去的地方与四川比较,觉得都不如四川人“一言一行中总有微妙的体贴”。好在她的走马观花并不只是记记菜谱,而且是通过一场场旅行描绘出了中国社会的复杂纠缠和巨大差异。她写到了福建郊区粗俗的农家乐,秘密烹制保护动物的小餐馆,追求珍异食材显示权力和财富的商人和官员,还有生活不宽裕,并不怎么吃得起肉的当地农民。最可贵的是,她是以一种“局内人”的角度写的,也就是说她不是处处把自己择清的观察者,而是体验者。她坦白的笔触详细写了那些有意无意的罪孽带给人的新奇体验,中产阶级对山水田园的天真想象,以及发现罪孽如何环环相扣缚住千万人时的内疚。像这样真诚的文化体验是极少见的。大多数写作者对异国体验不是全盘贬低,就是全面吹捧,目的不外是为证明自己正确或为自己开脱。
扶霞真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女孩子。唯其勇敢,所以真诚。毕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不敢吃甚至不敢看兔脑壳儿呢。 美食扶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