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虽圣人起,不易吾言
作者:苗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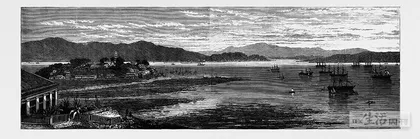 福州阳岐村严复祖居中,有一台留声机,游客可以听到大清国歌。歌词是严复写的,“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1911年9月28日,严复日记中记录,“到禁卫军公所,定国乐”。这里说的“国乐”就是“国歌”,清廷从康熙和乾隆使用的皇室颂歌中选了几个调子,请严复填上歌词。10月9日,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内准备炸药时发生意外,总督瑞澂开始全城搜捕,严复在日记中写下,“夜九点,瑞澂拿革党三十五人”。第二天,辛亥年十月十日,严复日记写下四个字,“武昌失守”。11月9日,严复离开北京,到了天津,“数日风声极恶,江浙皆告独立,资政院民选议员鸟兽散”。11月12日,接到资政院回京开会的函告,同时收到家乡福建的消息,福建总督松寿自尽。11月13日,严复到北京领了三份薪水,分别来自学部、海军部和币制局,同一天,“袁项城到京”。
福州阳岐村严复祖居中,有一台留声机,游客可以听到大清国歌。歌词是严复写的,“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1911年9月28日,严复日记中记录,“到禁卫军公所,定国乐”。这里说的“国乐”就是“国歌”,清廷从康熙和乾隆使用的皇室颂歌中选了几个调子,请严复填上歌词。10月9日,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内准备炸药时发生意外,总督瑞澂开始全城搜捕,严复在日记中写下,“夜九点,瑞澂拿革党三十五人”。第二天,辛亥年十月十日,严复日记写下四个字,“武昌失守”。11月9日,严复离开北京,到了天津,“数日风声极恶,江浙皆告独立,资政院民选议员鸟兽散”。11月12日,接到资政院回京开会的函告,同时收到家乡福建的消息,福建总督松寿自尽。11月13日,严复到北京领了三份薪水,分别来自学部、海军部和币制局,同一天,“袁项城到京”。人到迟暮之年,会有光阴加速的感觉。辛亥之前的严复,总把自己寄托在翻译中,辛亥之后,严复没有出版新的译著,他在历史中留下几处身影。其中之一是辛亥年12月12日,由汉口渡江到武昌。他三天前登上火车从北京赴武汉,列车上是袁世凯指定的各省代表,12月11日到汉口,满城都是战火迹象,北洋军纵火焚烧汉口,严复说,“民心大抵指向革军”。渡江之后,严复与唐绍仪等人一同到了青山织呢厂,严复见到了北洋水师学堂轮管科1888届毕业生黎元洪,师生相见,“感动之深,至于流涕”。黎元洪现在是湖北军政府都督。南北双方代表磋商,严复记录下革命党的底线:极端反对君主立宪辅以袁世凯内阁,但若实行共和,袁世凯可以当大总统。 另一处身影是在1915年8月12日夜,杨度拜访严复在北京西城旧刑部街的寓所。严复的学生记录了此次会面的要点,杨度一见面就问严复,是否看过古德诺写的《共和与君主论》。古德诺是美国人,行政法学权威,担任袁世凯的法律顾问,他著有一份《古德诺备忘录》,也就是杨度所说的《共和与君主论》。这篇文章的英文原稿已经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作者销毁了,中文版开头是,“一个国家,必定有其确定的国体,而国体的形成,通常并不是其国民选择的结果”。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君主制更好,共和制无法解决继承人的问题,君主制能更好地解决继承人问题,因此更稳定。杨度问严复,“公视今日政治,何如前清,共和果足以使中国臻于富强兴盛乎?”严复说:“此一时殊未易答。辛亥改革之倾,清室曾颁布宪法信条十九,誓以勿渝。仆于其时,主张定虚君之制,使如吾言,清室怵于王统之垂绝幸续,十九信条,必将守之惟谨,不敢或背,而君臣之义,未全堕地。内外百官,犹有所慑。国事之坏,当不至如今日之甚,或得如英国国君端拱无为而臻于上理,未可知也。”杨度说,我们打算成立一个筹安会,讨论的问题就是君主优于共和,古德诺的文章已经开了个头,我们要继续研究下去,您的名望大,请您做发起人。严复回答,今日人君威严,既成覆水,贸然复旧,徒益乱耳。国家大事,宁如弈棋,一误岂容再误。这一晚交谈的主题就是杨度劝严复作为发起人加入筹安会,严复并未应允。
另一处身影是在1915年8月12日夜,杨度拜访严复在北京西城旧刑部街的寓所。严复的学生记录了此次会面的要点,杨度一见面就问严复,是否看过古德诺写的《共和与君主论》。古德诺是美国人,行政法学权威,担任袁世凯的法律顾问,他著有一份《古德诺备忘录》,也就是杨度所说的《共和与君主论》。这篇文章的英文原稿已经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作者销毁了,中文版开头是,“一个国家,必定有其确定的国体,而国体的形成,通常并不是其国民选择的结果”。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君主制更好,共和制无法解决继承人的问题,君主制能更好地解决继承人问题,因此更稳定。杨度问严复,“公视今日政治,何如前清,共和果足以使中国臻于富强兴盛乎?”严复说:“此一时殊未易答。辛亥改革之倾,清室曾颁布宪法信条十九,誓以勿渝。仆于其时,主张定虚君之制,使如吾言,清室怵于王统之垂绝幸续,十九信条,必将守之惟谨,不敢或背,而君臣之义,未全堕地。内外百官,犹有所慑。国事之坏,当不至如今日之甚,或得如英国国君端拱无为而臻于上理,未可知也。”杨度说,我们打算成立一个筹安会,讨论的问题就是君主优于共和,古德诺的文章已经开了个头,我们要继续研究下去,您的名望大,请您做发起人。严复回答,今日人君威严,既成覆水,贸然复旧,徒益乱耳。国家大事,宁如弈棋,一误岂容再误。这一晚交谈的主题就是杨度劝严复作为发起人加入筹安会,严复并未应允。
1915年9月3日,梁启超在《京报》发表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总统府内史夏寿田拿来一张四万元的支票,请严复写文章反击梁启超。由此可以猜想,古德诺写那篇备忘录,应该也拿到不少稿费。严复没写反击文章,随后他收到20余封恐吓信。严复去见夏寿田,说:“外间以生死相恫吓,非吾所介意。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脱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
严复所说的“病患相迫”并非虚言,1916年1月5日,北京下雪,严复日记记载:“内廷召宴,未赴。凌晨一点半,卧中咳甚,服药膏一匙。早晨通便一次。中午十二点半,右腿注射四分之一克盐酸吗啡。午后四点一刻,左腿注射硫酸吗啡四分之一克。凌晨一点半,左臂注射硫酸吗啡四分之一克。”1月7日,阴雪,“内廷召见,未去”。严复日记用英文记录:“卧中服药膏一匙。一点,右腿注射硫酸吗啡1/4克。身体轻微着凉。约九点,盐酸吗啡1/4克。凌晨一点,再次饮酒两杯。”
严复1916年的日记,记录的是抽大烟、服药、打吗啡。6月6日,袁世凯去世这一天,严复日记写的是:“上午十点,右腹注射硫酸吗啡14毫升。正午,右腿注射硫酸吗啡14毫升。午后三点半,左腿注射硫酸吗啡14毫升。午后五点,左腹注射硫酸吗啡14毫升。晚七点十分,右腹注射硫酸吗啡14毫升。晚十点半,左腿注射硫酸吗啡14毫升。午夜十二点一刻,左腿注射硫酸吗啡14毫升。午夜两点二十,右腿注射硫酸吗啡14毫升。”类似的记录如复制粘贴一样,持续两年,在严复日记中占据100页左右,1917年7月1日,严复用中文写下“宣统复辟”。而后用英文记录——上午八点,右腹注射硫酸吗啡16毫升,左腹注射硫酸吗啡16毫升。午后一点三刻,右腹注射硫酸吗啡16毫升。午后四点三刻,左腹注射硫酸吗啡16毫升。晚八点,右腹注射硫酸吗啡16毫升。晚九点五十五,左腹注射硫酸吗啡16毫升。在严复日记这100页的注射记录中,偶尔可见几个汉字,“见冯总统”“段祺瑞内阁全体辞职”“段内阁复活”等等。
人文学者可以讨论严复晚年的思想是否变得保守,医学史家会讲用吗啡戒除鸦片是否有效、吗啡与身体及病痛的关系,但思想与身体与病痛与吗啡之间有何关系,就不是正经的学术题目了。晚年的严复还会写文章做演讲,还会写信。马勇所编辑的《严复书信集》中,收录了严复给熊纯如的109封信,从1912年3月持续至1921年10月临终前,熊纯如这位晚辈是严复最重要的倾诉对象。严复在信中谈论国内时局,谈论“一战”及俄国革命,臧否人物,吐槽梁启超孙文蔡元培等人。他谈日本的野心,“东方日本,其野心与德国同”,“其学校诸生毕业后,游于人国者,皆侦探也”。也谈国民性,“吾国人看事最为肤浅,且处处不是感情之奴隶,即是金钱之傀儡,其程度真无足言也”。他看不上白话文运动,“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
1916年9月22日,严复给熊纯如的信中有这样一段——“平生于《庄子》累读不厌,因其说理,语语打破后壁,往往至今不能出其范围。其言曰: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仁义也,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我查阅陈鼓应先生《庄子今注今译》,陈先生的译文是:“名器是天下共用的,不可以多取。仁义是先王的旅舍,只可以停留一宿而不可以久居,形迹昭彰便多责难。”严复的感悟是什么呢?他说:“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矣。”严复提到庄子讲的一个小故事,叫“儒者以诗礼发冢”,这个故事讲两个儒者一边背诵儒家经典,一边盗墓。参考陈鼓应的译文,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两个儒生盗墓,大儒问小儒,天快亮了,你干得怎么样了?小儒回答说,尸身的裤子短袄还没有脱下,他口中含着一个珠子。大儒就背了一段《诗经》,“青青的麦穗,生在山坡上,生不施舍人,死了何必要含着珠子”。接着发出指令说,抓住他的鬓发,按着他的胡须,用铁锤敲他的下巴,慢慢分开他的两颊,不要损坏了口中的珠子。这个故事是说儒者可以满口仁义道德,同时干坏事。严复由此议论,“罗兰夫人亦云,自由,自由,几多罪恶假汝而行。甚至爱国二字,其于今世最为神圣矣。然英儒约翰孙有言,爱国二字有时为穷凶极恶之铁炮台。”严复引用的这两句名言,前一句来自法国大革命时期上了断头台的罗兰夫人。第二句是约翰逊的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在这一段的结尾,严复总结,可知谈理论人,一入死法,便无是处。 庄子说不要囿于理念,严复说不要执着于平等、自由和博爱这些理论。他年轻所向往的欧洲及文明变了样子。1918年7月,他给熊纯如的信中说,“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8月的另一封信中说:“不佞垂老,亲见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作为一个熟读古书之人,严复肯定知道,两千年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但他依然相信,礼之用,和为贵,所谓礼,远于禽兽之事矣,所谓和,依乎天理之事也。
庄子说不要囿于理念,严复说不要执着于平等、自由和博爱这些理论。他年轻所向往的欧洲及文明变了样子。1918年7月,他给熊纯如的信中说,“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8月的另一封信中说:“不佞垂老,亲见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作为一个熟读古书之人,严复肯定知道,两千年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但他依然相信,礼之用,和为贵,所谓礼,远于禽兽之事矣,所谓和,依乎天理之事也。
100年过去了,文明这个概念有什么变化?2015年,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主编的论文集《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出版,刘禾教授在序言中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问世之时,进步主义历史观已大行其道,社会阶段论和文明等级论已成常识。黑格尔将进步主义的历史观推向顶峰,明确把中国放在“半文明半蒙昧”的阶段。刘禾说:“文明论于今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潜移默化,更加深入人心。在中国,它作为一个内在的历史逻辑,依然在推动着今天的发展主义;在欧美国家,它更是屡屡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导火索。历史证明,当这种文明论以政治无意识的方式运作时,尤其危险,值得全人类深刻警惕。长期以来,从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的时代直到全球化的21世纪,脱胎于文明等级论的东西文明比较论述,始终在引导着中国人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认识,而隐藏在这种比较认知背后的政治无意识却经常被人忽略。因此,对文明论和殖民史学的检讨在今天变得十分必要,甚至成为当务之急。对于当代人文学者来说,反省过去几百年的知识结构,探索新的历史意识的前景,当是责无旁贷。”
《世界秩序和文明等级》是一本涉及文明概念的全球史研究的论文集。梁展在其中发表了一篇分析康有为的文章,开头说:“数百年以来,文明作为受到人们自觉承认和接受的规范,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标准。然而从历史上来看,文明论却与欧洲启蒙运动揭橥的理性主义话语一样,构成了西方世界为发动残酷的殖民战争,以及强迫进行殖民贸易而构建起来的特殊的而非普遍和客观的知识形态。文明与野蛮,以及强调不同文明形态具有高下之分的文明等级论思想,是上述知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它们逐渐形成了在今天依然是出自西方世界的地理学、民族学、人种学、政治学、法学的政治无意识。”我问梁展老师:“文明等级论有什么错吗?难道西方的文明不先进?”梁展老师回答我:“我们反对文明等级论,不是反对文明和启蒙本身,而是反对片面地为文明制造一个西方标准。西方人制定标准,确定谁是野蛮国家,是非文明国家,他们站立在道德高位上,以此作为对这些国家实行暴力、实行压迫和剥削的理由,这是要反对的。林奈曾把人类细分为不同类别,这种排序分级系统导致了种族分类的出现,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把人类分为12个等级物种和36个种族,由非洲和大洋洲的土著人所构成的原始人列位最低,中国倒数第二。康有为的种族改良思想就是建立在文明等级论上的。”
我接着问,那么自由呢?严复所看到的自由,在我们这里就没有土壤吗?梁老师回答:“严复不会抽象地讲义理,他会把自由这个概念放在中西方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看待,比如他说美国为什么会实行自由主义制度,是因为没有外敌,而中国的情况不同,列强环绕,没有强人政治,国家必然分崩离析。他说一个国家实行君主制也好,共和制也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问题,而是基于它的地缘政治,在那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实现民主自由,他早就看出来了这一点。今天这个结论依然有效,并不是某一种制度绝对适合某一个国家。纯粹的理念是害人的。”
难道自由不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吗?我问清华大学的宋念申教授。宋老师说:“民主和自由这些概念是高蹈的,但是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它一点儿都不普世,比如对妇女,比如对有色人种,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边缘人群,比如说在殖民地,你对土著人是实行了自由还是友爱?还是代议制政府?都没有。你对美洲的原住民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把着眼点稍微放大一点,就会发现民主自由是一个抽象的原则,抽象原则一定要落地,看你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去怎么实践。英国工业革命之后,那一套制度非常好,但它同时是一个全球性的扩张性的殖民国家,它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实行了这套制度?根本就没有,在其他地方它实施了剥削和掠夺,从而有能力去在它的国内实行那种要靠非常强的物质基础来奠定的那一套理念。自由主义的理念作为价值观非常好,但是它的实践是非常残酷的。我们看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可能没有一个单一的价值能够统摄所有的时间,一个理念,恰恰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在特定的语境中成为一个值得大家尊崇的东西,一旦脱离这个语境,好像它就不是太适合。自由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它的意味是不一样的,你说我们所有人都追求自由,可是一个吃不饱肚子的雇农,他所要求的自由和你在城里喝着咖啡享受空调的一个中产阶级,构想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宋教授的这段回答,让我想起以赛亚·柏林文章中的一段:“埃及农夫对衣物或医疗的需要的确超过个人自由,但是他今天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自由,以及他明天有可能需要的更大程度的自由,并不是某种特别属于他的自由,而是与教授、艺术家和百万富翁相同的那种自由。”这可能是抽象地讨论义理,历史常识告诉我,1882年英国开始对埃及的统治,1956年英国人撤出苏伊士运河,正如严复所说,“以国之独立自主不受强大者牵掣干涉为自由。此义传之甚古。”
宋念申推荐给我一本书A Turn to Empire,芝加哥大学教授珍妮弗·皮茨的著作,这本书我只读了开头部分,简而言之,在18世纪最后几年,亚当·斯密、伯克、狄德罗和康德这样的思想家,对欧洲的帝国都是采批判态度的,但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托克维尔和约翰·穆勒,都支持欧洲对全球统治的扩张和巩固,这些自由主义者要证明欧洲统治的合理性。A Turn to Empire,讨论的是当自由主义与世界相遇会发生什么,为什么自由主义者会放弃细致入微的分析,而让位于野蛮与文明这种粗糙的二分法。如果自由主义建立在对人类尊严和平等的承诺之上,那么如此多的自由主义者对帝国的支持就成了一个需要解释的理论问题。
1920年10月29日上午十一点,一艘客船驶入闽江,在福建马尾罗星塔前抛锚停下,严复回到家乡,两天前他从上海登船,几年来,他肺病时时发作,这次回乡避冬。他在船上能看见罗星塔,塔高31米,七层八角,明朝时罗星塔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重要航标。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马尾创办福州船政,船厂和学堂就在罗星塔下。1867年1月,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堂中开设的课程有英语、几何、代数、三角、光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等,入学三个月后就有甄别考试,不合格者劝退,而后每个季度考试,成绩一等获10元奖励,二等不奖不罚,三等记惰一次,连续三次三等,开除。1920年10月29日回到家乡,罗星塔下,严复也许会想到他年少苦读的日子。10月30日,他搬入郎官巷的宅子,那是福建督军李厚基为他安排的住处。
如今,每个到三坊七巷旅游的游客,可能都会去郎官巷严复故居看看。大堂上有一副对联,写的是“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对联是严复的笔迹,落款处是严复的名字。严复非常喜欢以这16个字自况,1906年6月20日,郑孝胥日记中记载:“严又陵来,请为书,‘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1907年7月14日,严复请英敛之为他写了同样一副对联。此后这副对联总是被严复挂在书房里。郎官巷故居还有一副对联,“起傍梅花读周易,就书新竹记离骚”,读中国古书,能获得一种带着点儿虚无的沉静。另有一副对联,写的是“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1921年6月10日,严复给熊纯如信中说:“还乡后,坐卧一小楼舍,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哲学、历史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在三坊七巷中还有一座严复翰墨馆,展示严复的书法作品,绝大多数是临帖,临苏轼《洞庭春色赋》、临王羲之《十七帖》、临智永《千字文》,由此可见当年做一个读书人,所需要的文化资本要怎样一点点练习。翰墨馆入口处也贴着那副“有王者兴”对联,是郑孝胥的笔迹。如果1906年和1907年,严复对自己的著述有“不易吾言”的自信,那应该指的是他的译著,而不是他后来宣扬孔教的演讲。
由三坊七巷到马尾罗星塔公园及船政博物馆,大约20公里。由三坊七巷到阳岐村,大约10公里。阳岐是一个安静的小村子,严复祖居“大夫第”及严氏宗祠都在村中,由祖居,沿小溪走一公里,就到了严复墓地。严复在世时就建了墓地,并手书“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碑文,“侯官”是福州的旧称,“清”这个字,表明严复自认大清子民。墓碑前方的横石上刻着“惟适之安”四个大字。严复在1921年10月27日去世,和原配王夫人合葬于此,原来墓地只有200平方米,1988年动工扩建修葺。现在墓地四周正在建严复公园,规划面积是132亩,已完成100亩。夕阳下,公园草坪上空无一人。墓地前挂着一幅红底白字的横幅,上书“纪念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70周年”,看上去像是刚为他举办了一次生日聚会,客人已然散去。严复自觉病深之时曾手书遗嘱,其中说道,“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等等。这是他对后世的嘱托。死亡会增加一些词语的分量,让一些老生常谈变得意味深长。但稍具理性的人都知道,词语的力量来自明澈的思想和清晰的逻辑,来自美妙修辞,也来自作者不易吾言的自信。
必须要补充一段,《论自由》很大程度上是一位伟大女性写的,穆勒的妻子哈里特。穆勒说:“此书表达的整个思想方式显然全是她的,但是我彻底受到此种思想方式的浸染。”哈里特于1858年去世,穆勒在妻子的墓地边上买了处房子,在那里完善《论自由》,好像他们还在一起工作一样。穆勒认定《论自由》会比他的其他著作传世更久,因为它阐发了真理。他在自传中说:“社会平等和代表公众舆论的政府将不可避免会出现,这会把整齐划一的言论和行动的枷锁套在人类的头上。有一天,某个特殊的理论体系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依照这种理论体系组织起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通过教育把它的新信条灌输给下一代。到那时《论自由》的教导将显示出它最大的价值。” 严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