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柱楼诗》案(下)
作者:卜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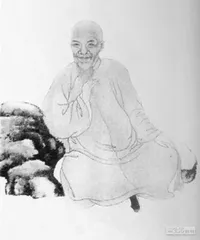 乾隆帝阅读萨载奏折后,即对高晋严旨问责,对江宁布政使陶易更不客气,说他对案件一味塞责,“徐食田贿嘱县书改查出为呈送,其鬼蜮伎俩甚为可恶,陶易亦并未究出,率行转禀”(《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五三六),命明白回奏。陶易出身寒素,乾隆九年中举,历任知县、知州、知府,四十年十月应高晋之请由广东调任江安粮道,不到半年即破格擢升布政使。此人廉正干练,也敢于为民请命,深得总督高晋器重,也赢得了皇上的青睐,没想到卷入一件钦办大案。
乾隆帝阅读萨载奏折后,即对高晋严旨问责,对江宁布政使陶易更不客气,说他对案件一味塞责,“徐食田贿嘱县书改查出为呈送,其鬼蜮伎俩甚为可恶,陶易亦并未究出,率行转禀”(《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五三六),命明白回奏。陶易出身寒素,乾隆九年中举,历任知县、知州、知府,四十年十月应高晋之请由广东调任江安粮道,不到半年即破格擢升布政使。此人廉正干练,也敢于为民请命,深得总督高晋器重,也赢得了皇上的青睐,没想到卷入一件钦办大案。乾隆将陶易作为此案关键人物,在于徐述夔的书经东台县、扬州府、江宁书局层层上报,蔡嘉树也曾亲往布政使呈状,卷宗上的批语为:“搜罗书籍,原为明末国初有著作悖谬、诗章讽刺实有违碍者,俱应收解奏缴。至讲论经传文章,发为歌吟篇什,如只有字句失检并无悖逆实迹者,将首举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著有明条,倘系蔡嘉树挟嫌妄行指摘,希图倾陷,亦即严讯拟议。”这段话虽为陆琰所拟,但经陶易圈阅行文,也就难逃罪责。倒是扬州知府谢启昆觉得倾向性太明显,做了一些删改。即便如此,也触发了弘历的敏感神经,不光怀疑陶易有意宽纵,还要求追究是否受了贿赂,有没有倒填日期的行为,下旨将东台知县涂跃龙、扬州府知府谢启昆、江宁布政使陶易革职,解往京师审讯。稍后,已到外地谋职的陆琰以及江宁书局的委员杂役被悉数解京。而在此之前,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徐食书,校书的徐首髮、沈成濯,以及原告蔡嘉树等人已被押解进京,远在新疆的举人毛澄因题跋被抓捕审问,解送京师。为防止串供,此类押解都要错开日期,可谓不计成本。
《一柱楼诗》愈演愈烈。先被查出的是“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表达诗人的出尘之思,意为期望明天展翅高飞,直到上天之仙界。而乾隆指出:“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五五八)此乃皇上的定性,有谁敢发表异议呢?而在此之前,乾隆还有独到的发现——
至阅伊同校书之徐首髮、沈成濯二名,更堪骇异。该二犯一以首髮为名,一以成濯为名,四字合看,明是取义《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诋毁本朝薙发之制,其为逆党显然,实为可恶。已交刑部存记,俟该二犯解到时,严加刑讯,务令供吐实情。此等鬼蜮伎俩,岂能逃朕之洞鉴?萨载、杨魁何以竟为其瞒过?即或伊二人文义平常,岂幕友中全无一人看出者,何皆为之隐讳不言乎?(《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五四二)
没有谴责刘墉,大约是念在其奏报之功,予以从宽放过。而刘学政看到此谕,心中必会有几分愧疚。不能不佩服乾隆的目力,如此一挖掘,的确有些诡异呢。徐沈乃徐述夔入室弟子,列名校对,萨载、杨魁接旨后即命将二人抄家逮捕,讯明徐首髮原名徐首發,沈成濯原名沈埙,述夔为改今名。萨、杨自认“愚昧疏漏”,表示“诚如圣明洞鉴,均非从幼取定,该犯等俱已解京审究,其与逆犯校书命名悖逆之处一经严讯自必水落石出,尽吐真情”。徐沈解京后果然悉数招供,承认老师确实说过“如今剃了头就是濯濯的意思”,并说“本朝剃头不如明朝不剃头好看”;徐首髮还交代后来改回徐首發,《一柱楼诗》刻成时见仍用“首髮”,曾要徐怀祖改正,怀祖不听。
乾隆对改名的判断得以证实,而认定徐食田并非自首、东台县倒填日期、各级官府有意包庇,则纯属臆想。此事后经刑部反复研讯,经手书吏金长五供称“徐食田实系四月初六、十六两次缴书,初次批语已示贴署前照墙,众所共见……委无受贿倒提日月情事”;原告蔡嘉树也承认“只系心疑,并无行贿凭据,不敢固执”。此事不再追究,办案重点放在对陶易渎职的审讯上。可怜这位65岁的老臣被革职抄家,解送途中突患重症,抵京即连续受审,仅十日就死于狱中。陶易留下两份供词,其一曰:“我原系一穷举人,仰蒙皇上天恩,由州县府道超擢藩司,父祖皆蒙荣耀,而于徐述夔又毫无瓜葛,乃于此等逆诗呈告到我手里,我不详细看出,立时详报督抚严行查办,转偏着徐述夔一边批发,这实是我的罪孽,竟与徐述夔无异,万死不足以蔽辜,只求皇上把我立正典刑,以彰国宪。”(《清代文字狱档》,625页)不敢辩解,不敢推卸,连委屈也不敢有一丝流露,读来令人恻然。素称英察的弘历曾对他亲自讯问,这些话也很像是陶易当面所说,大皇帝应能察知其一片志诚、满腹冤屈,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两案的处置有宽有严:为殷宝山《岫亭集》评点作序的殷一柱、赵学礼、尹发萃皆得以释放回籍,江宁书局委员保定纬、沈澜也以按旧规办事被开释,官复原职;对徐案则从严。徐述夔与徐怀祖虽皆亡故,“仍照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受命驰驿前往,会同江苏巡抚杨魁赶至东台县,监督施行,事后奏报:
奴才等即于初十日会同先诣新河口焦家林徐述夔厝棺之地拆砖启棺,细加查验,徐述夔尸身僵而未化,原戴纬帽及所穿袍褂颜色旧坏,尚未毁烂,并验明棺上标写“戊午科举人拣选知县徐孝文赓雅之柩”等字样,当即遵旨监视将该犯徐述夔之尸枭去首级,凌迟锉碎撒弃旷野,仍悬示东台县城。一面复至栟茶场,将徐怀祖住宅内尸棺移置野地开棺查验,该逆犯徐怀祖尸身亦未消化,原戴纬帽所穿袍褂均未朽烂,遂将其尸一律凌迟锉碎撒弃,即枭示于栟茶场地方……(《清代文字狱档》补辑,阿弥达等奏徐述夔等锉尸枭示情形者,658页)
乾隆朝文字狱颇有一些定为锉尸枭首,此则为极少见的现场描述,竟戮及逝者,残忍冷酷,泯绝人性。
食田兄弟和徐首髪、沈成濯,以及陆琰本拟斩立决,经皇上开恩减为斩监候;为《一柱楼诗》题跋的毛澄,定为杖一百、流三千里。陶易虽死于狱中,仍被定性为“故纵大逆之罪”,那些被抄没的家产应不会发还。而东台知县涂跃龙和扬州知府谢启昆,均以错谬怠玩、办理不认真革职流放。启昆出身翰林,亦吏事练达,乾隆岂不知其冤枉,几年后复加起用。对于那个敲诈不成就告状的蔡嘉树,弘历已指明“非实知尊君亲上”,刑部奏稿中也说他控告书吏受贿倒填日期之事不实,且早就知道徐书中存在逆词,直到争地才挟嫌告发,但毕竟举发了一桩逆书案,应予释放。有谁会记得这样的一个小人儒呢?有,徐氏后裔会长期衔恨,故乡人也会将之钉在耻辱柱上。
徐述夔案开了一个恶例,有着极大的示范作用,告讦迭起,各省督抚亦不得不按照此一模式吹求挑剔,纷纷上报。湖南巡抚李湖奏称查出明人所著《荣木堂集》等,江西巡抚郝硕奏称查出明季进士黎元宽《进贤堂集》等,均有违碍语,搞得皇上不胜烦扰,又不便叫停,恰好江苏巡抚杨魁拿着一个“赦”字整事,被臭骂一顿,算是表明了拒绝扩大化的态度。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