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写下的《塔斯马尼亚》
作者:蒲实 在处女作《质数的孤独》中,意大利小说家保罗·乔尔达诺——他同时也是一位粒子物理学博士——以深刻又复杂的孪生质数为比喻,微妙地描写了两个少年成长过程中彼此的情感,童年的创伤在青春时代投下深重的孤独与恐惧,他们不断靠近却又彼此分离,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距离和障碍。
在处女作《质数的孤独》中,意大利小说家保罗·乔尔达诺——他同时也是一位粒子物理学博士——以深刻又复杂的孪生质数为比喻,微妙地描写了两个少年成长过程中彼此的情感,童年的创伤在青春时代投下深重的孤独与恐惧,他们不断靠近却又彼此分离,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距离和障碍。这本小说之后,乔尔达诺一直在连续创作,翻译成中文的小说有《人体》(2013)、《黑与银》(2016)、《逆光之夏》(2021)和《新冠时代的我们》(2021)。近些年来,他的创作越来越多对现实和公共议题的关注,在保持着小说家笔触私密的“小”的同时,他的写作所依托的背景则变得更加开阔宏大。不久前,他曾两次前往乌克兰,与一些乌克兰人建立了个人关系。他察觉到,在新的军事冲突的现实之下,如何将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同时在另一些地方发生的暴力事件联系在一起成了一个难题。当他回到意大利,他感到罗马的安宁其实是以令人烦恼的时代噪音为背景的,而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生活在这种现实里。
他的新作《塔斯马尼亚》是在疫情期间开始创作的。这一次,叙述者“我”与妻子诺伦佐的关系展开于几乎难以理解和把握的大背景之上: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袭击,还有核爆炸,它们的共同点是事件一旦发生就具有毁灭性,而事件何时何地发生则具有随机性。这些宏大的不确定性将如何在微观层面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乔尔达诺告诉我,这部小说的构思与他在写作时对现实的感知有莫大联系。疫情的发生和结束留给他的是一个废墟的图景,而他感到自己是幸存者的一员。在这个废墟景象中,“房间已经不存在,你不会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而只是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而你不知道下一个地方是什么”。
这本小说中的角色没有出场,他们只是突然出现,然后突然消失,然后在某个地点又回来。这与乔尔达诺所体验的日常现实很相似,“生活里的各种朋友进进出出,今天见的一位朋友,可能再一次见面就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他们的生活可能会发生一些变故,比如离婚或换工作,你试图追溯和理解过去那几个月中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生活也不再有什么连续性,“现在我们在谈论我的新小说,半个小时后我可能已在飞机上阅读一篇关于战争暴力的文章,然后我可能掏出手机给未婚妻打电话,谈论我们今天新买的洗碗机。这是非常混杂的日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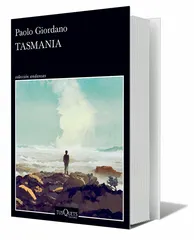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十多年前写《质数的孤独》的时候,你的写作是非常个人化和私人化的。是什么促使你后来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写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十多年前写《质数的孤独》的时候,你的写作是非常个人化和私人化的。是什么促使你后来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写小说?
保罗·乔尔达诺:也许与我的年龄增长和逐渐变老有关。有一句老话,大意是:你首先关心自己,然后才能关心世界;你得先拯救自己,再用这股能量来拯救世界。写《质数的孤独》时,我只有25岁,那时我想要安顿自己的生活,处理与自己、与家庭相关的问题,处理作为一个存在于世界上的个体的恐惧——充满着那本书的正是这种恐惧。时间一年年过去,这些事情逐渐从我的生命中淡化了,这些问题似乎也终结了。我的兴趣发生了转移,不再执着于“我”,而开始向外走,关心“我”之外的世界,对外部世界也越来越感兴趣。我的写作追随着这条路径。
三联生活周刊:在《塔斯马尼亚》一书中,你专门写到了武汉这座城市。气象学家发现,“在中国的武汉地区,降雨量出现下降,即便考虑到由于厄尔尼诺季节变化所引起的波动,这也是绝对不成比例的下降”。写这部分故事是在哪一年?
保罗·乔尔达诺:我在疫情暴发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开始写这本书,也就是2021年的9月,武汉在那时已经因为令人悲伤的原因而受到全世界关注了。但在书中,“武汉”出现的时间是2017年,一张气象地图使得一位气象学家注意到了这座城市,它还完全是地理意义上的。小说中的气象学家可以通过气象云图瞥见未来,从而经历了“前创伤体验”,心理学家称之为“卡桑德拉综合征”。疫情之后,创伤变为了现实。2020年3月我写了一篇关于流行病的短论文,那时新冠刚刚蔓延至意大利。此后一年中,我一直在写流行病,然后我决定回到写小说,开始写《塔斯马尼亚》。那时的我已不再想谈关于流行病和它所造成的创伤,而想谈谈在这一切发生之前的那几年。“创伤前应激障碍”在很多领域其实都存在着,当我们能够预知即将发生的灾难,而灾难尚未变为现实之前,我们一直都生活在“前创伤”中,这种现象在气候变化、战争、核武器这些领域都普遍存在;就像在这本书之后的时间里,在乌克兰、中东地区发生了事实上的军事冲突,而对这些的创伤在军事冲突在现实中发生之前就已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前创伤”的感觉是在什么时候击中你的?
保罗·乔尔达诺:对我来说是从气候变化领域开始的。这也是《塔斯马尼亚》这本书的起点:在学习了很多关于气候变化危机的知识之后,你对世界的观察和认识中多了很多使你感到威胁和恐惧的东西。下雪的时候你会开始想,这会不会是我看到的最后一场雪?当你身处大自然时,你会开始怀疑这是否是我能看到的最后的自然状态?这种威胁和恐惧的感觉会慢慢渗透进你的头脑。而这种感觉变为现实的事件是欧洲的恐怖主义袭击,小说也开始于巴黎的一场恐怖主义事件。作为一个在罗马和巴黎之间频繁往返的欧洲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恐怖主义就在那里,我和我周围朋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随机地身处恐怖主义发生的现场,而我们没有身处现场,也纯粹是概率问题。每个人都存在着在某个时刻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可能随时意外地受伤或失去生命。我原本相信,虽然很多事情在变得更加困难,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但在巴黎遭到恐怖袭击那一刻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在任何一个瞬间,糟糕的事情都可能突然发生。
三联生活周刊:在《塔斯马尼亚》中,你试图将日常化的个体经验与气候变化、战争、恐怖袭击这些事情缝合起来,寻找和丈量着事件发生之时日常生活与大背景之间间歇的缝隙。比如,一个被处以极刑的人需要7秒钟死亡;再比如,一个人瞬间陷入一场恐怖事件的那一秒钟。这是否是这部小说写作的动力之一?
保罗·乔尔达诺:当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疫情还未完全结束,欧洲已经放开了许多,但还有一些小限制,而中国还未结束封闭状态——那时危险真实地入侵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早在疫情还未发生的2017年,一些怪异的事情对我来说就已经发生了。当时“伊斯兰国”的一些视频在网上流传,而观看这些视频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体验:一方面,中世纪的东西竟然回到了现代文明的生活中,另一方面,每个观看视频的人在大受震撼之后,放下手机又回到了自己的正常生活,转身便将视频里的内容忘掉,一切照常进行,这反而使得这些中世纪的东西成为渗透进我们日常生活的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但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怪异的、不自然的。在《塔斯马尼亚》这部小说中,我想真正重新返回具体的事件,去探索那里到底有什么,去发掘这些事件发生时我们到底如何感受,去丈量这些暴力事件究竟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我们之后的生活,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审视过这些事件的后果。过去两年中,疫情和战争的图像充满了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它们究竟如何影响了我们的个体生活?我深信我们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坚强和有能力,相反,我们很脆弱;我也深信我们不会那么容易地就“翻篇”和“继续前进”,有一些事情已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病态或厌倦。我决定慢下来,回头,回到那些几年内已快速从媒体和公众讨论中淡出的事件中去,去理解不远的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时间来沉淀对过去的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战争、疫情……这些宏大的背景事件如何在微观上改变了个体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保罗·乔尔达诺:在你问这个问题之前,我的思考方式其实是反向的,我会先观察身边的关系,然后再看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但也许也可以先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再回到自己的小生活里看看是否有映射。作为一个欧洲人,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受到这种威胁。发生在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也深刻影响了我,它让我看到历史的某种黑暗的东西再次复活了。那种威胁感不是让我感到切身的不安全,而是让我意识到,我在20岁、30岁时所熟悉的那个世界的理念很有可能已不复存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受到一种乐观主义的哺育,那就是进步将促进世界和平,而且这种进步与和平会不断扩散。在我的青年时代,与外部世界产生联系是宿命般的事,我们甚至会集会来反对全球化。今天我们的命运似乎走向了另一个反面:世界在坍缩,美国在坍缩,其他地方都在坍缩,甚至欧洲各国都在各自坍缩;与10年前相比,我与任何一个地方的距离都在变得越来越远。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毫无预料的。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中出现了一位名叫库尔齐娅(Curzia)的记者。她身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现场,对死者及其家属抱有同情,却无法个体化地书写报道。你也曾以记者身份去过一些新闻事件的现场,不久前还去了乌克兰,作为一名小说家,这些记者/媒体经验如何影响了你的写作?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中出现了一位名叫库尔齐娅(Curzia)的记者。她身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现场,对死者及其家属抱有同情,却无法个体化地书写报道。你也曾以记者身份去过一些新闻事件的现场,不久前还去了乌克兰,作为一名小说家,这些记者/媒体经验如何影响了你的写作?
保罗·乔尔达诺:媒体与我们的关系是《塔斯马尼亚》想探讨的主题之一。与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的是,欧洲的媒体曾经是由市场力量影响和推动的,而在过去10年中,市场力量在不断受到削弱,这使得媒体感到自己的存在备受威胁,比如,新闻机构丧失了议程设定的能力,取而代之来设定议程的是社交网络。信息曾经是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得以运转的支柱,现在这根支柱受到了侵蚀和损毁,几近坍塌,媒体已成无权无势的场所。库尔齐娅是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女记者,她没有稳定的合同,处于一种摇摇晃晃的不确定状态,不得不在机构中不断乞求获得下一项任务,以争取自己的空间。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处境:社交媒体降低了信息的质量,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懂得新闻运作规则的专业记者。
我也给媒体写报告文学,而且现在写得越来越多。我是以作家的身份来为媒体写作的。我与记者一样,去到事件发生的现场,做采访,收集信息;但我处理这些素材的方式与记者有一点微小的不同,始终是从“我”如何看待事件与现场出发来写作的。第一人称视角或许会对客观性有轻微的扭曲,但这正是小说家写作的方式。我认为,小说家需要像记者那样的直接经验,走出门,感知现实,与现实互动,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来自虚空的想象。我不会直接描写我在乌克兰的经历,但我正处在这种写作状态中:将我在乌克兰的所见所感转化为小说家私密和个体的语言。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但也非常吸引人。
三联生活周刊:在一次欧洲的文学论坛上,你曾谈到,在新的大背景下,亲密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每件事都在“垂直层面上被扭曲了”。能否展开讲一讲?
保罗·乔尔达诺:在我过去的小说中,我一直是以很层级化的方式来想象故事的:一个或几个角色从某个起点开始,经历了一系列事情和变化,最后到达了一个与起点不同的地方。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写小说的方式,它已存在了上千年。疫情暴发以来和疫情结束以后,这种小说观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它更像是把某种宿命和结构强加于角色的生命,我也感到很难以这种方式来继续写作。许多作家,包括我,发现我们置身于一片废墟的景观中,在废墟中求生。这种“废墟”不断出现在《塔斯马尼亚》中,最终小说结束于广岛的核爆,也是一个水平的图景,所有的建筑大厦都倾覆,所有认为可以自上而下以一致性来建造事物的观念都坍塌了。那么接下来是什么?
这种变化改变了我的写作,也改变了我想象角色的方式。比如,在非常保守和传统的社会中,家庭和父母正是最垂直化的关系;你毕业了,结婚,找到一份工作,生自己的孩子,这都是非常垂直化的,年轻时的我对这一切都感到恐惧,如此既定的轨迹。正是我的第一本小说《质数的孤独》,给了我想要的自由,让我能够以更混沌的方式来探索关系。我爱上了一位处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女性,她已有两个领养的孩子,他们也逐渐成为我的生活和家庭的一部分。小说中的“我”头脑中原来也有很多既定的观念,比如他很想要一个自己血缘意义上的孩子,我也曾有过这些“正确”或“错误”的观念,不清楚这些观念来自于我内在的自己,还是来自于外在的影响;但这些观念阻碍他看清自己正拥有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非常有趣的、出人意料的,但我们如此狭隘,以至于当这些关系已经发生时,却无法辨识出它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乔尔达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