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高
作者:黑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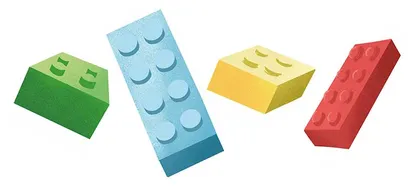 我们有砖块,而你有想法。这是乐高公司在90年代的产品目录中写的话。再往前倒推60年,随着大萧条席卷而来,丹麦的木匠大师奥莱·柯克·克里斯蒂安森迫切寻求谋生之道,他在制造梯子、熨衣板之余,投入了全新的木制玩具产品线,并将其命名为乐高,这个名字源自丹麦语“玩得开心”。从第一批木头玩具,到40年代末批量生产的乐高模块原型,再到50年代末新型模块的诞生,乐高凭借可连接的塑料颗粒,跻身世界三大玩具公司。在巅峰时期,乐高每年生产的砖块如果被全部拼接起来,足够通往月球了。
我们有砖块,而你有想法。这是乐高公司在90年代的产品目录中写的话。再往前倒推60年,随着大萧条席卷而来,丹麦的木匠大师奥莱·柯克·克里斯蒂安森迫切寻求谋生之道,他在制造梯子、熨衣板之余,投入了全新的木制玩具产品线,并将其命名为乐高,这个名字源自丹麦语“玩得开心”。从第一批木头玩具,到40年代末批量生产的乐高模块原型,再到50年代末新型模块的诞生,乐高凭借可连接的塑料颗粒,跻身世界三大玩具公司。在巅峰时期,乐高每年生产的砖块如果被全部拼接起来,足够通往月球了。在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博物馆,有一台由乐高颗粒搭建的存储器,顶部站着的两个小人颇有童趣。它是Google史上第一台存储器,也是极客论坛里被津津乐道的话题。1996年,拉里·佩齐和谢尔盖·布林攒了10个当时市面上最佳容量的4GB硬盘,通过乐高颗粒拼凑起来,测试算法,这个色彩斑澜的存储器一用就用了3年。除了佩齐和布林,乐高拥趸还包括皮克斯的创始人约翰·拉赛特。当这些商业精英被视为新时代的标杆时,乐高也和改变世界的创造力产生关联。毕竟乐高声称,如果你有6块相同颜色的2×4砖块,它们就能以9亿多种不同的方式堆叠,更不用说,算上不同颜色和形状了。
乐高砖块通常分为通用零件和特殊零件两大类,以散装形式或搭配好的主题套装系列出售。原本乐高都在深耕自己的主题线,比如,自1966年推出火车系列,它的粉丝横跨成年人和儿童,其受欢迎程度催生了国际协会和公约。作为经典,火车元素也延续在哈利·波特系列和城市系列中。再比如,80年代的太空系列,拼起来呈现出月球的表面,这几乎是最早成为系列的太空玩具了,后来的航天、科技系列都受其影响。然而,就当对手美泰在1999年让芭比娃娃在迪斯尼电影《玩具总动员》客串之后,乐高也开始和影视紧密结合。
一方面疯狂扩张,另一方面几款最成功的产品,如《星球大战》和《哈利·波特》,销量受电影档期影响,上下波动,这是乐高无力控制的。过重的负担使其在2004年濒临破产,重新专注于研究儿童的兴趣喜好并精简零件之后,才“起死回生”。精简之后的乐高人仔,基本上只是两种比例——成人和小孩。不仅如此,它从初始没有表情的身体结构,到添加表情,然后慢慢有了肤色、穿上制服,甚至从他们的帽子可以辨出身份,这些从形象上感受到的平等化特质与乐高的生产国丹麦微妙地呼应着。
从创意上,也可以看出乐高是一个“众创”的平等化游戏。自2011年起,Lego Ideas每年在全球范围内举办。玩家们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乐高模块“各显神通”,凡在比赛投票中获得1万票以上的模型,都有可能被乐高考虑投入量产和出售。“神秘博士”“生活大爆炸”系列的创意都来自这一机制。
相比于主题套组,散装颗粒才是发挥想象力的创作池。那些每年推出的全新颗粒乍看枯燥,却对执着于制作精密作品的人来说很是实用。建筑系出身的亚当·里德·塔克便是以此“复刻”出标志性地标的微缩版。在他接触乐高之前,这个玩具公司从未想过要量产低龄目标客群无法挑战的套装。2007年,当乐高建筑系列的“前身”实验性地出现在特定商店里时,不仅畅销,售价还远高于相同数量的儿童套组。无论对大人还是小孩,乐高都相当于游戏乐趣的同义词。就这样,不断扩充的城市系列日益成长为乐高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
塑料颗粒的创作弹性使其不仅能胜任复刻建筑,还能胜任复刻“安提基特拉机械”。制作于公元前150年到100年之间的安提基特拉机械,被认为是最古老的计算装置。虽然早在1901年就被发现于希腊岛屿的沉船中,但直到一个世纪后,高分辨率的X射线断层扫描才终于揭示了该设备的真正用途——以精密的齿轮模拟天体的运行周期,类似技术的航海天文钟在欧洲直到14世纪时才出现。在英国一家拥有百余年历史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的赞助下,经过30天的设计和建模,2010年,以1500个组件、110个齿轮乐高砖块复刻的安提基特拉机械,功能齐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乐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积木了,它能盛放的想象的东西非常多。如果你认为它是理工科的专属,就错了。在推出自己的大电影之后,它更是生生变成了乐高宇宙,进一步涉足流行文化和艺术。
2015年,早在奥斯卡提名公布时,《乐高大电影》的导演之一在推特上分享了乐高小金人的照片,来安慰自己未能入选。谁能想到在一众明星的“推波助澜”下,奥斯卡期间乐高小金人被提及了近5万次。其作者奈森·萨瓦亚(Nathan Sawaya)因此受到关注。奈森是一位以乐高标准颗粒创作三维雕塑及马赛克画作的纽约艺术家。像他一样重新定义乐高的关键人物全球一共有13位,而奈森是唯一一位同时获得乐高专业认证和乐高制作大师名号的人。
奈森从5岁开始接触乐高,曾搭出过一只和实物大小相同的宠物狗,在他看来,乐高无所不能。成为职业艺术家前,奈森在律所工作,白天做律师,晚上进行乐高创作。渐渐地,他的积木作品越来越成规模,其真人大小的作品在网站颇受关注,甚至有人邀请他完成定制作品。对兴趣的热爱让他放弃了律师的身份成为职业乐高艺术家。黄色半身人像是奈森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它撕开胸膛,像血液一样流淌的积木散落一地。2013年单曲《G.U.Y.》的MV中,Lady GaGa将自己的头像拼贴在奈森的黄色积木人之上,以此呼应“艺术不死”的音乐主题。
这些作品倒是对家长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原本中国家长们无法理解,一个塑料玩具怎么能卖得这么贵,直到它开始和教育挂钩,他们的观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当坚信乐高能拓展孩子的思维,尤其是在空间想象力层面上时,家长们开始毫不心疼地往里砸钱。2010年前后,国内兴起了乐高培训课。然而,把任何一种玩乐变成课程,听起来都多了“方法论”的意味,远离了开放式的可能性。
乐高能给孩子提供什么?一种综合的空间感。塑料颗粒不框定最终形态的操作方式,请孩子们来胡乱尝试一切事情。在这一点上,粗糙的瑞典电脑游戏《我的世界》(Minecraft)与乐高异曲同工。《我的世界》是一个试错和不断探索的世界,可以建造各种复杂的机器,把恶作剧拍成视频甚至创造艺术作品。那里充满了语义不明的文字指令和秘籍,这与大多数现代计算领域的趋势相悖——不为隐藏复杂,让界面易于操作,而为鼓励发现运行机理,甚至是去破坏或修复它们。
原本乐高也是如此,把世界拆分成一个个像素,孩子们先用简单的颗粒拼出复杂的图案,然后在周围的世界里发现这些图案。而现在的乐高更像是电影的周边衍生品,在它终于超过美泰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玩具公司时,贡献最大的并不是乐高经典的散装模块,而是主题模型,其中销量较好的主题,与电影相关的占了一半。这不免让老玩家有一些失落。大量喜欢乐高的人,从原来的自我搭建变成了去收藏:拆开套装,按照图纸行事,摆到书架上,然后再去买一套。令人惋惜的是,很少有人用这些主题模块再去拼接一些说明书之外的东西了。 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