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断裂中延续
作者:维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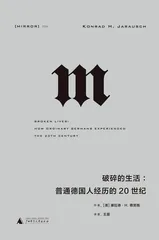 世界上可能很少有哪个民族像德国人这样,对本国的历史抱有如此复杂的态度。回顾过往,英国人仍可以为帝国往事而自豪,即便是那些有着悲惨、屈辱历史的民族,至少也可以将之视为殉难,激励活着的后人,然而对德国人来说,20世纪的恐怖经历带来的往往是一言难尽的耻辱,又或是发自内心的厌恶,更有一种罪恶感始终挥之不去。这就像是一户看似体面的人家,地下室里就掩藏着许多尸骨,那是难以启齿的过往,却又无法装作它们全然不存在。
世界上可能很少有哪个民族像德国人这样,对本国的历史抱有如此复杂的态度。回顾过往,英国人仍可以为帝国往事而自豪,即便是那些有着悲惨、屈辱历史的民族,至少也可以将之视为殉难,激励活着的后人,然而对德国人来说,20世纪的恐怖经历带来的往往是一言难尽的耻辱,又或是发自内心的厌恶,更有一种罪恶感始终挥之不去。这就像是一户看似体面的人家,地下室里就掩藏着许多尸骨,那是难以启齿的过往,却又无法装作它们全然不存在。
在这短短100年里,德国人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并且都身处战争冲击波最剧烈的心脏地带,连民族身份也一度被撕裂,其间葬送了两个帝国(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一个共和国(魏玛共和国),留下两个残缺不全的德国(东、西德),直到柏林墙倒塌,才在上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迎来了一个“正常”的国家。就此而言,可以说那些年里没有哪个德国人曾完整地拥有过正常的生活。
以往的历史记录通常是“眼光向上”的,聚焦于那些推动历史进程的“大事件”,直到近些年来,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眼光向下”,关注普通个体的感受。这并不只是简单地将望远镜倒置、突出人的维度,也是因为简单的事实:任何事件,每个人因其处境的差异,主观感受是千差万别的。一个意大利村庄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村民们在追忆过往时,最常提到的并不是那场遥远的大战,而是一次土匪劫掠,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才是鲜活、具体、产生直接冲击的重大事件。
20世纪的德国几乎已见不到这样幸运的桃花源居民,这也是在他们讲述自己遭遇时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没有人能幸免于被时代的大浪席卷,哪怕你不关心这些政治冲突,也总有一天会赫然发现自己的整个生活遭受到有时是毁灭性的影响。战争一度是军人和政治精英们的事,但在总体战的年代里,平民也无法置身事外,这既表明德国已是一个内在紧密联结的现代国家,也意味着普通人更难依靠距离躲避外部冲突的影响,左右自己的命运。一位难民雅各比娜·维托拉道出了这种感受:“时间像狂野而汹涌的海浪一样扫过我们,摧毁了一切。”
不可避免地,后来经历的那些可怕事件,会反过来重塑更早前的历史记忆。很多人会怀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个强盛、繁荣的德意志帝国,虽然那背后是艰辛劳动、缺乏基本权利和司空见惯的家庭暴力,但那时好歹还抱有一种对未来乐观的期许。然而,毁灭的种子已经播下,借用斯宾格勒的话说,“为了把他的意志的形式强加于世界,浮士德式的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那就是德国的悲剧所在,它一心想成为超人,以至于大量努力都用错了地方,最终才不得不承认自己做出了灾难性的选择。
此后的历史已被人反复讲述了太多遍,但普通人视角的回忆至少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历史教训:为什么德国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会选择走上一条现在看来如此明显的自我毁灭之路?答案或许是:在一个急剧现代化又经历了巨大挫败的国家,无数原子化的个体渴望着融入更强大的种族共同体,哪怕是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也乐于相信这一看似闪闪发光的前景,“因此需要非凡的洞察力和勇气才能始终远离、拒绝服从或积极抵制第三帝国的扭曲世界”。
彻底的战败和纳粹罪行的披露,使这一黑暗的乌托邦完全被祛魅了,成为现代德国的原罪。在经历过那些可怕的事之后,一个人不可能还是原先那样了。对如梦初醒的德国人来说,“好的战争”已成为一种无法接受的矛盾修辞,正是由此而来的反思和批判,使他们成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德国的浩劫”之后,每个德国人都是事实上的幸存者。在战后的废墟上,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道出了德国人痛苦的良知:“当别人被杀害而我却活下来的时候,我的内心有声音告诉我:我因侥幸活着而有罪感。”他说,那些年里,他碰到的不少德国人都说以自己是德国人为耻,“我要回答说,我以是一个人为耻”。
他表达的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反思,但对更多人来说,困扰他们更甚的是自我认同:既然“千年易过,德意志的罪孽难消”,那么在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之后,做一个德国人意味着什么?有些同化犹太人说:“我们是德国人。控制了国家的匪徒不是德国人——我们才是。”这的确有力地反驳了种族主义的论调,根据文明而非种族重新定义“德国人”,但简单地将“坏人”剔除并不能就此恢复共同体的纯洁,何况,正是那种共同的罪恶感,才让战后德国人得以团结在一起,也让他们重新站起来,因为没有人会“帮助德国人摆脱我们自己陷入的混乱”。
正因为经历了那么多自己造成的苦难,德国人的战后重建故事才那么集中在对“正常化”的渴望上,他们不再想当可怕的“超人”,而只想做一个正常人。然而正因此,绝大多数普通人只想忘记过往,重新开始新生活,更不愿意太多反思他们个人在第三帝国中扮演的角色,何必呢?他们也是受害者。要直面自己的共谋毕竟是一件难堪而痛苦的事。
何谓“破碎的生活”?那是一种在巨大的外力左右下,个人无法掌控自我命运的磨难,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想要专注当下毕竟也情有可原,然而,人们逐渐意识到,不管是回避还是否认,都不能让历史的幽灵就此安息,而他们如果想要真正回归“正常”,就必须勇于面对过往,在毁灭中重生,在断裂中延续。正是这种人生的断层和随之而来的批判,才使公共记忆文化转化为社会自我更新的动力,没有这样的反省,意味着不能学会任何历史教训。希特勒曾说,“德国战败意味着它不是优等民族”,但能在战败的废墟上反省、重生,才真正证明德国人确实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在冷战的分断体制下,这个一度陷入精神分裂的民族,有着迥然不同的经历和历史记忆,重述20世纪的遭遇不仅对个人而言是一次自我整合,也是对整个国族伤痕的疗愈。毫无疑问,不同的历史记忆仍然在争斗,而那些被记下来的也可能在有意无意中遭到悄悄的篡改、消除,那些未被提及的记忆甚至可能更为重要,以至于任何个人口述的真实性和代表性,都是需要再三警惕的一件事。不过,真正重要的是:正是这些将德国重塑为一个因自我反省精神而受世人尊敬的民族,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并未远去,因为活着的人始终需要它。 破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