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为什么要“走向世界”?
作者:艾江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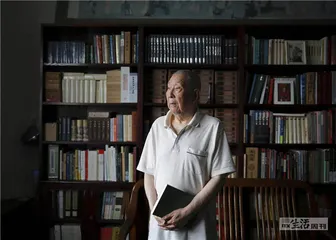 长沙开福区湖南省出版局的宿舍楼中,年过九十的钟叔河依然忙碌着。那天,当我们敲开那挂着“念楼钟寓”的大门时,钟先生正和前来探望他的客人在书房攀谈,书桌上摊开的是他即将重印的一本杂文集的校样。
长沙开福区湖南省出版局的宿舍楼中,年过九十的钟叔河依然忙碌着。那天,当我们敲开那挂着“念楼钟寓”的大门时,钟先生正和前来探望他的客人在书房攀谈,书桌上摊开的是他即将重印的一本杂文集的校样。
钟叔河自己曾在《念楼随笔》序言中解释过:“念楼”即“廿楼”,就是他所住的20楼,门牌起初由竹刻艺术家叶瑜荪所刻,后来又经雕塑家雷宜锌模铸,挂于门外。这位念楼主人,自上世纪80年代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便为人尊敬的出版家,对手艺向来情有独钟。原本用作书房的客厅,除了满架的图书,一张台球桌,颇为引人注目的还有书架上他的几件手工制品:竹笔筒、竹制茶叶筒、细工木刨、精工木刨。在一篇文章中,钟叔河写道:“我从小喜欢制作,如果允许我自由择业,也许会当一名细木工,当可胜任愉快,不至于像学写文章这样吃力。但身不由己,先是被父母拘管着在桌前读《四书》《毛诗》,1949年误考新闻干部训练班,又未蒙训练即奉命到报社报到,想进北大学历史考古亦不可能。1957年后,作为为国家服务的知识分子,是被投闲置散了,但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忙于做工,身体和精神上反而觉得充实了不少,尤其是能够在屋里放一条砍凳的时候。”
“我原来读书,并没有意识到以后会编书。我看书比较早,比较杂,这是我的一个优势。我出身读书人家,家里有书。”送走其他客人,我们的聊天从读书开始。眼前的钟叔河身形高大,略带口音,声音洪亮,丝毫不见老态。
钟叔河的父亲钟昌言是最后一批考过八股文的秀才,又是时务学堂的新式学生。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钟叔河被父亲送回老家平江乡下,在那里一直待到抗战胜利。在乡下,钟叔河几乎读完中国的旧小说,找到什么书就拿来读。“正常社会里,就算父亲是作家,也不一定在10岁前就看《阅微草堂笔记》。因为没有其他书可以看,父母也没在身边,在平江乡下,没人管我。读《阅微草堂笔记》时,有些地方不明白,比如‘承尘’,过了好久才知道是‘天花板’的意思,因为那时在平江乡下,房子抬头就是瓦,没有一间房子有天花板。”
1949年,高中没有毕业,钟叔河就考入“《新湖南报》、新华社湖南分社新闻干部训练班”,成为一名记者,少年时好读杂书的习性依然如故。与钟叔河同年考入培训班、曾在《新湖南报》工作的出版家朱正回忆1957年两人被打成“右派”前的那段日子:“晚餐以后,我常常和他一同到古旧书店去翻旧书。大体上我只注意和我的研究专题有关的书,而钟叔河涉猎的方面要比我广得多。当代的,古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从文史方面直到生物学和大众天文学,他几乎是无书不读。就这样,他从这看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阅读中获得了多方面的知识,这对于他后来编‘走向世界’丛书显然是很有用的。”
1957年钟叔河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之后20多年里先后做过仓库搬运工、木模工、化学工、电镀工、制图员,以维持生计。几十年过去了,朱正仍记得自己在1962年底结束劳教后在钟叔河家看到的情景:“我回来以后,发现他很会做木工,他和他太太两人做木匠,不是普通的桌椅板凳,是做机械的木模。我到他家以后,进门很小的天井里摆着木工用的砍凳,家里挂着锯子、刨子,大大小小全套木工设备,他就是一个木工了。”
钟叔河一边靠手艺艰难谋生,一边仍在思索:为何自己从一个解放前的革命青年,突然会成为“反革命右派”?他大量攻读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书,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读史的过程中,他发现在1800年以前,就有欧洲人到中国来;可是直到180年以前,还没有中国人去过欧洲。封闭造成了落后,落后又加剧着封闭。“长期封闭的社会一旦开放,发生的变化是极其广泛、深刻而激烈的。人们只要一‘走向世界’,他的价值观和哲学观就必然发生变化,这是改变封闭造成的落后状态的强大动力。早期‘走向世界’的人的现身说法,对现代化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
晚清那批知识分子,走向世界时不但记录所见所闻,同样记录当时的心境与思考,这让苦闷中的钟叔河感同身受。黄遵宪是第一个对日本有深入研究的维新思想家,他反映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重大变化的《日本国志》,还有吟咏日本国政民情与风俗物产的《日本杂事诗》均在“甲午之战”后的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戊戌政变”之后,他被开缺放归,只能做一个诗人。《人境庐诗草》中的多数诗篇正写于这一时期。在后来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的《日本杂事诗广注》导言中,钟叔河写道:“所谓‘放归’,就是放逐归家,等于现在的‘开除公职’。……他始终在紧跟着历史的潮流,关心着天下的大事。尽管自己名列株连黑籍,却始终对未来抱有信心,相信四亿人民一定会从二千多年的魇梦中醒来的。”可谓当时钟叔河自己心境的写照。
 1979年,经朱正介绍,钟叔河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作家蒋子丹,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编辑。她向我回忆:“那时候来了好多被打成‘右派’的人,钟叔河、朱正、江枫、杨德豫……有些人经历苦难之后,可能说话比较谨慎,我感觉钟叔河比较潇洒,那时候他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名气,什么都说。那些反右中的经历,包括后来坐牢的事情,他津津乐道,我们也听得很有意思。”
1979年,经朱正介绍,钟叔河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作家蒋子丹,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编辑。她向我回忆:“那时候来了好多被打成‘右派’的人,钟叔河、朱正、江枫、杨德豫……有些人经历苦难之后,可能说话比较谨慎,我感觉钟叔河比较潇洒,那时候他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名气,什么都说。那些反右中的经历,包括后来坐牢的事情,他津津乐道,我们也听得很有意思。”
重返工作岗位,钟叔河干劲十足,他计划把以前读过的,包括在北京、上海各地图书馆搜集的300多种晚清时期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记录进行整理,并选辑出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100种。“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没有与世界同步,中国脱离了这个轨道,如果与变化的世界同步了,那么问题就解决了。”钟叔河说。在他看来,回顾晚清那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所留下的记录,对改革开放后亟待重新走向世界的国人仍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正因如此,钟叔河坚持将丛书命名为“走向世界”。“起初他们不同意叫‘走向世界’,建议就叫作‘清人出国笔记’,因为这是一些古书。我编的书虽然是古人的书,但是是给现代人看的,而且也不是为了现代要看古书的人看的。要看古书的话,研究这些清末的人写的东西干什么呢?它写的是外国的事情,写的是巴力门(Parliament,议会)、德利风(Telephone,电话)这些东西。”钟叔河说。
可在当时,人们并不确信出版这套旧书的社会价值。此外,100种图书的庞大规模也挑战着当时的出版经营理念。依照规定,每个编辑一年只有4个选题,可如果拆开来出,便无法保证这套丛书史料的完整性与思想的连续性。钟叔河提出将自己3年的书号集中起来,这样就可以一次出版12本。
1980年冬天,各地新华书店上柜的一册薄薄的小书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本书封面左上角的内容简介写道:“一百多年前的友好访美记录,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的详情。”这正是“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本: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光绪二年(1876),在宁波海关任职十多年的李圭,以中国工商界代表身份受邀赴美参加规模盛大的世界博览会。在美国,除了参会,他还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等城市,然后过大西洋到欧洲,顺道游览伦敦、巴黎。这本书以一半以上篇幅记述了博览会中的见闻,以及美国建设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书的附录《地图图说》中,李圭以自己8个多月环绕地球一周的亲身经历,验证了“大地是一个球,围绕太阳运动”:“使地形或方,日动而地不动,安能自上海东行,行尽而仍回上海,水陆共八万二千三百五十一里,不向西行半步欤?”
这本李鸿章亲自作序的游记,由总理衙门出资印行3000部,在士大夫中产生很大影响。郭嵩焘使英期间,便翻阅此书,记入日记。康有为也是在读了这本书后,为其中描述的新事物所吸引,开始走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
回到19世纪的历史现场,国人对西方的真正了解,始于1840年那场屈辱的“鸦片战争”。据钟叔河在后来为丛书所写序言基础上撰写的《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的考证,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有三个中国人由于偶然机会到过欧洲并留下可信记载,其中仅有1782年因海难被外国船只救起因而“遍历海中诸国”的谢清高留下的《海录》,1840年左右得以在国内刊行,被认为是“中国人著书谈海事”之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了解外洋情况,学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客观需求,清政府开始派遣官员出洋。同治五年(1866),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游历欧洲后留下的《乘槎笔记》,这批人中学生张德彝留下的《航海述奇》;同治七年(1868),志刚率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使美欧各国后记录的《初使泰西记》,均是官遣出洋的产物。只是,如历史学者雷颐所说:“最早出国的几个人,斌椿、张德彝,并不是有目的地向西方寻求真理。他们都是职务所遣,被派出去看了看,懵懵懂懂之中,看什么都新奇,什么东西都记录下来。这些东西很有趣,也恰恰说明中国人最早是怎么看世界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人认为西方先进,开始有目的地出去寻找真理,比如郭嵩焘、黄遵宪等人。”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记述背景,钟叔河在每种书的卷首都撰写了万字以上的绪论,阐述作者“走向世界”的历史背景与研读体会。丛书以每月一本的速度出版,影响越来越大,到1983年,“走向世界”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20册,收录晚清人的外国记述26种。1984年,钟叔河被调任岳麓书社总编。截至1986年,加上重印扩编,丛书规模扩大为10卷35种。
上世纪80年代,这套丛书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成为热议话题。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评价这套丛书:“这确实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在这方面,推而广之,可称为整理古籍的典范。”1984年冬天,钱锺书联系钟叔河在北京见面,并主动为他的《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作序。杨绛后来在信中告诉钟叔河:“他(钱锺书)生平主动为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8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空前活跃,人们都将目光聚焦在国外形形色色的思想与文学潮流上。在当时五花八门的“丛书”中,一套晚清人物留下的历史记录,何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雷颐向我谈起那时的“丛书热”:“在80年代,有三套书影响很大,一个是‘走向未来’,一个是‘走向世界’,还有一个是‘文化:中国与世界’,开始把海德格尔、萨特、维特根斯坦等西方哲学家成系统地翻译出来。最先出来的是以介绍当代新科技、新理论为主的‘走向未来’丛书;第二个是谈论历史人物的‘走向世界’丛书。这两套一个谈最新的东西,一个谈历史,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有一种内在的共振,在那个启蒙年代给人一种思想解放:‘走向未来’,直接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介绍到中国;‘走向世界’,让人觉得中国走向世界、学习外国的历程艰难。”
1981年,雷颐在吉林大学历史系读大三时,便看到了这套书最初出版的几种,后来还在《历史研究》上读到钟叔河的几篇序言,印象极为深刻。“80年代,对我个人来说,刚刚接触到中国近代史。从前近代史讲发展线索,完全从革命角度看,中国近代史就是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再到辛亥革命。我后来的研究生导师李时岳,第一个提出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再到辛亥革命的中国近代史主线。洋务运动在之前的叙述中,长期作为‘反动政治标签’,事实上洋务运动引进现代科技与工业生产,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这套丛书,恰恰以现代化的眼光,讲洋务运动中近代中国人如何打开国门,怎么看世界。在革命叙述中,‘走向世界’这批被遗忘的历史人物,第一次重新出现,还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走向世界”,路途漫漫
1985年,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在岳麓书社出版时,距离他写下这些日记,已经过去100多年。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从上海启程,经历51天的海上航行,于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赴任驻英公使。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离开伦敦回国。《伦敦与巴黎日记》正写作于这两年间。
国外的耳闻目睹,使郭嵩焘得出比其他洋务派更为深刻的见解。出国之前,郭嵩焘已经看到“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出国后,他虽然也关注欧洲的技术文明,访问煤铁工厂,但他显然更为关心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在参观伦敦邮局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指出封建专制国家只求“富国”,资本主义国家却懂得先要“富民”。不但如此,他还研究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有次与人讨论英国税法时,他说道:“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学者陆建德1983年曾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告诉我,那时经常去伦敦,有时候还去位于Portland Place(波特兰广场)的中国大使馆,渐渐了解了这座建筑的历史,那正是在清朝光绪初年,由接替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的曾纪泽申请购置。也因此,引起他对那段历史的关注。从90年代开始,陆建德便关注张德彝、郭嵩焘、刘锡鸿等一批早期到英国的国人,怎么看外国人,怎么描写英国。那批最早走出国门的晚清知识分子,出于好奇、不带偏见记录下来的一些细节,在陆建德看来,往往能折射出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记录了伦敦一车夫因为鞭打马匹过甚被罚款并监禁一个月的事情,陆建德读后特别感慨:“我深深记得,原来住在北京劲松那块儿,一到夏天,农民赶着马和驴子来卖西瓜。我看到那些马和驴子非常可怜,由于缰绳套得过紧,后腿上的皮都磨光了,露出肉。英国100多年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已经很高,对动物权利有很高的认识,这种意识我们以前不大有。”有感于此,在2006年回顾这套丛书的一篇文章中,他谈道:“丛书所收著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了国人的眼界,同时又让读者意识到,身边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其实都是值得关注和检讨的。时至今日,这套丛书读来,依然具有让人不安的力量。”
这种“使人不安的力量”,似乎也印证着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中,这套书顽强的生命力。2008年,“走向世界”丛书再版,钟叔河在谈到别人的质疑时说:“‘走向世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中国还没有完成,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应该问一问自己,在物质上我们走向了世界,在内心是否走向了世界呢?”
1988年,钟叔河离任岳麓书社总编,“走向世界”丛书的后续出版被搁置下来。2012年,钟叔河将他保存了25年的书稿档案移交岳麓书社,并承担了不少具体工作。4年之后,这套共计100种的丛书终于出齐。
(本文写作参考钟叔河著《念楼随笔》,梁由之、王平合编《众说钟叔河》,朱正著《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书。感谢王铁军、戴君等人对采访的帮助) 中国近代史世界历史钟叔河走向世界郭嵩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