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作者:陈赛 即使衣食无忧,但在精神层面,我们却始终被一种匮乏感纠缠,不够美,不够瘦,不够聪明,不够有钱,工作不够好,房子不够大,人生不够成功……
即使衣食无忧,但在精神层面,我们却始终被一种匮乏感纠缠,不够美,不够瘦,不够聪明,不够有钱,工作不够好,房子不够大,人生不够成功……
在现代社会,我们努力追求金钱、爱、安全、幸福,以及最好版本的自己,但又永远感到匮乏。于是,我们求助于各种旨在提升自我的励志书、成功学、心理自助书籍和课程:如何锻炼肌肉,如何提高智商,如何修炼情商,如何财务自由,如何获得真爱,如何成就完美的人生……而且通常承诺可以在3个月、4个星期或者24小时内速成。
当个人成长/自我提升成为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时,或许我们应该停下来问问自己,这种关于自我的匮乏感到底从何而来?关于提升、变化的执念又从何而来?我们现在的自我到底有什么问题?怎样才算是最好版本的自我?自我升级的界限在哪里?停滞不前的人生真的毫无价值吗?
很多时候,关于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社会早已为我们写好了脚本,只不过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比如,当我们将人生视为一个进步的过程,只要有足够的意愿和相应的技能,就可以在一次次的自我塑造、自我雕琢之中达到完美的境界时,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相信这一点?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做最好版本的自己”之类的概念,我们几乎没怎么想过“自我”这种东西。关于人生,除了不要浪费食物之外,我母亲只教过我两个最基本的道理:1.你是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你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有好的未来;2.别人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
这当然是她自己的人生经验。他们那一代人,对匮乏和痛苦有足够多的体验,对人生的期待值不高,但作为红旗下长大的一代,又相信人定胜天这种事情。所以,在她看来,人生是可以掌控的,但要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当动力不足时,可以引入向上比较的机制,激励自己继续前行。当然,她关于子女教育的参照系不过方圆十里,比如她经常拿隔壁家的一位哥哥来激励我,“你看看那个哥哥读书多么用功”,以至于我每次见到那个哥哥扭头就跑。
以前的世界可能真的比较简单。我遵照她的原则践行我的人生,再加上一点点运气,也安安稳稳地活到了今天。我努力地学习,考上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也是她教我的,尽量保持合理的野心和朴素的责任感,量力而行,尽己所能,与人为善。
但是,当我的孩子出生后,当我思考孩子的未来人生时,突然发现我母亲的原则已经行不通了。在今天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作为普通人家的孩子,只要努力就会有好的未来吗?别人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吗?他刚出生的那段时间,我有时候看着他坐在小小摇椅上对着我笑,心里一片茫然。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会创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吗?我要在多大程度上为他的幸福负责?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用“流动性”来描述西方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特性。与固态社会(即大工业时代的现代社会)不同,在流动性社会中,一切神圣的、坚固的、持存的东西都消失了,整个世界被流动的、偶然的、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因素所占据。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就像身在流沙之中,没有任何固定的、可参考、可预测的框架。每一个试图稳固我们位置的举动,都可能适得其反,让我们陷得比以前更深。
我们也处在一个流动性的社会中吗?如果是,所有这些关于我们自己,关于下一代的焦虑和不安,是否都可以算是对“流动性社会”的一种正常反应?在流动社会里生存,第一条规则就是要学会应对变化。灵活性、适应性和持续不断的自我发展,是流动社会珍视的价值。停滞不前则是不可接受的堕落。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转向内心,以寻求某种程度的确定性和控制感。毕竟,相比于改变世界,改变自己容易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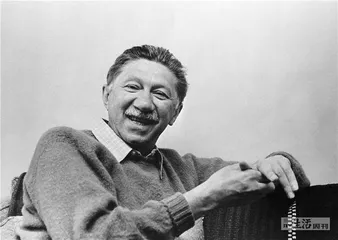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拉什在《自恋主义文化》一书中指出,“当人们除了自己无法依赖任何外界力量的时候,自我提升就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主张”。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拉什在《自恋主义文化》一书中指出,“当人们除了自己无法依赖任何外界力量的时候,自我提升就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主张”。
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拉什写作这本书的年代,当时的美国与今天的中国几乎有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经过30年的经济成长,大部分美国人摆脱了贫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自由,但60年代反文化运动已经耗尽了人们以政治改造社会的热情,所以,他们选择将世界的麻烦抛诸脑后,将所有的财富都投资在自我提升上面。不计其数的民众跑去参加自我提升研讨会,阅读心理自助书籍,“学习如何以自己为第一优先,理解这个世上没有受害者,自身的一切境况都是自己造成的”。
在《拯救现代灵魂:心理咨询、情感与自助文化》一书中,以色列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斯追溯了心理治疗的价值观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与心灵生活的过程。她认为,正是在美国六七十年代的“自我提升运动”中,心理学的科学话语与自助(Self-help)的民间精神真正融汇在一起,导致美国文化、情感生活和现代身份的重大变化。
按照她的分析,20世纪初,弗洛伊德对于美国文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为日常生活发明了一种语言,提供了一种意义框架。在这个意义框架内,精神健康是现代男人和女人身份的核心。不过,弗洛伊德对人性是很悲观的。他曾经说过,精神分析的目的并不是治愈心灵,而是“将神经症患者歇斯底里的痛苦转化为日常的不幸”。
之后,他的后继者,如阿德勒、弗洛姆、凯伦·霍尼等,尽管派别各异,但都修正了他关于人性的悲观论调,对自我发展持更加积极和开放的态度。比如,阿德勒否定了弗洛伊德的决定论,认为人生并不由过去决定,人会根据境遇的变化和长期目标而改变自己的行为。爱利克·埃里克森将人的成长从弗洛伊德限定的童年早期拓展到整个人生阶段。弗洛伊德关心一个人的童年创伤如何制造成年期的精神疾病,埃里克森则强调一个人战胜心理危机的能力。他将正常人的一生,从婴儿期到成人晚期分为8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殊的心理矛盾需要解决,但每一次危机也都为自我提供了成长的机会。由此,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与美国文化中固有的关于自我的观念越来越合拍,直到卡尔·罗杰斯和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正式将二者连接起来,从而将其推入主流文化。
卡尔·罗杰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善的、健康的,而精神疾病和犯罪都是本性的扭曲。他开创的人本主义疗法,其整个理论基于一个简单的假设:和一切生物一样,人也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一是创造的倾向,二是亲社会的倾向。心理咨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促成一个人顺着他的本性走,促进人的本性的现实化。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痛苦和烦恼,但表层之下都有一个核心的追索,或者说,每个人其实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样才算成为我自己?
而答案,要从他们的内心去寻找。
这种向内的转向,对于当时的美国社会系统而言可以说是一种解放,一种抵制,但它同时造成了另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当马斯洛将“自我实现”置于自我模型的中心时,他也是在告诉人们:如果一个人的人生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潜能,唯有如此才算活出了真实的生命,那么绝大部分人都是“未实现”的。而当自我实现与心理健康变成同义词时,也意味着一个拒绝实现自我潜能的人,就是一个“病人”。
一个人为什么会拒绝实现自我潜能呢?
马斯洛提出的答案是:对成功的恐惧。“我们害怕变成在最完美时刻、最完善条件下,以最大的勇气所能设想的样子,但同时我们又对这种可能非常地追崇。这种对最高成功、对神一样的伟大的可能既追崇又害怕的心理,叫做约拿情结或者约拿情意,它反映了一种‘对自身伟大之处的恐惧’。”
 人,是否真的有那么伟大吗?
人,是否真的有那么伟大吗?
我不知道。但易洛斯认为,这就是心理学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当追究人生失败的源头时,人们不再审视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社会环境和制度结构,而是理所当然地回到自己的内心——失败的感情、失败的工作、失败的育儿,都是因为我们的心理出了问题。你错误地成了你自身,所以改变也只能回到自身。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求助于心理学,在那里,人类的痛苦被分门别类、贴好标签,只要对症下药,我们的灵魂就会焕然一新。在她看来,这既是一种自由的幻想,也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和自助文化一起,成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
比如,“情商”之类的心理学概念本身表达了社会对于情绪合理化的强烈要求。“如今,情绪正处于新自由主义社会自我疗愈思潮的核心,它们被看作是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最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导致各种痛苦、不适应以及身心困扰的罪魁祸首,社会因此要求人们努力调节甚至掌握情绪。”
比如,自助文化不断鼓吹心理能力与经济成功之间的关系:一个人要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就必须具有强大非凡的自我。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你必须不断努力,你必须有创造力,你必须心智灵活,能应对无穷无尽的变化,这与资本主义经济提出的需求是一致的。无论从生产还是消费而言,它都希望人们选择一种利益至上、保持竞争力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心理咨询这个概念是从2008年汶川地震后开始进入大众文化视野的。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你会发现,心理咨询的话语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之中。很多时候,当我们思考我是谁,如何理解失败和痛苦,如何计划未来的目标时,我们已经默认了西方心理学关于人类行为模式的一些基本假设。比如在我们最为弱小的生命之初,隐藏着我们之后一生各种情感模式的密码;在一些微小的日常之物中,可能隐含着关于我们自身的重大线索;只要学会用坦诚的目光向内探寻,我们就可以不断接近自我与世界的真实……
但是,也许我们也应该问一下,到底什么是真实的自我呢?
曾经有人将抑郁症流行病归结于凝视自身过久——如果你过于关注自己的感受,一心想要找到自己,那么,当你最终意识到自身内部空空如也时,抑郁也就无可避免。有一则讽刺漫画是这样的:一个人上天入地寻找自我,最后在一个高山之巅找到了自我——一个西装革履的办公室职员。
自我提升的终点在哪里呢?
灵活的,可变化的,时刻想着提升和重塑自身的人,是流动性社会的理想人格,但未必是我们要去追求的。与其追求别人为你定义的成功和幸福,向内苦苦追寻所谓的自我,更勇敢的做法也许是承认自己的局限,我不想变化,我就在这里挺好。
社科院哲学所的学者李剑说:“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人生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遭到了环境的阻碍而无法得到发展时,我们可以减少或消除不恰当的自责与愧疚心情。若是那些我们无法成就的事情,其受阻的因素不是来自我们自身,我们就不应为此责怪自己,陷入懊悔与沮丧的泥潭。我们不为我们无法决定的事情负责。”
也许,我们应该为社会保留一些愤怒和苦恼,也为自己的灵魂保留一点困惑,一点脆弱,一点痛苦,一点平庸,一点不确定性,以及一点向外的好奇。毕竟,真相常常令人痛苦,美常常令人悲伤,爱常常让人撕裂,而所谓人生,按照日本童书作家佐野洋子的说法,“不过是平庸的人与平庸的人竞争,在竞争中产生的平凡的喜悦与悲哀而已”。
在《我和无聊亲密无间》一书中,她说自己小时候看儿子在游泳池里奋力游泳,再怎么努力也还是落在后面,于是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哪怕你没有一两种特别的才能,也要设法掌握三四种平庸的本事,对付着活下去呀。”
我也想这样告诉我的孩子。 弗洛伊德自我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