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古城:面、牛肉、合碗子
作者:吴丽玮 ( 平遥的一些饭店依据雷履泰80 岁寿宴的记载推出了创新的合碗子 )
( 平遥的一些饭店依据雷履泰80 岁寿宴的记载推出了创新的合碗子 )
面食108种
2001年,我第一次来到平遥。那年平遥办了第一届国际摄影节,我当时正在太原读高中,是作为志愿者幸运地被选来,待了三天两夜,印象中除了在一个老宅院里用蹩脚的英语向两个德国游客解释什么叫火炕外,基本没干过什么正经事。除了欢乐地跟同学去小吃摊上吃碗托儿、黄米炸糕和牛腰腰外,就是去买几粒真空包装的“一口香”平遥牛肉,站在“日升昌”门口晒太阳时,撕开一粒一口嘬进嘴里,放心地用任意一颗牙齿咀嚼已经软糯的粗壮牛肉纤维。
2014年元旦,我再来到这里。平遥与太原相距94公里,二者同处在黄土高原上的太原盆地,饮食上有很多相似处。在我看来,和太原现在已糅杂了各地风情的现代都市味相比,平遥是更具纯粹家乡风味儿的地方。它从明清时期基本形成了的饮食体系至今未变,平遥县文联主席赵永平对我说,由于晋商的繁荣,平遥在当时成了人和信息的一个交汇点,“食物上,尤其是面食,汲取各地特色的手艺特别丰富,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于是我寻找的起点就落在古城里家家都号称有的“面食108种”上。
108种的真假?“云锦成”饭店的总厨王英亮告诉我,几年前曾有顾客登门说:“你们把所有能做的面食都给我做出来,多少钱我都愿意出。”最后厨师们做出了三桌,每桌摆了15种左右,加起来没超过50种。“108种只是个约数,证明咱平遥的面食种类丰富。但同样一种面食,把白面换成高粱面、莜面或者荞麦面,做法、口味又不一样,这样算下来肯定超过108种了。”
当地人以“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山西面食在平遥”的“面食界地球中心”自居。山西是“小杂粮的王国”,玉米磨成的玉茭面、高粱磨成的红面、荞麦磨成的荞面、绿豆磨成的豆面、糜子磨成的黄米面,等等等等,农民家的面缸里塞着好几个口袋,每个口袋里是啥,伸手进去摸一摸就分辨出来了。
 ( 山西面食讲究的是制作者千变万化的手上功夫 )
( 山西面食讲究的是制作者千变万化的手上功夫 )
“面都有自己的性格,做法要因面而异。”王英亮说,“俗话说,‘四十里莜面三十里糕,二十里荞面饿断腰’。过去生活困难的时候,莜面是重体力劳动者的最爱,吃了耐饿。但现在人们已经没有这种需求了,莜面口感硬,一定要用开水和面,这样表面看起来是防止莜面变僵,实际上是用高温破坏其内部纤维组织,易于消化。”红面也是一种姿态强硬的食材,过去吃红面是粮食短缺时果腹的无奈,现在吃则是为了享受那种庄稼地的味道,有一丝丝甜,但更多的是清冽的草根儿味。王英亮说:“吃红面一定要配上豆面或者白面,再加入鸡蛋清,多加水调成红面糊糊,中和掉它本身的僵硬。”
馒头的香味
 ( 平遥人做面食的刀 )
( 平遥人做面食的刀 )
谁家做的面食最好吃?我向平遥县烹饪学会的副理事长邓瑞林请教,他编写了好几本介绍平遥美食的书,熟悉这里每一道菜的掌故,但这个问题还是把他难住了。面食谁家都做,谁家都吃,每个人念想的味道各不相同,相比之下也都“自谓抱灵蛇之珠”,互不服气。我决定先去寻找最熟悉的蒸馒头味道。上小学时,每天总要玩到饥肠辘辘才肯回家,有时正好赶上家里刚蒸好馒头,烟雾缭绕中,只听见妈妈烫手后的吸气声,再伸长脖子,就发现一锅馒头已经扣在案板上,垫在锅底的笼布还牢牢粘在上面。妈妈揪开笼布,先给我掰半个馒头,捧在手里第一步当然是先啃掉那层微微卷曲的光皮儿,不像馒头,更像粉条的滑溜和弹性。里面的馒头瓤更是蓬蓬松松,细细嚼总觉得里面是不是加了牛奶,这种香味唯独在出锅后半小时才能体会到,一旦馒头变凉,香味也会随着热气散去。
邓瑞林给我推荐了平遥县古城南门外的一家馒头铺。这家馒头铺只叫“纯碱馒头”,里外两间平房加起来十来平方米,里屋做、外屋蒸和卖,老板叫张敏,40多岁,她说因为使用的是天然的发面酵子而不是发酵粉,用“纯碱”二字便足以和其他店铺区分开。发面酵子是前日发面时所剩的酸水,配点温水,均匀地撒入面粉中。据面的状态酌情加水,少量多次,每次用手舀起一手掌的量,抹在面团表面的松散干涸处,直至面团变成一个湿滑发亮、软硬适中、分布着适量“蜂窝”的大面球。和面讲究“手光、面光、盆光”,为了不在容器上粘面团,活好面后她要把整团面从盆里抱出来,那团面略有稀松,一被拉扯,露出里面断裂、絮状的结构,皱巴、松软,仿佛抱的是一大团棉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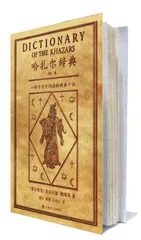 ( 压“猫耳朵”的剂子 )
( 压“猫耳朵”的剂子 )
冬天气温低,发面要在提前一天的中午准备,捂在棉被里直至第二天清晨。蒸馒头要起个大早,上午10点多就要基本蒸完。张敏和表妹王玲花同我们说着话,手上却一刻不敢停,今天除了散卖的馒头和糖包,还有一家摆喜酒来订了500个花卷,一个有小孩过12岁生日的家庭订了几个“括篮”。“括篮”是平遥当地的一种风俗,把面捏成图案,做成圆圈形状,封口的地方再捏一把锁,代表着对孩子长命百岁的祈福,蒸熟拿回家后,家长在中午12点准时把“括篮”举过孩子头顶,假意让孩子顶一顶后,再把“括篮”掰碎,分食。“括篮”是家中长辈的祝愿,张敏说,她见过最多的一家,一共为孩子订了50多个“括篮”,长辈们每人送孩子一个。王玲花手特别巧,她把面揉成条,拿刀在上面轻轻地砍出细密的纹理,两手一甩,面条卷在一起,拿起筷子从中间一夹,用刀再劈几个口子,一朵莲花就完成了。金鱼和兔子做得更巧,还是用砍出纹理的面条扭转成不同的形状,用刀切出金鱼的尾巴、用剪子剪出兔子的耳朵和嘴,再擀出一根细细的面条,卷成一朵花的形状装饰在小动物身上,最后用黑豆做眼,按进苍白的面里,金鱼和兔子立刻焕发了几分神气。
平遥人过年、乔迁、贺喜都喜欢蒸这种面食,既被用作祭祀,又是一种带着美好祝愿的馈赠。过年时,家中供奉的祖宗牌位被请到厅前的桌子上,略带装饰的花馍是主要的供品。如果有晚辈来拜年,长辈会从事先准备好的花馍中挑出一个送给晚辈,这些花馍大多表面镶着红枣,里面包着果仁,晚辈要全部吃完才算接住了长辈的祝愿。王玲花做完“括篮”,上锅的几笼馒头也蒸好了。烟雾缭绕中,馒头的表皮都炸开了花,张敏说,这才叫真正的手艺,馒头开花说明碱面放得正合适,碱大了,馒头发黄,品相极差,而且口感生涩,碱小了,馒头坚硬,一股酸味,只有开了花,馒头才保持适中的酸碱度,咬一口既松软又有嚼劲,随着咀嚼的增加,面的甜味伴着口水逐渐释放出来,嚼到最后变得越来越扎实。
 ( 开花馒头 )
( 开花馒头 )
面的手上功夫
曾有人用“拥出堆雪”来形容和面时的洁白柔软,小时候每到周末,爸爸都会亲自下厨做刀削面解馋,那面团也揉得如玉脂般细腻饱满。削面时人在锅前,一手托面,一手持削刀从上往下削,嚓、嚓、嚓,一刀赶一刀,那面条看似灵活轻盈,实际上是直直地被甩进锅里,削出的面叶儿中厚边薄,棱锋分明,嚼起来外滑内筋。费了一番工夫,捧出一碗热腾腾的刀削面,爸爸浇上西红柿鸡蛋或者茄子肉丁卤,先咬瓣腊八蒜,再滋溜溜吃进一大口,吃完必然大喝一声:“香!”
 ( 烟雾缭绕中,馒头蒸好出了锅 )
( 烟雾缭绕中,馒头蒸好出了锅 )
我认为不停地琢磨手上的功夫是山西人做面食和西北人的最本质不同。除了用刀,还可以用剪子剪,用筷子拨,用饸饹床压,甚至直接上手都是千变万化。平遥有种叫“揪片”的面食,把擀薄的面片拿在手里,用拇指和食指指腹的力量揪下一块比大拇指指甲盖更大一点的面片,揪面的动作朝上,这样更有利于在入锅的一瞬间对面片的薄厚做最后的雕琢。很多人爱吃揪片,因为它的表面积大,容易挂卤,但面片太厚口感不好,面片太薄又容易煮过了头,揪片的成败全在师傅的手感上。
面食做法的多元化是由现实条件决定的。山西地处高寒地带,蔬菜生产环节很薄弱,一般农家只是在庭院、垄间种瓜点豆,收啥吃啥,一年有数月吃不上新鲜蔬菜是平常事。长久以来,人们逐渐形成了重主食、轻副食的习惯,主食越做越精细,花样越来越多,这样只要搭配一定的副食元素,就能支持一个人的行动劳作。
 ( “猫耳朵” )
( “猫耳朵” )
桑勇师傅在古城外开了一家面食店,平遥面食如此丰富,桑勇却只做一种名叫“柳叶”的面条。他说自己的爷爷当年是阎锡山的厨师,从阎锡山还在忻州老家时就在身旁伺候,后来跟着到了太原,直到阎锡山逃往了台湾。解放后他爷爷对此犹恐避之不及,不敢再出手烧菜,后人袭来的也只有这柳叶面一道再家常不过的面食。“以前我们平遥人家都是祖孙三代同堂、叔伯兄弟不分家的大家庭,每天厨房要准备几十人的饭菜,但家里的劳力都下地干活儿,回来的时间没法统一。柳叶面就最方便了,擀好面摞好放一边,谁回来了给谁切几刀。面能放12个小时。”桑勇在擀面时揪起一撮玉米面,抖着手均匀地散布在面片上,一来防粘,二来下锅后会汤清面利。擀好的面片一层层卷在擀面杖上,拿菜刀顺着擀面杖切,面片劈落两半,再在中间横切几刀,把面片叠成厚厚的一沓。切面时,先提刀在顺滑的侧面切出一个个的棱角,再就着棱角切出一个个扁扁的三角形,乍看的确像幼嫩的柳叶形状。“我这个‘柳叶’是春天刚抽芽的‘柳叶’,可不是秋天已经老了的‘柳叶’。”桑勇切的面条只有三四厘米长,听起来是为了给面疙瘩增添生命活力的联想,实则是因为面条短小更容易制作出弹滑感。柳叶面的诀窍在于煮的时机,在铜锅里先煮汤,加入葱花、蒜末、酱油、花椒水、盐等作料,配上肉丝、白菜、粉条、海带、豆腐、土豆、木耳等副食,等水快煮沸时再开始切面,防止面静置后坨掉。切好后恰好水沸,面推进锅里,瞬间像飞进油锅的小银鱼,被水势顶起后翻滚跃下,面条挂着汤水,变成了仿佛被炸后的金黄色,锅中滚一分钟就要关火上桌,否则面的筋道和清爽就失掉了。这种饭、菜、汤合一的做法,客观上解决了蔬菜缺乏的困难。
面的风味也与卤的变化有关。王英亮给我列举了几种恰当的搭配:“擦尖儿面软,好消化,适合配素卤;红面剔尖儿口感硬涩,适合用肉卤转移视线;抿尖儿、手擀面容易挂汁,适合用黏稠的西红柿鸡蛋卤;猫耳朵形状小,可以把酸菜、豆腐干切成小块,一起用勺舀着吃更加方便。”对于我而言,对卤汁最敏感的是吃小吃的时候。山西各地几乎都有自己的特色面食小吃,浑源的凉粉、太原的面皮、清徐的灌肠等等,平遥有一种类似的小吃名“碗托儿”,是用白面和好浇入小盘中蒸制而成,所用卤汁是我最熟悉的味道。中学时,回家路上吃一碗凉粉曾是支撑我上完晚自习的最大动力,最后一节课时我们一起回家的几个女同学就开始窸窸窣窣地传纸条,约定是否要去小店里来一碗解解馋。我很爱那种浓稠的黑褐色卤汁,里面加了黄豆、腐竹和海带,酸、咸、辣,还能闻到大把鸡精在里面,那是属于不用考虑健康养生话题的年轻人的味道。每一块凉粉都要在卤汁里甩来甩去,贪婪地想尽量多沾上一些浓汁,凉粉送入口中,细细咀嚼,让卤的味道充盈在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待卤汁味快要消失的时候把凉粉一并吞下去,时机恰好。
 ( “括篮”是为平遥过生日的孩子准备的,拿在头上顶一顶,再掰碎、全家分食,寓意孩子可以幸福平安地长大 )
( “括篮”是为平遥过生日的孩子准备的,拿在头上顶一顶,再掰碎、全家分食,寓意孩子可以幸福平安地长大 )
平遥人有几样做面神器,最有名的叫作“擦床”。擦床体形庞大,如同木匠用的刨子,两头是木条架起的框子,中间是一块凸起的铁皮,上面均匀分布着鱼嘴状的小口。使用时,把擦床架在锅上,把面团使劲压在铁片上来回搓,经过小口的面团擦成带毛边的小块,直接掉进煮沸的锅里。擦床反映的是平遥传统民居的特点。老平遥人住的是有黄土高原特色的砖砌独立式窑洞,普通人家一进门,正中是客厅,两侧厢房里,火炕几乎能占到屋内面积的四分之三,睡觉、起居、饮食几乎都离不开屋内的火炕。做饭的锅灶和火炕连为一体,做饭的灶还起着烧炕的作用,灶大锅也大,巨型的擦床才能稳稳地架在锅上。平遥县文联主席赵永平对我说,灶台及通向火炕的通道叫作“直洞”,直洞最终会通往烟囱,通过空气流动来旺火。火炕的下面是纵横交错的通道,叫“花洞”,花洞的目的是将做饭的热量传递过来,提高炕的温度。“直洞上温度特别高,如果不小心坐上去烫得屁股都疼,花洞的温度较低,可以用来风干粮食和枣。‘炕’在我们这里当动词来使用,可以‘炕枣’、‘炕玉米’、‘炕面’,把绿豆泡上,放在炕上能生出绿豆芽,过年时候就多了道凉菜。”
灶火关系到饮食起居,因此当地人对祭祀灶神倾注了更多的情感。平遥女子诗社的张月玲向我回忆小时候家里祭灶神的情景:腊月二十三,灶王爷的神龛立在灶旁,两边贴上对联以示恭敬,祭祀活动要由家中的全体男性来完成。“除夕时要把小米煮至不太软熟,用笊篱捞出控干水分,放进一个花碗里压平压紧实,里面再扣进核桃、枣和其他干果,用来供奉灶神及祖先,这饭要放5天,到正月初五的时候全家一起吃掉,象征吉祥。”
 ( 面食的不同性格决定了与它相配的卤汁味道 )
( 面食的不同性格决定了与它相配的卤汁味道 )
熟牛肉和熏肉手艺
到了平遥,必寻的是平遥牛肉的踪迹,它是太深刻的印象,几乎是山西人逢年过节必备的最高档熟肉。在南方,牛肉大多风干处置,撕咬是一种体力,也是一种勇气,大快朵颐之后,后槽牙往往因用力过猛而酸疼不止。平遥熟牛肉却是一种温存的呈现,粉红色的肉块纹理分明,一条条半透明的肉筋镶嵌其中,需要担心的并不是你的后槽牙,而是你的刀工,无论你切得多薄,软糯的牛肉却怎么也不会松散倒塌,至多是卷起个卷来,像一张揉皱的纸。牛肉入口咸味十足,软糯的纤维很快在口中散开,有时还能先嘬出几口肉中的汤汁下肚,接着再嚼一嚼牛肉丝,再散出一抹咸香味。在市场上时常能买到小包装的牛肉,这就成了随身携带的零食。我上大学后,有时它还成了随时补身体的滋补品,每天掏出一两块,补上学校食堂里匮乏的油水,那个小小的锡纸包总让人意犹未尽,最后趁无人注意,还要把舌尖伸进去舔一舔留在里面的牛油凝块。
 ( 烧肉是平遥传统合碗子中必备的一道菜 )
( 烧肉是平遥传统合碗子中必备的一道菜 )
但在平遥城里这赫赫有名的熟牛肉手工作坊一点都不好找。已成为著名品牌的“冠云”牛肉早已实现了大型工厂化生产,其他几家略小的厂家也都使用蒸汽锅一劳永逸地解决从煮到焖的所有过程。在城里城外转了很久,终于在一间小小熟食店里遇见了王金铭,他的爷爷曾经在老字号“兴盛雷”牛肉铺当伙计,学得一身手艺后传给了儿子,又传给了孙子,现在王金铭和家人在古城内外开了几家熟食店,卖的是以猪肉为主的熏肉,但实际上使用的仍是老“兴盛雷”牛肉铺的方子。
王金铭的加工厂在沿村堡村里,距离王金铭的外甥闫忠日家不远。1992年初中毕业后,闫忠日开始跟姥爷王永仁学做肉的手艺,现在他负责监督作坊里的生产,并给几个零售店送货。村子还笼罩在微熙晨光中时,作坊里已经开始忙乎了。猪肘子、猪蹄、猪脸、猪耳朵、口条分堆摆在案板上,伙计们依次用叉子叉起肉来,伸到蒸汽锅上火烤燎毛。之后经过几遍清洗,开始对肉块腌制处理。闫忠日戴着手套,把大把粗盐均匀涂抹在猪肉上,反复揉搓,促盐融化,有些地方觉得太厚,用刀划开,手带着盐伸进去结结实实再抹一遍。老传统中原本使用平遥独产的硝盐,但现在已被国家禁止使用,换成了普通食盐加入适量亚硝酸钠代替。涂抹后入缸的顺序也极为讲究,先厚后薄,分层入瓮,不加任何作料,最后用猪肚封顶,空气就被完全隔绝开了。“过去要求把盛肉缸放在冷窖里腌制,夏天腌5~7天,春秋腌10~15天,冬天腌20~30天,中间还要把肉块翻动两三次,但现在求快等不到那么长时间,所以就改了腌制时加水的工艺,改成只用盐渍,让水分尽快析出,让盐分渗进去。”闫忠日边说边开始准备卤煮的工序。大煮锅里添上了原存老汤,再添水大火烧沸,腌制好的猪肉放入锅内,不加锅盖,急火大约煮一个半小时后,眼见着猪油一点点地开始凝聚在表面,闫忠日拿着叉子开始翻肉,有些已达到软度的肉块先取出搁置一边,“肉龄不同的猪肉成熟速度不一致,收缩、变软的猪肉就是已经煮熟了的”。大约再过半小时,肉都基本成熟,这时所有的肉全都推回锅内,依靠表面四五厘米厚的肉油做顶盖,包裹着渗不出来的蒸汽,肉焖在锅中两个小时后卤煮过程才算结束。
 ( 熏肉和传统的平遥牛肉做法接近,只是在煮过焖过之后再以柏树锯末烟熏 )
( 熏肉和传统的平遥牛肉做法接近,只是在煮过焖过之后再以柏树锯末烟熏 )
平遥牛肉的制作过程到此基本完成。闫忠日说,牛肉的脂肪含量少,无法再承受烟熏过程,所以熏肉大多只选猪肉。把柏树锯末平铺锅底,架上篦子,盖上锅盖,点火用烟来熏肉,不一会儿作坊里就会呛得人受不了。熏好的猪肘和猪蹄格外特别,颜色棕红,烟火气十足,吃到嘴时,立马想起那种专属于灶间的气息。
王金铭的堂弟王天明在“冠云”牛肉厂上班,他是平遥牛肉第七代传人,师从第六代传人雷时雨。王天明对我说,自己的手艺最多的还是从父亲那里学的。王天明和王金铭是同一个爷爷,爷爷的几个儿子手艺各有侧重,王天明的父亲擅长屠宰。平遥的牛肉大多来自山西北部或内蒙古,制作平遥牛肉的牛,必须非病非残、年龄不小于4岁,体貌呈长方形或圆桶形,体形宽厚,胸前端、尾根部两侧突出丰满,体重不低于300公斤才可入选。屠宰是平遥牛肉的一大关键,王天明说,宰杀肉牛,讲究净、静、稳,宰前禁食三日,只给肉牛喝盐水,宰时要在牛的脖颈上长拉一刀,割断两根主动脉血管,让牛血尽快放尽,尽可能不会渗入体内,屠夫需眼明手快、手起刀落,防止牛过度惊慌,因肌肉纤维猛然收缩而肉质坚硬。
 ( 平遥“长昇源”黄酒第七代传人郭林成。明代崇祯年间“长昇源”创立于古城金井市楼下,慈禧逃往西安途经平遥时曾作为御膳用酒 )
( 平遥“长昇源”黄酒第七代传人郭林成。明代崇祯年间“长昇源”创立于古城金井市楼下,慈禧逃往西安途经平遥时曾作为御膳用酒 )
王天明接的是父亲的班。父亲当年所在的单位是国营平遥县食品公司,1995年改建成公司建制。平遥县食品公司是在1954年由38家县城近郊的牛肉作坊组建而成的,这其中有几家还是明清时期的老字号。
随着明代晋商“货通天下”的发展,平遥开始云集各地商贾,当时已有的平遥牛肉借势随着商路远销口外,但当时的储藏条件十分简陋,需要将腌制的牛肉卷成肉卷,夜间将肉卷放置在席帘内,冻好后放在简易冰房里,运销时将肉包严,快速运往各地。到清嘉庆年间,平遥开始有了较为规范的作坊。先是雷全宁在文庙街开设“兴盛雷”屠宰场,后有任大才、任仰文父子在西大街设立的“自立成”牛肉铺,西郭村韩来宝在南门外创办的“隆盛旺”牛肉店。1900年庚子之乱,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西安,途经平遥时,知县沈世爃献上的第一道凉菜便是这“薄如纸片”的“兴盛雷”平遥熟牛肉。慈禧太后觉得这肉醇香细嫩,颇有好评,于是平遥牛肉名声大噪。
赵昌本退休前是晋中市考古所研究员,被称为平遥县的“活字典”。他告诉我,1370年平遥城的城墙向北、向西都分别做了扩展,扩展后,城内的北部一直鲜有人居住。“城墙角下原本就是古战场,人们都不愿意住在那里,所以就长久空着。‘兴盛雷’开了后,在城内的西北角上建起来屠宰场,并且打了一口井用来卤煮牛肉用,这口井的水后来一直用来腌制牛肉。”一直以来,平遥城下高硬度的碱性地下水被认为是平遥牛肉之所以好吃的关键。很多师傅身怀加工绝技,被高薪聘至异乡,却怎么也做不出原汁原味的牛肉,于是清朝有诗人写道:“苦柑生北地,蜜橘出南方。水土两相异,牛肉平遥香。”
加工肉的工艺在不断改进,但有些老传统却再也找不回来了。赵昌本说,几十年前的熏肉是用柏树的锯末和树枝配合着来熏的。树枝是秋天从树上摘下来的,人们称为“活枝”,锯末相对的就叫“死树”,两者熏出的味道有明显的不同。但现在不可能大规模地掰下树枝,人们只用简便、环保的锯末来熏,味道就和赵昌本无法忘怀的解放前古城熏肉老味道有了差距。他当时是十几岁的孩子,家住城隍庙街以南的巷口,那时古城里有好几家熏肉铺,隔着50米外就觉得香气四溢,“那味道一辈子都忘不了”。赵昌本现在说起来仍忍不住吞下口水。“每个铺面上放着的肉都不多,但肠子、肝、肚子、猪脸、口条一应俱全,那时哪怕是买两三块钱的肉都行,店主会耐心地切下一小块肝、一小块肠、一小块猪脸,几乎每样都给你来点,每种切得仅比纸张稍厚,用白纸叠成一个漏斗形状,把肉片放进去,把纸包成一个纸包。再买个烧饼拿回家一起吃,香极了。”
绵软的合碗子家宴
过了小年,平遥人家就开始忙着准备合碗子了。合碗子是平遥人提前备好的过年菜肴,用土陶碗蒸上各种半熟的肉食,每种肉食蒸好几碗,做好后敷上保鲜膜放在窗户外、院子中间的空水缸里,逐渐风干。吃的时候只需回锅一蒸,扣在盘子里就可以直接上桌了。
合碗子品种多,做起来麻烦,刚入腊月,谁家也没想着这么早就开始动手。好在有一家名叫“丽泽苑”的酒店已经开始准备年夜饭宴席了,厨师长董强强给我们展示了他制作合碗子的功夫。去找董强强时,他正在一块膘壮的后腿肉上片出层层叠叠的肉片,整块的红肉片下来做酥肉,小块的留着做丸子。合碗子的品种并无定式,但必不可少的是肘子、烧肉、大肉、酥肉、丸子、酱梅肉等几道荤菜。因为每一种都要准备若干份,即使对于有经验的主妇来说,这也绝对是年前最忙乎的一件大事。
肘子先用热水紧一下肉皮,再用火钳子叉着,在火焰里燎掉猪毛,接着放进糖水里,加葱、辣椒、花椒、大料,用小火慢炖半个多小时。烧肉选择的是腰上的五花肉,在油锅中炸至上色后,投入沸水中大火煮,直至表皮鼓起一个个油淋淋的小泡。酥肉要裹着加入鸡蛋的面糊下锅烹炸,董大厨的助手将炸过的酥肉交到大厨手中,董大厨片片切下,发现肉中间还在渗血水,马上叫助手回去重新炸了一遍。
肉的配料主要是土豆和炸豆腐。两小时后,煎炸炖煮的各色肉食逐渐完成,董大厨把肉切成条块,猪皮朝下,整齐摆好,最上面摞着炸过的土豆和豆腐,配上葱段、姜块、辣椒和大料,再撒上盐,放进蒸锅里蒸半个小时左右。因为食用前有一个扣的环节,所以现在的摆盘十分重要,一个小助理摆西兰花时不够精心,董大厨端起碗倒出菜来,像复原一颗西兰花似的小心翼翼地把它码放整齐。
山西人喜食软食物,合碗子的烧肉绝对是烹制至入口即化的程度,酥肉、丸子等也都要保持松软滑嫩的口感,古城里还有一些酒店所走的是雷履泰家宴路线,所选食物就更加绵软了。雷履泰是平遥第一间票号“日升昌”的首任总经理,堪称山西票号的鼻祖。雷履泰80岁时,厨师曾为他办过一次盛大的寿宴,席上所做皆为软烂松软的食物,但具体的菜肴并没有留下记载。一些饭店揣测着雷履泰当年的寿宴情形,推出了羊肉、山药、南瓜、小米等为主的雷履泰合碗子家宴。这其中,山药是平遥本地最有名的特产。平遥山药仅生长在岳壁乡内,尤以西源寺村的山药为最佳。赵昌本分析说,这可能与当地的水质有关。西源寺村紧邻着惠济河,当地传说这里有一弯神池,因此生长的水稻特别好吃,一粒粒都是水晶晶的。“大跃进”时为了大炼钢铁,神池的水道被挖断了,种出的水稻就再没有了曾经的辉煌,但这里种山药依然比别的地方品质好。西源寺村村民李毓志是村里第一个种山药的人,他发现村里的地和其他村的不太一样,“土质砂,可以蓄水,同时山药生长还不受限制”。我们去看李毓志家的山药地,白露后挖完的最后一垄土坑还没被填上,一群羊在地里吃食,幸运的话能挖到一棵干枯的小山药吃。“山药只能在春天上点羊粪,不能上化肥,否则温度太高会烧死山药苗。挖山药也是个辛苦活儿,只能靠人刨开一点点找,稍不注意就把山药挖断了。这是个脏活儿,挖完连人带山药全都是土。”自然生长的平遥山药果然口味不俗,又沙又面,适合蒸着吃。我们在李毓志家的火炕上烤山药吃,烤好后把皮一剥,山药就像一座小冰山一样,不太整齐地立着,但吃起来真是软糯。
合碗子是平遥主妇烹饪技能的评测标准之一,卖相、口味欠佳的合碗子会让主妇失去颜面。合碗子扣进碗里后,还有最后的关键一步,那就是浇汤。这汤是用捣碎的猪大骨和鸡肉在水中煮三四个小时后烹调出的高汤,关火前加上葱花香菜,浇在热腾腾的烧肉合碗子上。邓瑞林说:“客人上桌,先喝汤,汤做得好,才能说明主妇手艺高超。与汤相比,肉都在其次了。”
(文 / 吴丽玮) 牛肉平遥古城平遥牛肉美食平遥烹饪技巧古城揪片面食合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