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醉蟹
作者:王恺(文 / 王恺)
 ( 上等的醉蟹,不仅仅螃蟹重要,酒也很重要。选择黄酒或者米酒,最后风味完全不同。图为“成隆行”准备用黄酒制作醉蟹
)
( 上等的醉蟹,不仅仅螃蟹重要,酒也很重要。选择黄酒或者米酒,最后风味完全不同。图为“成隆行”准备用黄酒制作醉蟹
)
随着蟹价的昂贵,一般的人家已经慢慢放弃了自家制作,总觉得这不是正经菜。本来“长三角”的殷实人家会在蟹季或醉或腌,甚至酱制大批的螃蟹,现在几乎绝迹了,要吃上好的醉蟹,只能依靠专业厨师的手艺。
不过也有不是厨师而擅做醉蟹者,去苏北兴化的中堡镇,汪曾祺提到过的“中庄醉蟹”居然还在,镇上的化学老师现在主持打理着一切;而上海一位普通的主妇汪姐的醉蟹,随着一部纪录片的热播而成为名品,无数人上门,其实只是想回味那股家常的味道。
来,醉一只大闸蟹
“不过汪姐醉的是毛蟹,还不是大闸蟹,鲜是鲜,可惜太家常。”“苏浙汇”的总厨朱俊说到现在上海声名在外的汪姐家的醉蟹。自从《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去汪姐家吃饭需要排队的时间就更长了。到了,不能点菜,她当天买的什么就是什么,价钱,也是她来随口报,这种大厨娘的风范,都快到顶了。
大家蜂拥而来,想吃的最多的还是醉蟹,汪姐的醉蟹是电视里特写镜头最多的。拍摄的编导张铭欢回忆说,当时汪姐还只是小圈子里出名,来吃的仅限于朋友,她自己负责处理一切。去菜场挑螃蟹,会挑那种特别活的,一买上百只。买回家,放在自己家的大浴缸里一只只洗刷。就是这个场面让编导感动。这时候还只是六七月份,螃蟹刚褪了壳,俗称毛蟹,有点黄,腿肉虽不丰肥,可是也鲜味已经具备,有耐心的话,一点点从壳里剥出来,半透明的一小条。拿在指尖,像哆嗦的凉粉,可是凉粉哪里有这股鲜甜。
 ( “成隆行”制作秃黄油时,蟹黄(左)和蟹膏(右)的比例是4∶6
)
( “成隆行”制作秃黄油时,蟹黄(左)和蟹膏(右)的比例是4∶6
)
这个季节的螃蟹,上海人多是买回家做毛蟹炒年糕,或者是做醉蟹。朱俊也是上海人,说起这道家常菜,回忆中充满日常的温热气息。都是家中女性长辈操刀,醉蟹拼的不是技术,而是耐心:买回家的毛蟹洗刷干净,用高度白酒浸泡,刚放进去的时候,螃蟹吐泡的声音还能听到,过了一段时间才渐渐消沉,悄然无声,也不一定是死了,很可能只是醉得晕了过去。有泡得长的,也有几十分钟就捞出,放黄酒酱油冰糖料酒和花椒,特别讲究的放茱萸。据说可以经久不坏,不过多数主妇应该都不知道茱萸是什么了。
这种醉蟹,制作不复杂,放上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吃了,因为个头不大,所以目的不在吃肉,而纯属吃那点鲜味,是早上过泡饭时的最佳伴侣。也有人站在黄泥螺一边,认定清晨泡饭的最佳伴侣是泥螺。不过这个讨论当然局限于上海人,最多加上沿海地带的江浙地区之间,因为外地来客很难欣赏这种有点甜有点腥但是没什么大实质内容的小佐餐物。就像他们同样不理解上海人为什么爱吃海瓜子,花那么多时间去吃个没有干货的鲜味,这确实是只有吃得精细的地区的居民才能理解的饮食乐趣。
 ( 陈宝全是制作蟹菜的高手,他会盯着制作秃黄油的整个过程,不让旁人插手
)
( 陈宝全是制作蟹菜的高手,他会盯着制作秃黄油的整个过程,不让旁人插手
)
随着螃蟹价格的逐渐高昂,包括鱼塘养殖蟹的大规模流行,从正反两方面刺激醉蟹逐渐从家庭菜谱中消失。偶有购买,但是那味道和自己家制还是有很大差别。汪姐的醉蟹之所以流行,一个经常光顾的熟客对我说,不是因为她的菜好到哪里去,或者难到哪里去,为的就是那股家常菜的味道。家常菜并不是一味平淡素朴,而是也有用心良苦的,一个女人,为买几百只螃蟹要上多个菜场精挑细选,然后放在自己家洗澡的浴缸里清洗,这就是心意。
朱俊所供职的“苏浙汇”主打的是江南菜,醉蟹当然少不了。这家餐厅选材十分广泛,像他们的清蒸鲥鱼就是选择的美国鲥鱼,而螃蟹的挑选也走出了长江三角洲,选择了广西南宁膏蟹,这种蟹的特征之一就是黄多,甚至充满了整个后盖,个头也大。朱俊他们的标准是选择一斤左右的,然后在醉的过程中会放一些别人不太添加的东西:老陈皮、白兰地。尝试新材料,反倒能做出不一样的口味来。这个酒醉膏蟹至今还是这家餐厅的四大名菜之一。
 ( 醉蟹是“成隆行”的招牌菜之一
)
( 醉蟹是“成隆行”的招牌菜之一
)
因为吃得太多,朱俊和他的一帮子厨师长朋友们聚集在一起,又弄出了新花样。“你知道哪种最好吃?醉大闸蟹,选三两半的母蟹,要不就是四两以上的公蟹,如法炮制,那个鲜甜。”大闸蟹所做的醉蟹,味道比起南宁膏蟹要鲜美许多。“本身湖蟹的鲜就是不一样的,吃南宁膏蟹,吃的是肉多黄多的满足感,还有就是黄流油,加酒腌后特别甜,但是鲜美程度是比不上大闸蟹的。而毛蟹呢,包括六月黄,肉又太少,加上那时候肉没有长成,往往只有点鲜味,基本上都是骨头,没什么可吃的。”就因为吃刁了嘴,他们几个现在开始做大闸蟹的醉蟹,今年你做,明年我做,轮流做东,不多,也许就是一坛两坛,吃客局限在小圈子里。“全都是嘴吃刁钻的老食客。”这么一来,这点醉大闸蟹,倒像是隐藏在上海厨师圈子里的武林秘笈。
醉蟹的几种方式
 ( 太湖螃蟹 )
( 太湖螃蟹 )
成隆行的柯伟就是这群好吃的厨师圈子里的一个。起源还是因为自己的好奇心。最初是每年醉100只大闸蟹自己和朋友分享,现在来要的人越来越多,才开始一年做上几千只,装箱出口。“一般人吃螃蟹,是到了季节吃个几次;从前大户人家过了蟹季,还想吃螃蟹,怎么办?就想糟、醉,还看到古谱里写酱蟹的。”
《养小录》是清朝顾仲写的饮食专书,代表着江南大家的饮食之道。说到藏蟹,开宗第一句就是:“雄不犯雌,雌不犯雄。”雄蟹和雌蟹一定要分头储藏,否则就会“沙”,蟹黄不能像咸蛋黄那样发沙,味道就不好了。必须软和糯。书里说这是明朝南院的名妓所传的方子,屡次尝试都不错。
 ( “成隆行”做秃黄油的蟹油用螃蟹和豆油炸成 )
( “成隆行”做秃黄油的蟹油用螃蟹和豆油炸成 )
老柯说他们自己试验过许多次,一发沙,就觉得陈了,失去了醉蟹的鲜美。《养小录》还说:酒不犯酱,酱不犯酒。就是用酒醉蟹的时候一点酱都不能沾,反之亦然。不过现在酱蟹已经失传,老柯和苏州的叶放他们都去民间搜索过,几乎没人做。其实做法很简单,就是用上好的甜酱把活蟹包起来,然后储藏,两个月后开罐,壳很容易就去掉了。“怎么就失传了?不知道。要不当时就是只有几个大家族自家制作,所有外面也不流传。”
倒是醉蟹,在民间开花散叶,渐渐成了各种流派。主要有宁派和苏派。宁波人爱吃糟醉食物,而且用得是浓汤糟醉,酱油、糖外加腌料和黄酒,拿出来的时候红彤彤的,看起来像熟了一样。老柯说自己不太喜欢,而且宁波人喜欢做海蟹,湖蟹的糟与醉倒是苏州人在行,所以他们最后选择了用苏帮做法来做大闸蟹。“虽说是家家户户都做的东西,但是不在行,做出来还是不一样。”虽然和自己手下的大厨一起动手,可是刚开始还是做坏了不少螃蟹。“不知道用什么罐子腌,开始用瓦罐,有一次醉完了,没过几天就坏了,螃蟹全都浮在上面,个个都发空。”后来用了装黄酒的坛子,才对了路。大概是这坛子本身就能透气,太密封的效果反而不好。坛子选对了,用什么酒的问题是第二个,试验过白酒,和传说中的苏北做法一样,结果太猛烈,不得其蟹味。古书上记录是用苏州的三白酒,一种米酒,可是老柯他们总觉得现在的三白酒并非古法,所以废弃了三白酒,还是改用黄酒。“做了几年方才做成功。”现在这道醉蟹,是他们店的招牌菜之一,开设在虹桥路附近的他们自己家的蟹庄,用的是陈香梅家的老宅子,陈香梅有年回来,看到房子没什么感触,大概她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吃到老柯他们的“上海醉蟹”,倒是大发了一通感慨。“不过最厉害的不是她,是台湾的一位女明星,一个人来,默默坐在一个小包间里,一个人,吃了八只醉蟹。”这个女明星,老柯本来也没看过她的多少戏,可是这食量把他吓住了,让他永远记住了她。因为放的黄酒不多,掺杂了若干白兰地,所以醉蟹颜色如活蟹一般,刚端上桌的时候,壳是活螃蟹的青灰色,蟹脚上还有一些没有全部掉的绒毛,只从脐部隐约透出的黄看出来这是一只已经醉透腌好的螃蟹。那女明星在别处基本吃不到,索性一次过足醉蟹的瘾。“实在看不出来,她平时是以演文艺女青年出名的啊。”老柯笑得跟什么似的。
 ( 在太湖里饲养的螃蟹都用小鱼小虾来喂养,有种骨子里的甜味 )
( 在太湖里饲养的螃蟹都用小鱼小虾来喂养,有种骨子里的甜味 )
醉蟹等于是活蟹的生制品,所以老柯他们最害怕的是不卫生,怕细菌超标。“过去都是自己吃,不要紧,拿出来销售就不行了。”活蟹买回来,挑选白底板的,这种蟹健康和强壮,本身就带的病菌少,先放在清水里养几天,过去是喂蛋清,让它们吐尽肠肚中的泥沙,现在是喂一种催吐剂,老柯强调,是欧盟标准的药品。
养好后,肯定离不开白酒,用白酒杀菌。“我们用的是五粮春,白酒不仅仅是杀菌,还能增香。”所以舍得投好酒,为了整体效果,觉得不能省在料上。白酒不仅是清洗,还要喷淋,一道道下去,这螃蟹基本已经不会动了。不过,肯定还活着,偶尔动动爪子,显示自己的生命力。之后是将之放进配好的料中,放进冷库中一段时间,就可以吃了。
 ( 醉好的螃蟹放入罐头瓶内包装好
)
( 醉好的螃蟹放入罐头瓶内包装好
)
说到料,也麻烦。“酱油用广东的,冰糖要水晶的,陈皮是香港采购回来的老陈皮,黄酒一般用八年陈的绍兴酒,最关键还要加白兰地。就像画龙点睛,不加就觉得欠缺一点味道。”料都要烧开,熬的火候要有拿捏,大厨要坐镇,过去也就是家庭主妇的菜肴,可是餐厅要推出来,是创牌子的事情,只能细心。“馆子菜,还是要有一亮相就惊人的效果,否则怎么延续下去?”这道醉大闸蟹,前两三年还是试验,到现在才固定配方,虽然是一群厨师最初一起交流的结果,现在却各家保守机密,味道也微有不同了。
老柯现在每年做3000只左右的醉蟹。“还是个精细活,没办法大规模量产。何况原料价值也不便宜,三两多的螃蟹今年的价格一斤就上百。过去醉蟹是被当作家常菜的,现在醉大闸蟹一般家庭也舍不得随便吃,买的人不多,反倒是郑重的大菜了。”基本上都是买回家摆碟做冷盘的;或者干脆就当主菜,专门请客,醉蟹配陈年花雕,一冷一热,基本上是一种半精致半随意的名士范儿。醉的大闸蟹摆出来,哪怕就仅仅一个冷碟,也不丢人,无论是体积还是色泽,都属于上乘酒友:先吃腿,剪开口轻轻一吸,半透明的腿肉就暴露在空气中,比起那些拆好的蟹粉,醉蟹肉实在是艺术品,像活的,味道却都已经进去了,酒香和甜醇混合,是稀少的味道,众多的味型中缺乏的一味。
 ( 化学老师出身的张大友,把有关知识用到醉蟹制作中,结果螃蟹保存时间更久,更加鲜甜
)
( 化学老师出身的张大友,把有关知识用到醉蟹制作中,结果螃蟹保存时间更久,更加鲜甜
)
因为醉蟹的汤料鲜美,有北方的大厨买醉蟹回去,吃完蟹不丢汤,而是用来泡鲍鱼。“也好吃,不过鲍鱼厚实,所以那时间等得更久,等到汤汁味道都进去才能食用。”
老柯是个喜欢玩的人。把自己家的醉蟹定型了,还想多些螃蟹的美味:于是每天拿食物玩游戏,比如用醉蟹的膏子做心,外面包上一层牛油果冻,像个小小的皮蛋,是他们尝试的新鲜冷菜。还用盐和高度白酒来锔螃蟹,客家菜的烹饪法则,食材则是完全江南化的。这种咸鲜蟹的肉质白嫩,与醉蟹的透明又是不同的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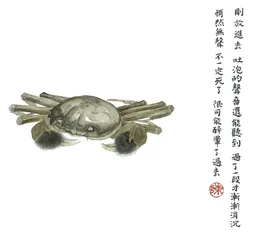
蟹宴好玩。因为材料贵重,所以每家尝试去做的方法虽然不同,但珍视的态度是一样的。苏州名士叶放一直也在自己家恢复蟹宴,全部用曲牌名做成菜名,作为冷盘的醉蟹名字是“将近酒”,也是当作一道下酒好菜。苏州醉蟹也是配方多样化,他找的大厨喜欢钻研,配料里加的不是糖,可是照样很甜鲜。“一是原料好,二是从苏州众多的蜜饯果子中挑选一二,入了配料中,自然而然多了甜味。”
这道苏州的醉螃蟹,叶放他们配酒也配茶,一样有股别致的滋味,因为都属于慢享系统,可以吃上几个小时也不厌烦。蟹宴的好处,不仅仅在于吃喝,更是在于玩乐,所以,雪花蟹斗成了“醉花阴”,蟹黄豆腐成了“青玉案”,边吃边猜哑谜。
中堡醉蟹:隐藏在古镇的秘密
如果不是汪曾祺在他的小说和散文里始终提到苏北小城兴化的醉蟹,大概这种地方名产就被彻底遗忘了。连老柯这种见多识广的吃客也只是说,苏北醉蟹用白酒和盐,不好看,也并不好吃。
在如果不是去了兴化中堡镇,也许真就错过苏北的醉蟹了。醉蟹在苏北日渐式微,甚至在兴化县城都难以吃到。这个旧属扬州的小县城保持了若干精致生活的痕迹,例如早茶:主要食物是蟹黄包和笋丁包,滚烫的,都属于现包现蒸的产品。有兴化特色的拌干丝,用嫩姜片和卤汁拌,放白糖,就当地的炒青绿茶,有股子意想不到的鲜味。晚餐是隆重的,醉虾醉螺,包括硕大的昂嗤鱼炖汤,就是没有醉蟹。问厨师,犹豫地说,从前有过,现在是好久没人吃了,当地人觉得不划算。“吃醉虾吧,味道更好。”现成的当地青虾,壳是青蓝色而不是青灰,据说产量占到全国的1/10。个个肥壮,用白酒和卤汁现场浸泡,端上来用舌尖剥开壳,明白为什么青虾被称之为“小玉”,不透明,但是筋道密实,有质感。不过这种现场的醉河鲜只适合小物,比起长时间浸泡的醉蟹,自然是不同。
中堡镇离县城还有30公里,从前这里到县城只通水路,现在有一条田埂扩张成的水泥路,两旁还是湖泊为主,连绵的小水塘,就是当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这里就是传统的里下河地区,一直以来,依附的是富庶的扬州,出售当地物产。水产的丰饶是有历史可查证的。汪曾祺有篇小说写扬州画家金冬心请客,冷碟是十几样,完全按照当年扬州盐商请客的规矩,单子写在纸折上:“金华竹叶腿、宁波瓦楞明蚶、黑龙江熏鹿脯、四川叙府糟蛋、兴化醉蛏鼻、东台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糟鹌鹑、糟鸭舌、高邮双黄鸭蛋、界首茶干拌荠菜、凉拌枸杞头。”有醉蟹,不过还不是当地的,而是苏南的。兴化拿出来摆盘的,是醉蛏鼻,还是小河鲜之类。
汪曾祺也确实写过兴化的醉蟹,简略的几段话,说是用陶罐装着,上面封着大红的纸条,逢年过节拿去送礼,有种特别乡土的美感。
如果不是遇见张大友,就真错过了兴化醉蟹。早年中堡镇做醉蟹的人多,几乎就是家庭制品,可是随着食品加工业的规范化,这种生制水产品越来越难拿到国家批文,只有那种特别明白的人,才能将醉蟹的生产工业化,维持下去。但工业化还要保证原来的自然的鲜甜的风味,这就难了,张大友的作坊就是如此,所以,那块得过江苏省著名商标的“中庄醉蟹”也就归属于他的企业。镇上人提到他的时候,都带了几分钦佩,那钦佩里又有点小不满:为什么就他成了气候?
中堡镇水路四通八达,随着城镇的现代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古镇的感觉,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乡村。如果不是湖泊众多,还真乏味。张大友有个腌蟹作坊,就靠近著名的蜈蚣湖边,这个湖泊和大纵湖合成南北湖,是里下河地区的著名湖泊,产的就是最著名的苏北簖蟹。虽然苏州的叶放他们这批美食家看不上苏北别的地区的螃蟹,但是对这两个湖泊的螃蟹网开一面。“所谓的簖,是一种渔民竖在水里的工具,到了季节的时候,湖里的螃蟹往河里爬,一个个从簖上翻下来,能爬上去的,都是健康雄壮的,其实和大闸蟹没什么区别。”
张大友的醉蟹,就是选用这些簖蟹。他从前是镇上中学的化学老师兼语文老师,对自己转行做了醉蟹总有几分说不出的感觉:“特别简单,就是腌咸菜似的,算不上什么本事。”所以他对当地镇上资料里写的中堡镇醉蟹的要70多道工序,包括拿过什么南洋博览会金奖之类宣传材料不屑一顾。“哪里有千年历史,整个中堡镇的历史有没有那么久啊?”张大友有种当过老师的讲求实际的精神,对我讲述了一个更可靠的醉蟹起源:兴化当地产的甜米酒和簖蟹自从上海开埠以来就一直供应那里,有200多年历史了,最早的时候采用木帆船运输,从兴化的七圩过长江到江苏靖江,然后运往上海。然而此水路并不通畅,碰上刮大风就要阻江,结果有次被拦在江北十几天,螃蟹和米酒全都要坏了,有个人不甘心,把螃蟹扔进酒坛里,没想到,就成了醉蟹。这是又一个误打误撞出来的美食故事。然而根据当地的一些资料,确实有一位叫罗德盛的大商号老板从200多年前生产醉蟹销售到上海、苏州一带,所依靠的不仅是当地的米酒,还往里添加了一些香料,成就了一种地方名产。因为一开始就是销售外地的高价产品,兴化本地就没有养成食用的习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兴化宴席上也少有醉蟹的传统。最早的包装,确实是陶罐盖红纸,但是容易晃出来,现在改了玻璃瓶,“能看见膏的颜色和个头大小,更加放心”。之所以叫“中庄醉蟹”,是因为中堡镇又叫中堡庄,省了中间一个字,更加响亮。
张大友从前教化学,特别知道如何防止螃蟹腐坏。“用米酒还不够,还要加些白酒。高酒精度才能杀菌消毒。”米酒是用当地的米甜酒,属于糯米酿造,不同的地方是还添加了若干陈年的糯米酒,所以香味更浓厚,过去也是当地名产,随着清末扬州的经济地位衰落,这些名产也随之走了下坡路。张大友说,这甜酒可和醉蟹难以分开,他醉的螃蟹不加任何糖,可是吃起来特别清甜,就是酒的关系。另外添加的白酒,张大友比较不惜工本,是江苏名酒双沟大曲。这几乎是所有制造醉蟹者的口头语:加料就要加最好的,包括不起眼的花椒,选用的也是四川的大红袍。
蟹之味美,和这些料确实关系很大,周围地区也尝试做醉蟹,为了延长保质期,要么就加盐,要么就加酱,都不如选择质地优良的酒:杀菌不说,甜味自酒中来。老张笑着说:“你看我的化学老师没白当吧?”
南北湖的螃蟹并不像传说中的没有腿毛,因为是生食,所以过去在腌制前会清洗得格外干净。当地人发明了一种铁刷用来刷毛,最后以讹传讹,就成了这里的螃蟹无腿毛了。张大友不仅仅用铁刷,还发明了一种去毛机器,螃蟹往机器下一放,一会儿就干净了,身体还完整无损。那些青灰色的大螃蟹满地爬着,可是他雇佣的当地的妇女们能干得很,轻轻一提,张牙舞爪的活蟹就立刻不动了。
苏北的劳动妇女,比起苏南的来更显得高大。几十个大缸旁边都是她们忙碌的身影。大螃蟹洗刷干净,酒淋消毒后就要入缸了。大陶缸里放置着几千只螃蟹,掀开盖子,酒香扑鼻,这才知道,我们看不到中庄醉蟹,并不代表中庄醉蟹就消失了。苏州不少特色蟹企业的醉蟹都是这里代加工的,这里就是个醉蟹的OEM基地。“我选蟹有一套。”老张说,他选的南北湖的螃蟹,壳薄膏壮,没有加工的时候一般人看不出所以然,可是稍微醉过,那黄亮的膏就透出壳来,时间越久色泽越饱满,甚至带紫色,正面还是活蟹的青灰,背面,简直是拼图:紫黄白,艳得很。
“挑几只带紫色的给你尝尝。”他自己掀开缸盖子,从里面挑出几只来。即使是兴化人,对此也不是很明白,曾经有县城人找到他,质问他蟹黄为什么发紫。是不是坏了。老张脾气大了,说“要是坏了,你把瓶子砸过来”。他的企业一向是市质量监测局的样本企业,有底气说这种话。
醉蟹很大,他选的都是三四两以上的雌蟹,看着一只都犯愁。掀开后盖,最中间的黄已经发紫,泥状,确实与一般的不同。老张期待地看着我。拿筷子尖抿上一点,刚进口就化开了,瞬间被征服,这是一路吃过来味道最鲜美的尤物。那紫膏,确实是醉蟹的精华;吃完了黄,开始吃腿,甜味隐藏得很好,是蟹本身的甜被酒激发了出来,而不是外在的强加物。遇见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往往就没话说,我也是这样,涌现出的是日本人说的“惜物”感,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被自己遇见了? 美食醉蟹醉蟹的做法大闸蟹的做法螃蟹海鲜中庄醉蟹苏北兴化大闸蟹大闸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