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县《顺氏宗旨簿》:建文帝流亡西南的一个旁证
作者: 俞荣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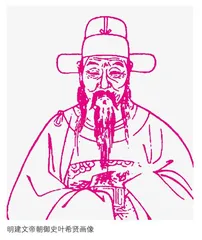
摘 要:明朝第二代君主建文帝在“靖难”政变中是死是活,成为“千古谜案”。《顺氏宗旨簿》记载:他们的始迁祖叫叶希贤,官居建文朝监察御史,燕王攻入南京时,追随建文帝逃亡,僧名“应贤”,法号“雪庵和尚”。后辗转来到茂县,改姓为“顺”,意为入川之叶(“页”与“叶”同音),蓄发还俗,娶妻生子。《顺氏宗旨簿》所言,与《明史·本纪第四·恭闵帝》《明史·列传第二十九》《明神宗实录》,以及一些明清时期的杂史,如赵士喆《建文年谱》、张岱《石匮记·让帝本纪》、郑晓《吾学编》、夏燮《明通鉴》等所记有可互参之处。《顺氏宗旨簿》从家族史的角度,为建文帝的下落提供了一个可资进一步考究的旁证。
关键词:《顺氏宗旨簿》;建文帝;叶希贤
明王朝第二代君主、朱元璋的嫡长孙朱允炆,也就是建文帝(1398—1402年在位),在他四叔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政变中,是死是活,是自焚还是流亡,600多年来扑朔迷离,成为一大“千古谜案”。
1994年7月,笔者带队赴茂县、汶川、理县和马尔康等地调研“羌族习惯法”,意外发现与这一“千古谜案”相关联的一个家族故事。这一家族姓“顺”,世居岷江流域上游的茂县。《百家姓》中找不到“顺”姓。据2018年人口普查,全国顺姓居民约3000人,姓氏排名在第994位,属于稀少姓氏。7月底,调查队撤离茂县前,笔者终于挤出时间夜访顺家,并在7月25日的日记中记述如下:
晚上分三组行动……我带蒋××(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学生)去茂县中学教师宿舍找顺公著[1]的儿子顺明允老师,谈得很投机。但顺家已无其父的书籍、手稿,给了我们一本家谱。带回看后,发觉写有建文帝下落之事。明日复印后再还他。
这本家谱题名《顺氏宗旨簿》。《顺氏宗旨簿》有三篇序文:一曰《顺氏谱序》,系顺氏十五代孙顺绍基于中华民国27年(1938年)所撰(下简称《顺绍基民国序》);二是顺氏十三代孙顺秉杓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续篇》所撰的序(下简称《顺秉杓光绪年序》);三为顺氏第十六代孙顺明允于1987年5月为《续篇》所撰的《再序》(下简称《顺明允1987年再序》)。这些序文中记载有建文帝削发为僧流亡西南及顺氏之姓氏由来等种种故事,颇为新奇有趣。
一、茂县顺氏自称是建文帝朝臣叶希贤后裔
《顺秉杓光绪年序》写道:
粤稽吾先祖顺公讳君重者,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人氏,系大明太祖朱元璋所属四先生内叶琛之后,山西平遥训导叶居升之裔,建文允炆时监察御史叶希贤是其人也。
《顺明允1987年再序》称:“原籍一说是江西省南昌府,一说是浙江省松阳县,究系何处,已无从查考。”《明史·列传第二十九》明确指出,叶希贤是松阳人。松阳县今隶属浙江省丽水市。丽水古称“处州”。“松阳姓氏文化”研究专家称:叶(葉)姓为松阳“十大姓”之首,有3万多人。叶姓一族原为西晋末“衣冠南渡”时,最早移居松阳的大族。
《顺秉杓光绪年序》则认为建文帝削发为僧,化名“应文”流亡时,叶希贤亦削发从亡,僧名“应贤”。历尽艰险,遍尝苦难,最后叶希贤匿迹川西岷江上游,易姓为“顺”,寓意为入“川”之“页(‘叶’的同音字)”,取名“君重”:
燕王篡国,疾从亡如寇雠,忠臣失君,既改元,羞覆戴,天命已攸归,姓名将安附,弃而违之,不得已也。既而之“川”,复加为“顺”,取姓曰“顺”,名曰“君重”,义取先年事君勿欺,为建文所珍重之意耳。
顺君重最后定居于岷江上游的茂县凤仪镇宗渠村,蓄发还俗,娶妻生子:
是时希贤年已七十矣,念故乡之难归,辄飘然而泣下,忠虽尽矣,孝何同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孟子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爰将行粮坐裹之余金,成婚治业,故世居于终云。迨后生子二人,长子“顺里”,次子“顺美”,又取其里仁为美,可以处仁之义也。
《顺绍基民国序》中描述更为详细:
稽古系氏,古非今姓,实周时楚国叶县叶公之后也。……至希贤公,独冠前贤,为建文时监察御史。遭燕逆陷京,神器倾移,应牒更名,祝发为僧,服袈裟,执度牒,同帝随亡游滇,驻跸西平侯沐晟家,就白龙山结茅为庵,计作韬隐。
《顺绍基民国序》中,记述叶希贤入川至茂县还俗和改姓“顺”的经历也比较清晰:
……于是希贤公伤心惨目,怀动家山,落魄天涯,终无了局,人事未尽。亚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安转侧,由松至茂,复来宗渠,羡兹山明水秀,人杰地灵,乃售轻软,蓄发娶妻,方落业焉。变姓易名,借“页”为“叶”,配“川”于左,合体成“顺”,更名“君重”,盖“顺君重”者。揆诸意义,临难顺君,为君之所贵重者也。……厥后君重公生子二人,长曰“里”,州文庠;次曰“美”,惜无传(待考)。
《顺绍基民国序》的另一个特点是,为始迁祖顺君重、二代祖顺里以下一直到十五代顺绍基本人为止的中间十三代先人开列了一个血缘传承清单,内容包括名、字、号、功名、官职等。
《顺氏宗族谱·序》中有些说法,不足为信。如叶氏是《论语》中那个以为儿子去官府告发他的父亲偷别家的羊是符合“直”道的“叶公”后裔。再如叶希贤即顺君重70岁才还俗娶妻,居然生了两个儿子,这在古代生育史上应属于极小的小概率事件。其实,此类瑕疵在家谱中屡见不鲜,着实难免,对于本文也无关紧要。重点是建文朝臣有无叶希贤其人。
二、建文朝确有御史叶希贤其人
茂县顺氏宗谱称始迁祖顺君重原名叶希贤,官拜建文朝监察御史。有无其他资料可以佐证呢?
至清乾隆四年(1739年)才修改定稿的《明史》中,有《建文遗臣传》一卷,见于《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列传第二十九》。史官搜罗颇详,记述建文朝遗臣齐泰、黄子澄、练子宁等30多人,在《练子宁传》中附有《叶希贤传》:
希贤,松阳人。亦坐奸党被杀。或曰去(发)为僧,号雪庵和尚云。
虽短短22字,但可证明建文朝确有叶希贤其人。至于他是“被杀”还是“为僧”,《明史》作者下笔谨慎,一个“或”字,予以存疑。
《顺氏宗旨簿》3篇《序》文说,叶希贤不但未被杀,而且随建文帝“从亡”,法名“应贤”,号“雪庵和尚”。
燕王朱棣以“清君侧”名义搞军事政变,皇袍加身后,清除建文朝的史官实录文字,彻底抹煞建文年号与治绩,建文君臣被刻意扭曲,抹黑为“奸党”,希冀在历史上永远抹去建文朝存在事实。朱棣确是一位企图实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典型代表。国史阙失,野史杂记迭兴。170余年后,至万历朝(1573—1620年),终于恢复了建文年号,建文朝臣受株连外亲也得以放赦。《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三年(1585年)三月载:万历皇帝下诏,“释革除年坐忠臣方孝孺等谪庶者,浙江七百一十三人,江西三百七十一人,福建二百四十四人,四川四十一人,广东三十四人”,为建文君臣平反。于是记叙建文君臣故事的笔记小说、稗官野史纷纷登场,神秘怪诞的包装下或许能透露一些历史真相。叶希贤是否建文“从亡”遗臣,是否削发为僧,只有从这些别史杂记中寻找蛛丝马迹。
明赵士喆在《建文年谱》中是这样描绘建文君臣的亡命经历的:当燕王大军攻陷南京城时,建文帝“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劝告说“不如出亡”。少监王钺说:高帝(朱元璋)升遐吋,留有一“遗箧”。取出此箧砸开后,“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还有袈裟、剃刀、金锭等物。遗箧向建文帝指明出路:削发为僧逃亡。建文帝无奈地一声叹息:“莫非天数啊!”于是:
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2]
明末清初的张岱在《石匮书》的《让帝本纪》中,明确地说:“建文帝出奔事,见史仲彬《致身录》及程济《从亡随笔》。”他认为《致身录》《从亡随笔》是信史:“建文革除事,传疑久,一似耿耿人心者。兹《致身录》出自从亡手,含荼茹苦,自尔真功,其文质而信,怨而不伤,独史氏书也哉,足以传矣。”(《石匮书》卷二《让帝本纪》)其记述建文帝出宫逃亡之事,大量引用《致身录》的文字:
《致身录》曰:大内火起,帝从鬼门关遁去,时六月十三日未时也。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亡去。”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升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灌铁(引者案:据《从亡随笔》:“闭以二锁,锁以铸铁灌。”)。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大内。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鞋帽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备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疑,有等著名势必究诘,有等妻儿在任心必牵挂,宜各从便。”[3]
赵士喆、张岱都肯定建文朝有叶希贤其人,并削发从亡建文,改名“应贤”。
《顺秉杓光绪年序》描述建文君臣的出逃情节,与《建文年谱》《石匮书·让帝本纪》中所载大同小异:
靖难兵入京城,文武宦侯迎降,帝欲自裁,适内官升一红箧至云:“太祖所遗嘱,临大难当发。”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鞋帽剃刀俱备,黄金十锭,朱书存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泣曰:“数也。”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披牒,从帝至鬼门而一舟舣岸,为神乐观道士王升见帝叩头称万岁曰:“臣固知陛下之来也,畴昔高皇帝见梦,令臣至此耳。”遂导至观,相与逃亡。
顺秉杓的这段序文,是抄自《建文年谱》《石匮书》或《致身录》《从亡随笔》之类的书籍,还是出自顺家祖祖辈辈的口耳相传,不得而知。
从《顺氏宗旨簿》可知,顺氏十一代祖顺登拔和十二代祖顺万椿,即顺秉杓的祖辈和父辈,曾到桂州(今广西省桂林市)、干州(今湖南省吉首市)做过吏员一类的小官,他们一定会关心顺氏族源,探究自己从先辈那里传下来的流亡故事,以及相关文字根据;或许见到过这些别史、杂史和笔记小说。这一推测若能成立,那么,《顺秉杓光绪年序》的这些描述很有可能就是抄自《建文年谱》《石匮书》之类的稗史。
这一故事情节太过离奇,如明太祖朱元璋为继承皇位的孙子朱允炆预留逃亡秘箧,又托梦道士接应等等。其实,将出逃过程描写得越发神奇、愈加精确细致,水分就越大,编造的痕迹就越明显,历代史家对此质疑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在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认知水平下,祭出高皇帝的亡灵,才能抬高建文帝的合法性,才能博得对其被迫出逃最广泛的社会同情。神奇的情节是编造的,削发为僧而成功出逃许是真实的。剥离其光怪陆离的外衣,才能获知合理的事实推断。这是我们参酌赵士喆、张岱著作所应取的态度,也是对待郑晓《吾学编》、夏燮《明通鉴》等书所应取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夏燮在撰写《明通鉴》时,“参证群书,考其异同”,不仅认为建文帝活着逃出生天,还挖出了叶希贤故事。书中记录了一则关于叶希贤的传说:从惠帝出亡为僧的监察御史叶希贤,法名应贤,号雪庵,尝云游于滇、蜀间,爱重庆府大竹善庆里山水,其里隐士杜景贤为结茅于白龙山。和尚听夕诵易乾卦,山中人以为读佛经,景贤知之不忍问,惧和尚不能安,和尚亦知景贤意,遂改诵《观音经》,寺因名观音寺。和尚好读《楚辞》,时时买一册,袖之驾小舟,进中流,朗诵一叶,辄投一叶于水,投已辄哭,哭已又读,叶尽乃返,众莫知其意,景贤益怜敬之。和尚好饮,饮必高歌,能文,落笔成章,气焕发人。后寂于杭州僧寺。卒之日,其徒问:师即死,宜铭何许人?和尚张目曰松阳,问其姓氏,终不答。遗诗若干篇。这个传说与茂县顺氏宗谱所述的易姓改名、娶妻生子等相径庭。此处略备一说。夏燮死于光绪元年(1875年),顺氏十三代孙顺秉杓的《顺氏宗旨簿·序》撰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据此,夏氏应不知有茂县顺氏这一支叶希贤后裔存在。尽管与茂县顺氏宗谱所述不同,但夏燮认定有叶希贤这个“从亡”者。他在《明通鉴》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