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霞·孤鹜及其他
作者: 李凤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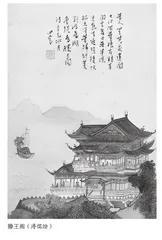
摘 要:由王勃《滕王阁序》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引出的“落霞”“孤鹜”之辨延续至今。持“落霞”是飞蛾或绯羽鸟等观点的人,都错在没有从《滕王阁序》的用语规范、意象选择、抒情基调去分析,故这些异说经不起推敲。
关键词: 落霞;孤鹜;“零散”的由来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某先生发表于《文史杂志》2024年第6期的《说“落霞”》,就特别出奇。文曰: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落霞”,不是云霞的意思;而是指“零散的飞蛾”。
这个句子,出自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要了解王勃此序的意义,当时当地的风物不可不晓。对此,宋代吴曾在其《能改斋漫录·辨霞鹜》中说:“落霞非云霞之霞。盖南昌秋间有一种飞蛾,若今所在麦蛾是也。当七八月之间,皆纷纷堕于江中,不究自所来,江鱼每食之,土人谓之霞。故勃取以配鹜耳。”宋代俞元德也在其《萤雪丛说下》中说:“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世率以为警联。然而落霞者,野鸭也。野鸭飞逐蛾虫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齐飞。”由此看来,“霞”不是云霞,而是一种飞蛾。另外,“落霞”之“落”并不是“飘落”的意思,“落”在句中与“孤”相对,意思与之当相同或相近,是“散落、零散”之义。零散的飞蛾被孤单的野鸭在水面上追捕,就形成“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千古绝唱。
文章不长,问题不少。我觉得很有解读的必要,现为读者逐一分剖之。
一、文章或许是抄来的
写文章不比领养儿女,然而有些人却信奉“天下文章一大抄”。近些年,抄袭之风大有回旗反鼓之势,其中还牵涉到某些名流、学者的论文造假。毫不客气地说,某先生这篇短文,也大有抄袭之嫌。读者要是不信,不妨待我也来抄上一抄:
……“落霞”是指“零散的飞蛾”……宋代吴曾说:“落霞非云霞之霞,盖南昌秋间有一种飞蛾,若今所在麦蛾是也。当七八月间,皆纷纷堕于江中,不究自所来,江鱼每食之,土人谓之霞,故勃取以配鹜耳。”
俞元德也在其《萤雪丛说下》中说:“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世率以为警联。然落霞者,飞蛾也,即非云霞之霞,土人呼为霞蛾。至若鹜者,野鸭也。野鸭飞逐蛾虫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齐飞。”
另外,“落霞”之“落”也不是“飘落”的意思,“落”在句中与“孤”相对,意思当相同或相近,是“散落、零散”之义。零散的飞蛾被孤单的野鸭在水面上追捕,就形成“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千古绝唱……[1]
此文数年前即见于网络,署名齐家平国。我抄录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诸君,读罢这部分内容有何感想?这个齐家平国与某先生是什么关系?如果是同一个人,我当然无话说;如果不是同一个人,那么,某先生是不是该给大家一个交代?
二、引文驴头不对马嘴
前引某先生《说“落霞”》,第三自然段有这么几句表述:“宋代俞元德也在其《萤雪丛说下》中说:‘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世率以为警联。然落霞者,野鸭也。野鸭飞逐蛾虫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齐飞。’由此看来,‘霞’不是云霞,而是一种飞蛾。”
某先生在第二自然段明明提出“‘落霞’,不是云霞的意思;而是指‘零散的飞蛾’”的论点,在第三自然段又以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辨霞鹜》为论据,来支持这种说法,按理,接下来他引用俞元德的话,也应该是阐明落霞是“飞蛾”的,怎么突然又来个“然落霞者,野鸭也”呢?这倒把人搞糊涂了!某先生究竟要论证“落霞”是“飞蛾”还是“野鸭”?提出的论点是A,使用的论据却证明那不是A而是B,这不违背行文的逻辑吗?况且,某先生“由此看来”后边的结论,又是怎么得出的?这个“此”,是指吴曾所言“飞蛾”还是指俞元德所言“野鸭”?
显然,某先生是把俞元德的话抄错了。他可能没有见到过俞成(字元德,东阳人)《萤雪丛说·辨〈滕王阁序〉落霞之说》的原文,经他脱头漏尾这么一抄,不仅搞得读者一头雾水,而且弄得他自己也后语不搭前言,驴头对不上马嘴了。
三、吴曾、俞成、郎瑛的“落霞”之辨
20多年前,王勃《滕王阁序》被选入全日制高中语文课本时,我正担任高中语文教员,因教学需要,倒是去过几家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查阅过有关资料,手自抄录且认真核对,只是那时没有想到今天写此文还要用到其中几条,未曾抄下页码。
当年,我查得两宋之交的吴曾、南宋的俞成、明代的郎瑛都对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个句子有过辨析,这里颇有一说的必要。
(一)吴曾的《辨霞鹜》,不仅辨霞,也辨鹜。他说:
梁江淹《赤虹赋》云:“霞晃朗而下飞,日通笼而上度。”张说《晚景》诗云:“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飞。”凡淹说所谓霞飞,则云霞之霞也。王勃《滕王阁序》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土人云:“落霞非云霞之霞。盖南昌秋间有一种飞蛾,若今所在麦蛾是也。当七八月之间,皆纷纷堕于江中,不究所自来,江鱼每食之,土人谓之霞,故勃取似配鹜耳。”不知者便以为云霞,则长天岂可与秋水同色也哉。予又按,孔颖达曰:“野鸭曰凫,家鸭曰鹜。鹜不能飞腾。”故郑康成注《宗伯》云:“鹜取其不飞迁。”李巡亦云:“凫,野鸭名。鹜,家鸭名。”然则鹜本不能飞耳。论文虽不当如此,要之作文者,亦不可不察也。[2]
吴曾的见解可归纳为三条:1.王勃句中的“落霞”不是云霞,而是飞蛾;2.若是云霞,则长天不与秋水同色;3.鹜是家鸭,凫才是野鸭。
(二)俞成的《辨〈滕王阁序〉落霞之说》是转述吴獬的见解。他说:
王勃作《滕王阁序》,中间有‘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句,世率以为警联。然而‘落霞’者,乃飞蛾也(即非云霞之霞),土人呼霞蛾。至若鹜者,野鸭也。野鸭飞逐蛾虫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齐飞。若云霞,则不能飞也。见吴獬《事始》。(按:原书为木刻影印,没有断句,标点为笔者酌加)[3]
吴獬的《事始》我没有查到。俞成的转述也可归纳为三条:1.王勃句中的“落霞”不是云霞,而是飞蛾;2.鹜是野鸭;3.“齐飞”是野鸭飞起来追食蛾虫。
(三)郎瑛的《七修类稿·落霞》,对王勃“落霞”句中的落霞又作了另外的解释。他说:
落霞乃鸟也,余旧尝于内臣养户处见之,形如鹦哥少大,遍体绯羽,《萤雪丛书[说]》以为飞蛾,误矣。又曰:“鹜,野鸭,盖因野鸭逐飞蛾欲食,故曰齐飞。”此又强解可笑。然王勃序文,世以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古今奇句。昨读《困学纪闻》,乃知变庾信《马射赋》“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之句也。[4]
郎瑛的这番话依然可以归纳为三条:1.王勃句中的“落霞”不是云霞,而是绯羽鸟;2.俞成的飞蛾说是错的,说野鸭追食飞蛾故曰齐飞“强解可笑”;3.王勃的名句系由庾信《马射赋》“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仿造而来。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张:“落霞”不是云霞。那么“落霞”真的不是云霞么?
清人袁枚可不这么看,他指出:
……大抵宋人好矜博雅,又好穿凿:故此种剜肉生疮之说,不一而足……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此落霞,云霞也,与孤鹜不类而类,故见妍妙,吴獬《事始》以落霞为飞蛾,则虫鸟并飞,味同嚼蜡。[5]
“虫鸟并飞,味同嚼蜡”,鸟鸟并飞,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袁枚虽然批评的是宋人“好矜博雅,又好穿凿”,可步其后尘的明人郎瑛,恐怕也有此通病吧?
四、我对吴曾等人之辨的再辨
“落霞”是不是云霞的问题且放一放,让我们先来看看吴曾、俞成、郎瑛之辨涉及的其他几个问题有无道理。
吴曾说“不知者便以为云霞,则长天岂可与秋水同色也哉”,意思是天空有了云霞,就绝不与秋水“一色”了。其实王勃描绘的是水天相接,水色天光浑然融为一体的辽阔景象,这种景象是不会因云霞改变的,因为天空的云霞同样会倒映在水中。吴曾又说鹜是家鸭,凫才是野鸭,其实古人对家鸭野鸭也没分得那么细。《广雅》指出:“凫鹜也,此统言而未析言之也。”《太平御览》引《说文》曰:“鹜,野凫也。”可见鹜也指野鸭。“落霞”“孤鹜”,“秋水”“长天”,不仅对举,还有个平仄协调问题不得不考虑,所以错的不是王勃。吴曾虽也懂得钻牛角尖不对,说是“论文虽不当如此”,却又指摘王勃作文“不察”,岂不自相矛盾?
俞成转述吴獬的话虽承认鹜是野鸭,却说“齐飞”是野鸭与蛾虫齐飞,“若云霞,则不能飞也”。他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晏几道《思远人》:“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谢混《游西池》:“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刘秉忠《溪上》:“我欲揽怀晚霞飞”,不就有“云飞”“飞云”“飞霞”“霞飞”之类的字眼吗?
郎瑛指出俞成“落霞与孤鹜齐飞”是野鸭追食蛾虫“强解可笑”,王勃名句仿自庾信《马射赋》,都对;可说“落霞”是一种“遍体绯羽”的鸟,就让人不敢恭维了,难道他不同样“强解可笑”么?这鸟即使真有“落霞”之名,也真为他亲眼所见,又焉知这样的鸟名不是养鸟人或别的什么人根据王勃《滕王阁序》给取来蹭热度的?
上述几个问题既然辨得经不起推敲,可见吴曾、俞成、郎瑛做学问还不够严谨。他们的“落霞”之说,遭人“好矜博雅,又好穿凿”之诮,也是必然。
我认为,王勃名句中的“落霞”就是晚霞,根本不是什么蛾虫或绯羽鸟。理由如次:
其一,吴曾的说法违背人们的省称习惯。即使“南昌秋间有一种飞蛾,若今所在麦蛾”,但那也该叫“霞蛾”,不应简称为“霞”,正如“松鼠”不得省称“松”,“竹荪”不可省称“竹”,云雀不能省称“云”是一个道理。因而我怀疑“土人谓之霞”的表述有违事实本身(俞成文中就说“土人呼霞蛾”),“霞”应该是吴曾自己对“霞蛾”的省称,而不是南昌当地人的省称。
其二,吴曾、俞成把落霞释为“飞蛾”不合《滕王阁序》的语境。就算南昌当地人真把这种飞蛾省称为“霞”,就算这种“当七八月间,皆纷纷堕入大江之中”的飞蛾可算做“落霞”,但这种“堕入”显然是不辨方向的乱飞,何况吴曾说这种飞蛾“若今所在麦蛾”,麦蛾一般长4到7毫米,形体很小。霞蛾与麦蛾相若,也不会相差太多。这种极小的蛾虫,稍远便看不清,根本不可能与孤鹜形成“齐飞”的景观。且不说野鸭不善飞捕蛾虫,就算野鸭有燕子那样矫捷的身手,可以“飞逐蛾虫”而食之,那也该是群起对蛾虫围歼,王勃笔下就不当出现“孤鹜”——难道只此一只野鸭吃荤,其他野鸭都是吃素的?
其三,文章高手对词语的选择和使用必然遵从一定的规范。王勃是名家,他写《滕王阁序》,通篇用的都是文言词汇,故“落霞”当是文言词汇,不当是土语词汇。此外,于洪都府来说,王勃只是一位来去匆匆的过客,即使当地土语有名叫“霞”的蛾虫,他知道的概率也很小;即使他机缘凑巧知道了这种“霞”,他也不会把它叫“落霞”。因为“落霞”这个文言词汇的出现是在王勃之先,梁简文帝《登城》诗:“落霞乍续断,晚浪时回复”便是明证,而且此“落霞”释义正是晚霞。王勃这篇序,不是写给当地土人看的,他犯不着在通篇文言中夹杂一处僻涩的土语而造成人们的误解。
其四,写景与抒情必然密切相关,这很关键。王勃因杀官奴曹达连累父亲远谪南荒,心情一直不好。他写《滕王阁序》抒发的是何种感情呢?是“怀才不遇、愤懑悲凉而又不甘于沉沦的复杂感情”。[6]作者虽处“胜友如云”“高朋满座”之乐,却始终抹不去他“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之悲。因此,文中不仅用“落霞”“孤鹜”“秋水”“长天”来营造落寞凄凉、渺远空旷的氛围,且进一步以“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作了加深,为后文慨叹“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奠定抒情基调,所以文中的“落霞”只能是晚霞,将其解释为飞蛾或绯羽鸟都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