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报刊诗作特色之辨
作者: 张文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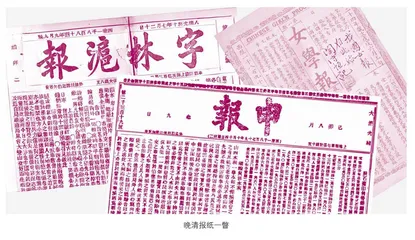
摘 要:晚清时期,报刊成为文学传播的新媒介,为传统诗词提供了现代化载体。报载诗歌的发展淡化了诗词传播的地域特质,突破了传统诗词的题材领域,拓宽了诗词创作的受众群体,革新了传统诗词的创作与传播方式,使诗歌创作更多关注时事与新思潮。
关键词:晚清报刊;诗歌;传播
波诡云谲的晚清时代,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与影响,应时而生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强劲的势头席卷晚清政界与文坛。我国早期的中文报刊多由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创办。甲午战争后,国人自办报刊的高潮兴起,报刊逐渐承载起宣传政治事宜、传递公众舆论、传播文明思想和发表学术创获的重任,开启了以报刊新媒介为中心的文学时代。新一代知识分子以报刊为阵地,发表作品,传播新知,构建了具有时代属性的文学平台。在这一背景下,诗歌作为传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渐在报刊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书写政界风云与时移世变的时代之歌,成为晚清文学的重要指向。以新的传播媒介为平台的报载诗歌,逐渐呈现出与传统诗歌的分野,革新了传统诗词的创作与传播方式,呈现出报刊诗作的鲜明特色。
一、淡化了诗词传播的地域特质
报刊上发表的诗作与非报刊发表的诗作的异同辨析,是研究报载诗歌的前提;报载诗歌在创作、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与传统诗歌产生的差异,正是其特色与价值所在。报刊诗歌淡化了诗词传播的地域特质。
文学史发展到明清时代,地域文学传统的自觉意识逐渐显豁,地缘成为诗词传播的生态纽带,文人诗作往往在特定区域的诗词同人圈子之间传阅,流通范围则受限于诗人身份的轻重和诗作质量的高低等因素。独特的地域文化背景滋生出的作品风格,很容易以地域作为分野,使具有共同倾向的作家群体凝聚成为诗歌流派。如明初,诗坛即分为吴派、越派、江右派、闽派、五粤派五大创作群体,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1]有清一代的地域诗派更是不胜枚举,如河朔诗派、岭南诗派、虞山诗派、娄东诗派、秀水诗派、饴山诗派、浙派、桐城诗派、高密诗派、常州诗派等,[2]同时涌现出岭南三大家、江左十五子、江右三大家、江西四才子等文学团体,另有诗社等文人雅集。诗坛格局呈现出地域传统。
新兴报刊媒介的出现,实现了文学作品无差别跨地域传播的可能,诗词传播的时效性也得以大幅提升。传播渠道的升级,使诗词传播不再局限于师友传阅、别集刊刻与文人雅集等活动,诗人群体有机会通过报刊这一平台公开发表诗作,诗人群体的跨域性集结成为可能,共同的诗歌创作理念成为凝聚诗人群体的新型纽带。《申报》[3]率先于《本报条例》中公开提出“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4],为广大文人群体免费发表诗作开创了先例,在文人群体中引起轰动。该报最初并未辟出专栏发表诗词,但已于报刊末尾有了大体固定的位置,初具副刊规模,“成为后世所谓‘报屁股’的滥觞”[5];之后特辟《瀛寰琐记》《四溟琐记》《寰宇琐记》等附属的文艺专刊,除诗词外兼刊散文小说和笔记论说,为囿于经济而刊刻不易的寒士布衣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起到了延揽稿源和巩固传统文人地位的作用。此后的《字林沪报》[6]等报刊相继效仿,纷纷发表公开声明,凡登报之诗词歌赋概不取值渐成定例,于新闻时事后刊载“诗词杂作”。文学栏目逐渐发展为许多报刊不可或缺的固定专栏,之后创办的报刊基本都会刊载诗词。随着报刊诗词专栏的进一步发展,其俨然成为各诗派的创作园地,如《东方杂志》刊载“同光体”诗歌,成为有清一代宗宋诗风发展到晚近时期的高峰;《新民丛报》等改良派所办报刊成为倡言“诗界革命”的阵地;《南社丛刊》亦是刊载南社成员诗、词、文等文学作品的机关刊物;另有《中西教会报》等以宣教为主的教会报刊。这些报刊的作家群体遍及国内,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报刊诗词对地域特质的突破。
秉承着相同诗学理念的文人自觉聚集于各类报刊,报刊承担起创作园地与理论阵地的双重作用。它们以专栏形式为诗词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由此,报刊作为文学传播的现代传播媒介,不仅“对诗词等传统文学作品实现了外在传播模式的变革”,还凭借共同的理念和追求,“内在地实现了对传统文学作者群聚合模式的超越,并内在地对诗词创作的内容实现了统一与融合。”[7]
二、突破了传统诗词的题材领域
就诗歌内容来讲,传统诗歌创作更多地体现了诗人的个人情感、思考和艺术追求,艺术性和情感表达是其关注重点。报刊诗作更多是为了满足特定主题或文学活动而作,其创作目的更加明确,内容多与时事密切相关,时代潮流与传统书写皆囊括其中。诗歌题材从吟咏风雅转变为反映新事物、新思想和现代文明,世界局势的变化成为文人笔下的集体关切,直接冲击了传统诗词的题材领域。
一方面,报刊媒介提升了诗词的社会参与度。传统诗词本身具有“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特点,报刊则为诗歌紧跟时事这一特点提供了快速见刊的平台,大大缩短了作者创作与读者接受过程中的时间差。在我国,“近代化的报刊,是外国人首先创办起来的”[8],故旧体诗词在报刊上的传播也起始于此。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共发行39期,其中有13期摘录或刊发过传统诗词,班固、左思的赋,李白、苏轼的诗词皆选录在内。最有意义的当属原创性的《兰墩十咏》《医院》等诗,对英伦风土、先进医术皆有吟咏,开启了于报载诗歌中传递西方文明的滥觞。其后,多家传教士报刊皆有诗歌见刊,初期最具代表性的劝诫诗,包括劝禁烟、反缠足等时事内容。《中西教会报》先后刊载了《劝禁种烟》《劝诫酒竹枝词》《劝勉改除鸦片四言歌》,《万国公报》刊发了《缠足论》《缠足辨》。《中西教会报》亦发表有《教外妇女缠足歌》《教会妇女放脚感恩歌》等诗文,另刊有上书清廷请禁鸦片的奏折多篇,内容均与当时的反鸦片运动和不缠足运动等社会性运动相呼应;义和团运动等政治性事件也包括在内。其后,报载诗歌的取材范围逐渐扩大,报刊栏目也愈加丰富。从外国人在华的早期办报活动,到国人自办报刊,与此间的宗教宣传、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译报活动、太平天国、维新运动、民主宣传、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等政治、经济、文化事件皆紧密相关,观照了国家动乱与民生艰难的时局,书写了自强求新与反帝爱国的情怀,切实见证了历史洪流中晚近时代的发展大势。
另一方面,借助报刊媒介的传播平台,女学与女权等新兴女性思潮也逐渐纳入诗歌领域。文学史中能以诗词留名的女性作家只占少数,能在文学史的汰洗之中崭露头角实属不易,报刊平台则为更多女性作家提供了发声的机会。女性所关注的话题与内容,得以通过诗歌进入大众视野。至《女学报》《女子世界》《女学新报》《女学生杂志》[9]等晚清女性报刊的相继创办,女学渐兴、女权日倡,产生了一大批以女性为主要参与者、以女性问题为主体、引导和启蒙女性意识觉醒的报刊诗词。如《女子世界》所刊《复权歌》鼓励女性奋起抗争,捍卫自身权利,首句“古来第一事不平,男尊女子轻”直指男尊女卑之糟粕传统,又以“须知独立自尊,第一学问是根本”[10]为捍卫女性权利指明向学道路。此外,《女子世界》“文苑”栏中辟有“学校唱歌”(后改名“唱歌集”)栏,随后陆续添加“因花集”与“攻玉集”等诗词专栏。[11]此后秋瑾所办《中国女报》(1907年1月)、陈以益主编的《神州女报》[12](1907年12月)等刊亦多设同类“唱歌”栏。《娘子军》(《女子世界》1905年4月第11期)、《女国民》(《女子世界》1907年7月第6期)、《勉女权》(《中国女报》1907年3月第2号)等女性诗歌,提倡女学、扬厉女权,开风气之先,在晚近报刊中谱写了中国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重要篇章。
此外,随着国门渐开,诸多新事物和新技术远渡而来,皆以新名词、新语句的形式集中体现于报载诗词中,异境新声随着海外诗人的脚步融入诗歌的书写之中。有海外留学或游历经历的群体,会将异地见闻经历见诸诗篇。留学群体的海外诗中,对世界各地的自然景观、人文古迹均有涉及,从中可见当地的风物民俗,诗歌境界渐次异于往日。诗中记述的西方自然风物,打开了国人通过报端了解世界的窗口。除因海外经历而创新诗境的新知识群体外,国内文人同样受到西方文明的洗礼,西学东渐之风吹到各地,各类新器物、新名词于诗作中大批涌现,极大地促进了西学新知的传播,拓宽了诗歌书写的题材领域。
三、拓宽了诗词创作的受众群体
就读者接受度的差异性来讲,传统诗词的读者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多为知识分子等文化群体,诗友中更以挚友同门为主力,读者圈较为狭窄。诗词歌赋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无形的阶级阻碍,文学活动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狂欢,文艺逐渐衍化出高雅与通俗之分。而《新民丛报》等致力于启发民智的报刊诗词更注重通俗性,符合报刊读者的接受能力和阅读兴趣,其受众则更为广泛,包括了不同文化层次和年龄段的读者。它们聚集了大批诗作者在共同阵地上发表作品,使诗歌创作与时事密切相关,形成了较为稳定且广泛的读者群体。
这些新兴报刊在传播方式和阅读成本两方面均有优势,使读者能以更低廉的成本得到更具广度的作品欣赏和信息获取。
首先是报刊媒介的传播形式为读者提供了阅读便利。传统的诗歌传播多以师友同门间的赠阅唱和为主,诗人别集也主要依靠个人出资刊刻传抄,作者成为主导,读者也囿于知识群体。在晚清社会思潮的涌动和西风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报载诗词成为启蒙国民的利器。从最早的零星刊载到诗词专栏的设立,再到附出传统文学专刊,报刊为诗词开辟了新的媒介传播途径,为读者提供了更为便利的阅读条件和形式,更加适应市场需求。一方面,报馆为保障报刊销量,借刊布诗词等传统文学作品,在传统文人中打开发行局面,巩固报刊在传统文人这一稳定受众群体间的地位。通过现代传媒来发表传统诗词的文人,成为得风气之先者,同时收获了超出预期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概不取值的征稿方式为报刊延揽稿源提供便利。诗词刊布保持了报刊与传统文人的稿源关系及与受众的关系,同时又为新思潮提供了发展阵地,凝聚了持有相同理念的作者群体。以诗会友的传统诗词传播方式与新兴大众传媒相结合,碰撞出彰显时代潮流的传播效果。
其次在于阅读成本的降低。与传统诗文集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相比,晚清报刊在出版成本、见刊时间、发行数量等方面皆具明显优势。在印刷上,清代“各通商口岸及大城市纷纷出版期刊报纸,传统的雕版与木活字印刷,逐渐为西方的石印、铅印技术所打倒而代替”[13],西方较为先进的石印与铅印技术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印刷技术的改进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成本也随之降低。以文学类期刊为例,小报如《新闻报》(1897年)“售价起始为每份五文”,《笑报》(1897年)为“每张售钱五文”,《采风报》(1898年)为“每张售制钱四文”,《趣报》(1898年)为“每张售制钱六文”,《通俗报》(1899年)“每张售制钱四文”,《海上文社日报》(1900年)“每张售钱四文”,《春江花月报》(1901年)“每张初售大钱六文”,《及时行乐报》(1901年)“每张售制钱六文”,《方言报》(1902年)“每张售大钱六文”,日商所办《支那小报》(1902年)“每张售钱七文”等。[14]就1900年左右发行的以上报纸定价来看,每张平均售价大概在五六文钱。关于清代的诗文集等书籍定价,“平均每册均在0.3两银左右”[15],几乎等同于基层劳动者一个月的收入。以清代的银钱比价来看,“应以银一两换制钱千文作为平价”,但银贵钱贱的现象时有出现,“从乾隆五十年以后迄于清末始终处于银贵钱贱阶段,特别在光绪初和宣统三年,银一两换制钱总在一千二三百文以上,偶尔可换二千文”[16]。即便按平价的银钱比价来算,书籍与报纸的差价显然不止毫厘。在读者的消费心理上,正如阿英所说:“中西各种书本,价钱都是贵的,若然用白话做在报上,一天一张,便觉所费不多。”[17]相较于书籍来讲,报刊的低廉定价与可单张购买的形式打破了全册购买的捆绑式销售,降低了读者相应的购买成本,无疑为当时的消费者提供了更经济的购买选择。
与单向传播的传统诗集相较,报载诗词可以及时关切读者反映并作出相应的说明和调整,与读者群体形成积极的双向互动。同样,接受市场检阅的诗词创作逐渐脱离仅以自娱为目的的状态,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了报刊诗词的有效传播。总之,晚清报刊诗作在淡化地域特质、突破传统题材领域和拓宽诗词受众群体等方面展现了独特的特色与价值。这些变革不仅反映了晚清时期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也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注释:
[1]参见王学太:《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
[2]参见刘世男:《清诗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91页。
[3][6][9][12]参见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0页,第175—176页,第57—59页,第85—86页、第275页。
[4]《本馆条例》,《申报》第1号,1872年4月30日。
[5]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881年版,第56页。
[7]焦宝:《晚清民初诗词作者群与文学期刊关系研究——以〈申报〉相关期刊、〈新民丛报〉与〈东方杂志〉为对象》,《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3期。
[8]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
[10]《复权歌》,《女子世界》1905年2月,第10期。
[11]参见夏晓虹:《晚清女报中的乐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3]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6—547页。
[14][17]参见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0—83页,第64页。
[15]袁逸:《中国古代的书价》,《图书馆杂志》1991年第4期。
[16]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13页。
作者:中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