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勘误
作者: 王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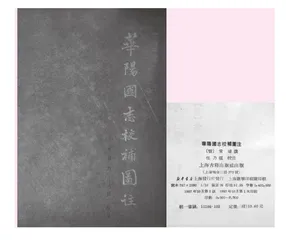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任乃强先生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该书不仅使东晋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详细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解决了历史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翻检该书,文字错误较多。本文列举勘误数则,以补缺憾。
关键词:《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勘误;任乃强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的代表著作之一。是书对我国第一部方志、晋代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整理,不仅使东晋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详细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其中的许多论述解决了历史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成为学界公认的定论。正因其重要的学术贡献和突出的文化价值,该书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后,一举斩获首届国家图书奖。但因年代久远和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今天看来,该书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字上的错误。本文列举数则,以补缺憾。
一、李弈与李奕
在任乃强先生为说明本书研究时限而制订的年表中,在公元346年条,有“李弈自晋寿叛,寻败死”的记载。按,“李弈”当作“李奕”。《晋书》卷一百二十一《载记第二十一·李势传》载:“李奕自晋寿举兵反之,蜀人多有从奕者,众至数万。势登城距战。奕单骑突门,门者射而杀之,众乃溃散。势既诛奕,大赦境内,改年嘉宁。”《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记十九》“穆帝永和二年”条载:“冬,汉太保李奕自晋寿举兵反,蜀人多从之,众至数万。汉主势登城拒战,奕单骑突门,门者射而杀之,其众皆溃。势大赦境内,改元嘉宁。”据此,“李弈”当作“李奕”,原版形近而误。
二、季王与季玉
本书卷七《刘后主志》五正文有“季王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按,据文义,“季王”当作“季玉”。据《三国志》卷三十一《蜀书一·刘二牧传第一》,刘焉是汉鲁恭王后裔。因侍中董扶“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之言,谋领益州牧。其权势鼎盛时,子刘范为左中郎将,刘诞为治书御史,刘璋(字季玉)为奉车都尉,皆从献帝在长安。“季玉父子”,即指刘焉与刘璋而言,作“季王”则不通。刘璋袭益州牧后,因忌惮曹操攻势,听从张松建议,交好刘备,最终迎刘备入益州。刘备攻刘璋,刘璋出城投降,刘备得入成都。
三、永州与永川
本书卷一《巴志》十一注18中,任乃强先生对乐城废县址进行了考证,其中有“今璧山、永州、江津,皆当是故乐城县地”的记载。按,“永州”当作“永川”。柳宗元《捕蛇者说》开篇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这个永州在湖南南部,今为湖南省辖地级市,而前“璧山”、后“江津”今皆为重庆市辖区。永州距离璧山约870公里,距离江津约843公里,显然故乐城县地不可能覆盖如此大的区域。而与“永州”形近的“永川”,今恰为重庆市辖区,距离璧山约53公里,距离江津约65公里,三个地区的地理位置连线呈三角形,符合县地的要求。
四、水精字与水精子
本书卷二《汉中志》二注2中,任乃强先生对从西域传进中原的14种珍贵特产进行了解释。其中提到,“昔人妄谓雪山坚冰所化,故或作‘水精字’”。这个“水精字”是什么呢?明代曹昭、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论》里说:“古语云千年冰化为水晶,其性坚而脆,刀刮不动,色白如泉,清明而莹,无丝毫瑕玷击痕者为佳。”两处说法一对比,似乎“水精字”就是“水晶”。那么,“精”“晶”二字可以通用吗?答案是肯定的,依据就是《康熙字典》辰集上“日部”的两则引文:一为《通雅》曰“古精、晶通”,二为《读书通》曰“水精,即水晶”。
既然“水精”即为“水晶”,那么就可以确定“水精字”的问题了。乾隆皇帝曾作有《水精子》一诗,首句“老冰化石为水精”,即指水晶而言,而这句诗的意思恰与关于水晶的传说一致。据此,“水精字”误,当作“水精子”。
五、於与于
本书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三正文末句为:“自是,守藩供职,自建武至乎中平,垂二百载,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矣。”在“乎”字下,有小字夹注曰:“吴本作於。”
此处涉及《三国志》的版本问题。《三国志》的传世本以百衲本、殿本、金陵活字本、局本为主,中华书局在点校时,不但以这四种版本互校,而且利用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卢弼《三国志集解》及蒋杲、翁同书、吴承仕的诸家之说。任乃强先生所说的“吴本”,即指吴承仕的版本。笔者未见吴本,但按文义,既然本段小字夹注针对的是《公孙述刘二牧志》正文中的“乎”字,按照形近原则,吴本作“于”更合乎任先生的看法。此处很可能是在繁简转换中,直接把“于”改作“於”所致。本文将这一猜想权且提出,敬请读过吴本的读者为笔者解惑。
六、贵築与贵筑
本书卷四《南中志》七注13,任乃强先生考证了且兰国的地理演变,其中有“黄平州西南,贵築县东北,皆故且兰县地”的记载。“贵築”误,当作“贵筑”。“筑”主要有三种释义:1.在作建筑解时,繁体字为“築”,读4声zhù;2.在作乐器解时,旧读2声zhú,繁体字仍为“筑”,如《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所载高渐离击筑即是;3.“筑”还是贵阳的别称,旧读2声zhú,繁体字仍为“筑”。具体到“贵筑”,清代在此置县,因古代贵阳盛产竹子,以制作乐器“筑”而得名“贵筑”。因此“筑”字应不变,作“築”误。
七、李重夔与李朝夔
在本书《前言》的第十部分“校勘述例”中,为方便表述,任乃强先生将《校记》中所举版本,每种只以一个字代替,其中有“函——清乾隆通州李调元刻《函海》本。道光绵州李重夔重镌本同”条。按,“李重夔”误,当作“李朝夔”。在“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中,出身于绵州李氏的李调元赫然在列。李调元是清代“蜀中三子”之一,著述丰富,其中就包括《函海》。《函海》收录有150余种著作,是清代著名的私刻丛书。李调元有四子,李朝础、李朝隆、李朝夔、李朝尧,李朝夔为其第三子。《函海》现存最常见的版本有两个,一为嘉庆十四年李鼎元重修本,一为道光五年李朝夔增补本。
八、处(處)与虞
本书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论》二注3论及“李、处、陆、杨四家书”,“处”(處)为“虞”之误。其一是不知“李、虞、陆、杨四家书”之意,其二是“处”的繁体字“處”与“虞”形近。“李、虞、陆、杨四家书”,指为扬雄《太玄》做注的四人及其作品,他们分别是三国蜀李譔(四川绵阳人,著名经学家)的《太玄指归》、三国吴虞翻(浙江宁波人,曾任骑都尉)的《太玄注》、三国吴陆凯(江苏苏州人,吴国重臣)的《太玄注》以及西晋杨泉(河南睢阳人,哲学家)的《太玄经》。
九、《益郡耆旧传》《益都耆旧传》与《益部耆旧传》
本书卷四《南中志》二正文“霸为中郎将”后有小字夹注,对何霸其人进行了考证。其中两引常璩《益部耆旧传》,第一处作“《益郡耆旧传》”,第二处作“《益都耆旧传》”,皆误。此处的问题,一是知识性错误,不知道常璩所写为《益部耆旧传》;二是录入不严谨,前后间隔仅有一行字,却出现了两种错法,殊为不当。
十、纪年错误
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存在大量纪年有误现象。如卷一《巴志》四注3,将《左传》昭公十三年注为公元前577年,应为公元前529年;卷二《汉中志》一注2,将《春秋》哀公十八年注为公元前476年,应为公元前477年;卷四《南中志》十五注3,将宝鼎元年注为公元268年,应为公元266年,等等。
十一、卷次错误
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存在大量引用卷次有误的现象。如李郃、李固父子,《后汉书》卷八十二上、卷六十三并有传,任先生作卷一百十二与卷九十三(见卷二《汉中志》二注5);任文公,《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有传,任先生作卷七十二(见卷三《蜀志》三注12);赵典,《后汉书》卷二十七有传,任先生作卷五十七(见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论》二注13);张俊,《后汉书》卷四十五有传,任先生作卷七十五(见卷十下《汉中士女》十三注3),等等。由于此现象的普遍性,推测任乃强先生所据底本与当前通行本不同,但先生所据具体是哪一版本,尚待进一步考证。
十二、引文错误
此种情况也比较常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由手稿进行电子化时,个别字辨认不清;二是任先生所据底本与通行本不同。如卷一《巴志》三注2引《史记》言黄帝“治五气,艺五种”,“藝”(艺的繁体)当作“蓺”;同卷《巴志》五注7引《晋书·乐志》言《巴渝舞》“粲问巴渝帅李管、种王歌曲意”,“王”当作“玉”;卷二《汉中志》十二注3引《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莋都最大”,“莋”当作“筰”,等等。通观全书,引文类错误在200处以上。
有关该书的问题还有很多,但不可否认,该书难度大、学术价值高,其问世居功至伟,瑕不掩瑜。
作者:巴蜀书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