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超越开生面 八方来风任我行
作者: 张志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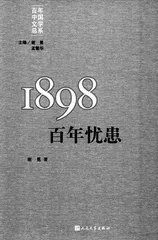
重读谢冕的《1898:百年忧患》,它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浓重的苦涩与忧伤。
谢冕出生于1932年,在近一个世纪中饱经沧桑:自小家境贫寒,几度濒临失学的危难;亲历日军占领福州的苦难时光,被迫做过为日军修机场的童工;投身过解放大军直捣东南沿海的滚滚洪流,在海岛前哨执戈待旦以卫社稷;亲历过马寅初校长在北京大学大饭堂发表新年贺词,彻夜狂欢,歌舞翩翩;曾经在特殊时期屡经波折,三遭落难。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浪潮初起,文化界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溃败,金钱和世俗化的诱惑导引文学走向媚俗化和粗鄙化。凡此种种,萃集一心,思往追昔,如谢冕所言,世纪末的衰老夕阳正在播洒余晖,告别这充满忧患与动荡的世纪百年。但是,正如忧患元元中走过的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谢冕拒绝沉沦,拒绝妥协,生命岁月已逾越一个甲子,仍然元气满满,意气纵横,率先作则,写出《1898:百年忧患》这部篇幅有限却意味深长的学术力作,为时代立证,为文坛立心。岂不壮哉!
人生识字忧患始,忧愤深广今胜昔
鲁迅曾经说过,在积弊重重、保守僵化的传统中国,即便是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忧患”二字,本土自生,从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到苏轼的“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怳令人愁”,鲁迅移用前人评价杜甫的“忧愤深广”一语彰显其《狂人日记》与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差异所在,直到叶剑英元帅的诗作,“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经过历史时空的层层累积,成为中国文化人一个深厚的心理情结。岳阳楼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种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是写文章就可以挥洒张扬的,它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界面拓展中一个小小的关节。《1998:百年忧患》的内在张力,是时隔近三十年之后,仍然可以感受到的强烈情绪。2024年,先生已届九十三岁高龄,他的人生与百年中国重合,但忧患依然,沉重依然:
我几乎也是在沉重的思考中,含着泪光写下《1898:百年忧患》中的每一个字。
百年忧患,强国新民,于是成为我求学治学永远的母题。
风雨人生,何止只做一件事
《1898:百年忧患》在谢冕的学术论著中,从诸多方面来说,都是个罕见的例外,是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多重跨越。
首先是文学疆域的越界击球。
谢冕以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见长,并且宣称“一生只做一件事”。2018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等举办“一生只做一件事:谢冕与中国百年新诗——《中国新诗史略》新书发布会”,在精心设计的青春盎然的葱绿色基调的会场氛围中,更是把这个口号推进到与会的诸多学者和各家媒体面前。谢冕对郭沫若、艾青、蔡其矫、海子、牛汉等诗歌大家,充满推戴之情,他对于北岛、舒婷等朦胧诗人的大力举荐,为之争得崇高的诗歌地位,这都是文坛佳话,诗史丰碑。
《1898:百年忧患》却是一个新的学术视野的开拓新创,是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近代文学融合打通的勃勃雄心。1898年是本书的着力点,谢冕的眼光还往往投射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将龚自珍、林则徐忧国忧民的行迹与诗文,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与文学的前奏。
近代中国社会的危机和动荡,是近代中国文学忧患的源头。鸦片战争翻开了中国近代史最悲凉的一页,同样,也翻开了中国近代文学史最悲凉的一页。从1840年开始,中国的上空始终为浓重的阴云所笼罩,悲凉的袭击使中国染上了感时伤世的心理承袭。
要是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色调是感伤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作为感伤文学的根源,却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的屈辱和苦难。……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压根儿就处在这种挥之不去的集体性的悲怆氛围之中。它的滋生,它的成长,它的发展,均得到世纪苦难的恩泽。
这不仅是谢冕学术领域的一大跨越,而且是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的崭露。在现有的文学史格局中,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文学,似乎就是一截“盲肠”,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记得我读大学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它是被归并在古代文学课程中的,但是任课老师似乎没有多大兴趣讲授之,学生亦不以为憾。毕竟,数千年文学史值得讲授的大家名作实在是太多了。现代文学从陈独秀力倡“文学革命”讲起,奇峰突起,不计前缘。即便是鲁迅先生提出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但要真正去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浮光掠影之作,还真的要有很大耐力。
从历史阶段而言,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是一个完整的阶段,《1898:百年忧患》则是对这样一个长时段文学史的积极而有效的探索。它的历史语境就是中国式现代性的大时代转型。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历史的三峡”的命题,这也许是两个高远超迈的心灵暗中相通的一点灵犀: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进入曲折动荡的“历史三峡”,开始了缓慢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多少精英参与其间,汇入这股波涛汹涌的历史大潮。他们摇旗呐喊,蜂拥争先,浪卷船翻,惊险莫名。他们言忠信、行笃敬,默默耕耘,把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慢慢地推向现代化。唐德刚指出,中国的历史转型,从秦到汉约二百年,实现了从封建向帝制的转型,要实现从帝制到民治,实现现代转型,从1840年算起,也需要二百年。这也是关心历史、政治与文化者所需要借鉴的一个新视角。
文学—文化—政治的多元视野
再一重越界,是从文学到文化和政论的跨越。
先生阅历丰富,饱经沧桑,从中学时代就在对巴金、冰心等作家的阅读中,感知对生活爱恨交织的强烈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巴金教我抗争,冰心教我爱。”从投身军旅起,到20世纪末,谢冕一直在时代的风浪中浮浮沉沉。但是,谢冕自己的学术研究,一向是恪守着文学的边界。即便是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也保持着诗心的纯净。20世纪末的八月中秋,我们在武汉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晚间乘船游览东湖,谢冕倡议众人各写一篇同题散文《清风明月下的东湖》,得到我们的热烈响应。最后形成文字,只有谢冕的文章最为纯粹,眼前景,心中情,超然出尘,完全沉浸在此时此刻的山光水色中。回想四十余年间在谢冕门下行走,促膝相谈的机会多多,但基本保留着两个限度:第一,很少谈论时政,第二,很少说人是非。并非偶然,而是人生经验和处世智慧。
但是,《1898:百年忧患》却是一次空前的“出圈”,跳出文学圈,直接从民族兴亡、时代苦难谈起,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第一章就从颐和园的石舫讲起,一座今人看作是园林景观的建筑物,却是那个时代病症的萃集之所在,为了给慈禧太后祝寿,讨圣上欢心,竟然将原定派作更新海军装备的军费挪作修建颐和园的费用,直接的后果就是甲午海战失败、割让台湾的国耻国难。由此引发出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引发出梁启超、黄遵宪、丘逢甲、刘鹗等仁人志士选择文学和文化的方式,去抒写心中的忧虑,忧国忧民,进而以文字的方式做社会启蒙、唤醒民众的宏大事业。
而且,他们还是从不同的路径走过来的。翻译《天演论》和《原富》的严复,本来是水师学堂出身,从事海军军事教育,曾经多次参加科举而不第。他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参加过新建的北京大学、复旦公学的校务工作,但他最辉煌的人生之笔还是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学术经典,开启民智。刘鹗一直是在从事社会活动,参加过黄河治理并且卓有成效——须知,那可是三年两决口,河南和山东两省饱经水患的时期——他办过实业,行过医,做过洋行买办,开过印刷厂,在庚子之乱后自筹善款到北京赈灾,还以《铁云藏龟》跻身中国第一批甲骨文研究学者之列。他写作《老残游记》本是阴差阳错,半是游戏之笔,半是替友还债,却在晚清小说中拔得头筹,人生的种种失败促成小说的成功。苏曼殊出生于1884年,1898戊戌变法兴起之时,不过十四岁少年,后来呢,许多人把他看作是鸳鸯蝴蝶派的开创者,但是这位通梵文、工诗画、半狂半癫的情僧,同时又是激进的革命者的苏曼殊,却因为诗歌的才情,表现出不同于《红楼梦》式古典爱情的现代感伤,因其对决绝出世与红尘纷扰的矛盾抒写,具有新的情感特征,得到谢冕的青睐。
进一步而言,在1898年这样的历史节点,旧神未死,新神将临,在时代先行者的浪漫想象和路径选择中,具有充分的不确定性,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些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在风气大开中占得先机,率先接受了欧风美雨日流俄潮的冲击,在不同文化的交汇与对冲中激荡起挽救危亡、绝地逢生的豪情,内在的使命感、崇高感以及对光明未来的憧憬,又给他们以强烈的狂喜。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会在流亡离乱中瞩望新中国独立富强的未来,为什么鲁迅会在风雨如磐的沉痛中涌动血荐轩辕的豪情。对于谢冕,这样可以回应我曾经纠结未解的一大困惑:为什么宣称快乐生活每一天,却又写下这悲凉遍被、忧患满纸的《1898:百年忧患》?为什么会对丘逢甲的《春愁》格外青睐,在书中多次引用?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从《诗经》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杜甫《春望》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到《牡丹亭》中的姹紫嫣红都付与断壁残垣,《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中国诗歌传统的伤春悲秋、情景交融、感物伤怀,建构成强烈的春愁情结。丘逢甲的诗作,可谓此类题材的殿军之作。征夫还乡、闺阁春怨,都各有千秋。但是,杜甫和丘逢甲之所以更受人称道,是因为他们在一个传统的话题中注入了更为廓大的意境,在诉说大痛苦的同时,为它所蕴含的巨大的共情力所沉醉。古人云,独乐乐何如众乐乐,同理,如果一个人的悲愁万里,忧通万众,气雄千古,视通万里,它的品格自然不凡,是博大开阔的精神气象的精彩表露,大痛苦之中亦有大欣喜。谢冕对丘逢甲的激赏,就是从中读到了可以作为引领百年忧思的奠基之作。
八方来风,行高致远
谢冕的学术论著成果丰厚,亮点颇多。其中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他的论点和论证,基本上是论从己出,自说自话。记得已故学人古远清讲过一个趣事:90年代他和谢冕都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相关规定要求他们任期内要给学报写一篇学术论文。谢冕提交的论文被认为不合学术规范,因为他的文章中没有一条引文。这显然是胶柱鼓瑟。我可以说是从1979年起,从读到谢冕的《和新中国一起歌唱——建国三十年诗歌创作的简单回顾》起,就被其文风深深吸引,他评论诗歌的文字,华彩蔚然,充满诗性,几乎是在以诗解诗,以强烈的激情去激活、去燃烧他所阐释的诗人诗作,进而激活和燃烧读者的心弦。尤其是做当代诗歌研究,他很少去进行引经据典式的引证。一是当代诗歌研究的当下性,许多时候谢冕就是这些诗作的第一位批评者,没有多少现成的论文可以参考和引证。二是谢冕的学术自信,他看似诙谐潇洒、宽容通达,但持守一个信条,非经深思熟虑,他不会轻易发声,很少有“急就章”,但凡要在会议上发言,一定是事先就准备好文字稿。他的学术论著,论域广阔,你可以批评他的学术观点和评价尺度,但你无法指责他对所论述的作家、诗人长篇短制的评论是隔靴搔痒、草率命笔的。
记得2002年,我们一帮弟子为谢冕庆祝七十岁寿辰,餐前有个小型的学术座谈会,弟子们以各自的切身感受表达师从谢冕得到的教益,大家都很动感情,直抒胸臆,即兴而言,唯有谢冕在致答辞时掏出一篇精心准备的发言稿。这让我们再一次受到言传身教。记得老孟(孟繁华)讲,从此以后,他就一定是写好了发言稿再去参加作品研讨会的。
《1898:百年忧患》却是一个反证。其中许多论述,都有引证,有的是史料的出处,有的是他人的观点。在重述19世纪中后期的历史悲情时,被谢冕引证的有翁同龢、丁韪良、康有为、梁启超等历史现场亲历者的记事,有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对谭嗣同的评价,有张灏在《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五章中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与戊戌变法兴起的逻辑关系的梳理。第三章是黄遵宪的专论,论人论诗,谢冕当行,按理说处理起来不是很困难,但是谢冕非常严谨地引用了康有为、梁启超、高旭、徐世昌、胡适、胡先骕、钱仲联等名士闻人对黄遵宪的高度褒扬,加重了作品的历史感,浓墨重彩地充实了本章的雄辩力量。
更进一步地,《1898:百年忧患》全书的一些重要论点,也约略地看出其所借助的一些理论资源。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论断,可能是受到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某些启发;启蒙与救亡的论题,显然来自李泽厚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宏论;对于现代印刷术、现代报刊与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共生关系之论述,也许与90年代的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等有所关联。关于戊戌变法中产生文化巨人的言说,转用恩格斯对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群落的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