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日记》中的学术和学人
作者: 段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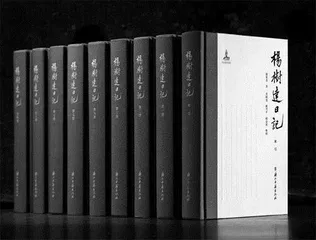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后取《荀子》“积微成著”之义,以“积微”二字“名其居”。杨树达是湖南长沙人,语言文字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一生勤于治学,成就斐然。史学家陈寅恪赞誉杨树达:“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杨树达)为第一人。”202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9卷本《杨树达日记》(最后一卷为索引,颇便检索),共计300余万字。其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1907年至1908年的留日日记,第二部分为1920年至1956年的《旅京日记》《旅平日记》与《积微居日记》。此次出版的《杨树达日记》,全方位呈现了杨树达近40年的学思历程、社会交往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是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社会和时代变迁的一部珍贵文献。
杨树达一生跨越了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历史时期。其童年时代先后就读于长沙时务学堂、求实书院,后又曾在日本留学数年。归国之后,他长期任教于湖南第一、第四师范和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1955年6月毛泽东返湘之时,言及昔日在湖南第四师范就读时,曾旁听杨树达授课。此次出版的《杨树达日记》的整体内容,以杨氏的读书札记和学术交往为主,其中不乏论学评人的文字,最能感受贯穿杨树达一生的学人本色。一般而言,个人日记属于典型的“私人文字”,但从杨树达根据其日记编订而成的《积微翁回忆录》可知,其生前有着将日记公开“示人”的用意。因此,阅读这部卷帙浩繁的《杨树达日记》,或许更需要关注《杨树达日记》里的“私房话”与其公开言行之间的互补关系。同时,读者若能取张舜徽《壮议轩日记》《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桥川时雄《民国时期的学术界》等时人记录和《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杨树达先生之后的杨家》等著述相互参阅印证,当更能深入全面地了解《杨树达日记》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味。
《杨树达日记》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晚清民初学术转型的历史状况。从日记中可以看到,杨树达早年学习新学,但立下的却是“有志于训诂之学”的学术志向。他后来虽留学日本,然而就其一生治学的方法论而言,基本仍是偏于旧式。因此,杨树达自陈,“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的影响”。同时,他也坦陈“生平服膺高邮王氏,治学方法与清代大师相合”,并自信地说:“余学力愧不逮前人,然于文字之学却有独创突过前人处也。”(1952年2月3日日记)在20世纪初期现代学术日趋专业化的背景之下,从杨树达的著述(如《汉书补注补正》《词诠》《马氏文通刊误》《中国修辞学》《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可知,他已经表现出相当清晰的“专家”取向。在日记中,杨树达也乐于从音韵训诂的专业角度,评价当时的学术与学人。比如,他认为自己的治学取向与沈兼士接近,因为“国人于文字学偏治音韵,而兼士独治义诂。治义者海内止余与兼士而已”(《积微翁回忆录》,1947年8月4日)。他对于湖南学人曾星笠的评价甚高,认为“湘中学者承东汉许、郑之绪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来星笠一人而已”。而在“新文化”人物当中,在他眼中,陈独秀比胡适学养更佳,是因其“小学”功底更深。
从《杨树达日记》中不难看到,杨树达之所以成为20世纪的一代大家,与他身处的那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氛围密不可分。诚如钱穆所言,20世纪20—30年代,正是现代学术共同体(现代大学制度、学术社团、学术期刊、学术规范等)在中国初步形成并开始与国际接轨的时期。正是在1920年至1937年,杨树达任教于北京的多所著名高校,得天时地利与人和,其学术研究也在此期间突飞猛进。当年在京求学的湖南人张舜徽回忆,那时自己身边“以专门名家者,经学则有吴承仕;文字训诂则有沈兼士;音韵则有钱玄同;史学则有陈垣、邓之诚;诸子则有孙人和;金石则有马衡;文辞则有高步瀛”。同时,“吾湘前辈若杨树达、黎锦熙、骆鸿凯诸先生,咸任教各大学,舜徽以同乡后进,时往请教,往来尤密”。居京学界同行与前辈以及湘籍学人,也共同构成了杨树达在北京的“朋友圈”与学术网络。他们的名字也在《杨树达日记》中频频出现:梁启超、郭沫若、陈寅恪、钱玄同、胡适、黎锦熙、李肖聃、骆鸿凯、马宗霍、孙楷第、吴承仕、余嘉锡、曾星笠、谭戒甫、王啸苏、周秉钧、周德伟等。
在如此优质的学术环境之中,学术交往与同行评议显得尤为重要。当时,杨树达“交友求益之意颇殷”。然而,在他眼中,“湘人居京者,无一真读书人”,唯独“朴诚无华”的湖南常德人余嘉锡(季豫)是其心目中真正的“学人”(1929年7月3日日记)。余嘉锡后来成为辅仁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以精研目录学闻名于世,可见当日杨树达眼光不凡。与此同时,随着现代学术体制的日益确立,在传统的地方学术取向与现代国家学术体制之间、学人的自我期许与他人评价之间的碰撞也开始日益凸显。在《杨树达日记》当中,这种“公论”与“私议”之间的思想张力,主要表现为他对于时人关于“湘学”认知的评价、对于当日大学学风的记述,以及他与部分学人私人关系的暴露。日记中的这些细节既丰富了今人对于民国学术界的理解,也折射出民国学人思想的复杂与多歧。
从《积微翁回忆录》以及《杨树达日记》可知,其时部分浙派学人对于“湘学”其实颇有苛评。张孟劬(尔田)曾评论:“湘中学者自为风气,魏默深不免芜杂,王益梧未能尽除乡气。”章太炎的弟子吴承仕则讥讽,“湘人言经者多不明训诂,于音理尤茫然”。老师一辈的章太炎也认为,湘人不通小学,称“大抵湘中经学亦杂沓,然有一事则为诸家之病,盖于江、戴、段、孔古音之学实未得分毫也,偶一举及,其疵病立见矣”。章氏甚至视湘学为“矿区”,认为湖南人无力“开采”,只有等浙江人“开采而后可用也”。面对学界的这类讥评,张舜徽曾愤然表态:“湖南人之矿,终待湖南人发掘之。”杨树达也与曾星笠相约,定要“雪太炎所言之耻”。加之20世纪30年代,北平教育界多为“浙派盘踞把持,不重视学术”,社会评价不佳。日记中涉及“浙派”人物(如朱希祖、马裕藻等人)的不端之处,杨树达亦不遗余力予以抨击。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家陈垣(援庵)与杨树达对于当日教育界的某些看法颇为一致。因此,杨树达写道:“于此知天下自有真是非,宵小之徒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也。”
虽然部分学界人士对于湘学屡有苛评,也引发了湘籍学人的不满,但这些浙派学人对于杨树达的学术评价甚高。张孟劬(尔田)认为:“两君(杨树达、余嘉锡)造诣之美,不类湘学。”钱玄同的评论更具体:“君(指杨树达)治学语必有证,不如湖南前辈之所为,而做人则完全湖南风度也。劭西(黎锦熙)做人尽脱湖南气,而为文字喜作大言,全是湖南派头也。”有趣的是,对于湘籍学人的治学水准,“不类湘学”竟是外人心目中佳评,不知身为湘人的杨树达听闻之后作何感想?细品钱玄同的表述,所谓“湖南风度”(“湖南气”)或指湖南人性格中的率直洒脱,所谓“湖南派头”则似指湘人的治学风格偏于浮泛。钱玄同等浙籍学人恣意评价“湖南前辈”的态度,也透露出其心目中浙学压过湘学的自负。此外,钱玄同径直以“湖南派头”“湖南风度”等熟语评点湘籍学人,可见在其他地域学人的舆论场中,似对于湘学湘人早有定见——杨树达、黎锦熙不过是钱玄同印证其心中定见的两则个案而已。值得注意的是,浙籍学人在当日学界的影响力不可低估。作为学界前辈兼领军人物,章太炎甚为看重杨树达,杨树达也一度欲从太炎治学。章太炎曾称:“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寥寥数语,让杨树达听后,感觉“得宗匠一人之褒,信念益增”。(1932年4月3日日记)
值得注意的是,两造之外其余学人的评价,或许更为客观公允地表现出杨树达的学术成就。陈垣在读过杨树达《读王氏读书杂志献疑》一文后,认为“精核之至”,称“湘士多材,君(杨树达)今又继二王而起矣”。文字学家黄侃则表彰,“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余嘉锡)、杨(杨树达)二君皆不愧为教授。其他则不敢知也。遇夫于《汉书》有发疑正读之功,文章不及葵园(王先谦),而学问过之。《汉书补注》若成于遇夫之手,必当突过葵园也”。陈寅恪也说:“湖南前辈多业《汉书》,而君(杨树达)所得独多,过于前辈矣。”杨树达在日记与回忆录当中,对这些评价均予以详细记载,从中可见身处学术舞台的杨树达,相当敏感于学界同人对于自己的评价。日记中的这些记录,或可视为杨树达“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内心渴望,也可看作他对于自身工作的一种内在激励。他写道:“余于《汉书》治之颇勤,亦稍有自信……足见真实之业自有真赏音,益喜吾道之不孤。”
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杨树达在北京任教达十七年。根据杨树达后人杨逢彬的概括,这一时期杨树达的学术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是1930年之前,以汉语语法研究为主;后一阶段是1930年之后,侧重于训诂学、文字学、语源学的研究,还兼及修辞学、古文献学及考古学。在京十余年,也是杨树达一生中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平均每年出版一部著作。不过,从《杨树达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清华大学内部的人事纠葛颇为复杂。这也让杨树达深感不适与不安,最终他做出回湘任教的决定,由此开启了他人生“下半场”的历程。
《杨树达日记》从其本人的立场与视角,对于这一曲折经过与心路历程留下了相当详细的记述。1932年5月11日,杨树达给系主任刘文典(叔雅)写信,表明下半年不愿再接受清华的聘任。而刘叔雅来信则称,学校不许辞职,但休假不成问题。“此次当教授皆续聘三年,希望假满后仍回学校任教云云。”5月22日,文学院长冯友兰访杨树达,谈到他给刘文典的信,劝他打消辞职的念头。杨树达回答:“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冯听后,“唯唯而退”。
这是杨树达后来在《积微居回忆录》当中的公开记述,而在《杨树达日记》里,他对于主持此事的冯友兰、刘文典,当时即未尝假以辞色。杨树达写道:“此人(冯友兰)狡猾,已拟暗中与余为难,及见为公论所不许,乃又掉头转向,欲见好于余耳。”(1932年5月22日日记)在第二天的日记里,杨树达对于此事的描述与评价着墨更多,细节描摹之处,更见杨树达对于冯、刘二人的鄙视:“此次冯芝生(冯友兰)立意与余为难,叔雅颇亦附和。”他转引来自友人的信息,称“叔雅得余信后,即持示芝生,芝生云此甚好,即不必留,改为讲师可也”。后来,友人问刘叔雅:“遇夫(杨树达)信作复否?”叔雅云:“既已辞,无庸作复。”主事者两面三刀的态度,的确让杨树达寒心。他在日记中写到,近日两人之所以“改换面目,忽表殷勤”,是因为“梅月涵(梅贻琦)校长能持大体,对余极表好意之所致耳”。(1932年5月23日日记)
梅贻琦校长表态之后,当事人的态度似乎也为之一变。1934年10月的一天,杨树达由清华大学入城,车中恰遇刘叔雅。他“忽谓余云:‘我对于遇夫先生钦佩之至。’余颇讶其语唐突无因,则言:‘吾辈旧友,何为如此客气?’渠乃云:‘近读《学报》大著,实属钦佩之至。不佩服者,王八蛋也!’乃知其为近著而发,却又无可置答”。杨树达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其语出人意外,错愕不知所答。在彼或出于至诚,而其态度之神妙,又不能不让人大吃一惊矣。”经历此“神妙”之事与“神妙”之言,杨树达对于前倨后恭的刘叔雅只能敬而远之:“此君最宜不相见,相见则苦楚殊甚,此后当设法避之耳。”(1934年10月22日日记)
杨树达曾坦承自己“性不喜谈政治”,但话锋一转,又指出“人在社会,决不能与政治绝缘”。在1920年前后,三十来岁的杨树达亦曾积极参与长沙健学会,响应新潮;在湖南“驱张(张敬尧)运动”期间,他作为代表入京请愿。凡此种种,皆尽显其儒者形象之外另有的“金刚怒目”一面。《杨树达日记》当中相当丰富的涉及政治人物和政治运动的观察与评论,足以让读者一窥20世纪激变时代之中,政治权力与读书人之间的力量博弈。翻读《杨树达日记》,最令人感佩之处,乃是无论时代风云如何诡谲翻覆,杨树达终其一生都保持着纯粹、简朴、自律的读书人生活,心无旁骛且自得其乐。1949年10月4日,正是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刻。那一天,杨树达的生活依然被持之以恒的阅读、思考和写作所环绕:“晨阅《仪礼正义》讫,续阅《乡饮酒礼》。饭后小寝。到侯哲葊处还书。读《朱子读书法》。晚出席新知学会,听罗仲言讲马列主义之发展,九时归寝。”或许正是这种执着淡泊、宁静致远的学人心性,成就了“一代儒宗”和“汉圣”的杨树达,也奠定了“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陈寅恪语)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