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翁婿”到“舅甥”的唐蕃关系
作者: 卢芷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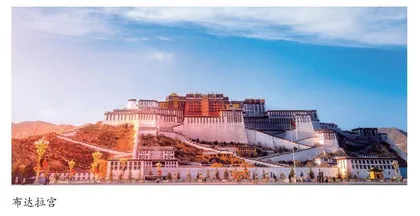
从文成公主入藏至金城公主嫁入吐蕃,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由“翁婿”向“舅甥”的演变。这种称谓上的转变不仅反映了双方亲属关系的变化,还受到了文化习惯及政治理念变迁的影响。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分别于641年和710年远嫁吐蕃,而首次正式提及唐皇室与吐蕃王室之间的舅甥关系,则发生在金城公主出嫁前后。尽管一般认为,随着文成公主的联姻,唐蕃舅甥关系即已形成;但实际上,直到金城公主出嫁之后,这一身份才在唐蕃的互动中被更加明确地强调。
从“翁婿”到“舅甥”
文成公主入藏后,唐太宗伐辽东还,松赞干布遣禄东赞奉贺表曰:“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
在这份贺表里,松赞干布自称为唐太宗的“子婿”。护雅夫指出,在隋唐时期,当皇帝将公主许配给少数民族政权的领袖时,两者间的关系往往被描绘为“舅婿”或“府君、驸马”。山口瑞凤依据这些历史记录进一步佐证了护雅夫的观点,强调松赞干布使用的是“婿”的称呼而非“甥”,表明“舅甥”这一术语并不适用于描述岳父与女婿之间的关系。
开元二年(714年)秋,吐蕃的将领坌达延与乞力徐率军侵犯临洮,并进一步对兰、渭等州发起了攻势,在掠夺了大量牲畜后撤离。面对这一局势,唐玄宗令摄左羽林将军薛讷及太仆少卿王晙领军迎战,颁布了亲征诏书,其曰:“……小蕃远寇,假息游魂,爰自昔年,慕我朝化,申以婚姻之好,结为舅甥之国。……”
由此开始的一系列军事冲突均以吐蕃失利告终。至开元四年(716年)八月,吐蕃请和,唐玄宗同意,并向金城公主及其夫君赞普赠送了锦帛与器物等礼物作为赏赐。随后,金城公主呈上了谢恩表:“仲夏盛热,伏惟皇帝兄起居万福,御膳胜常。奴奴奉见舅甥平章书,云还依旧日,重为和好。……”
开元六年(718年)十一月,吐蕃遣使奉表曰:“仲冬极寒,伏惟皇帝舅万福。……当令望重立盟誓,舅甥各亲署盟书,宰相依旧作誓,彼此相信,亦长安稳。……”
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在官方文书中首次正式确认了唐朝与吐蕃之间的舅甥关系。自此以后,在双方的官方交流中,这种亲属称谓频繁出现。唐蕃关系从“翁婿”关系转而表述为“舅甥”关系。林冠群先生指出,“舅甥”这一表述不仅体现了唐蕃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而且反映双方关系从世代联姻发展至更广泛的政治联系。
唐蕃对彼此舅甥关系的强调与追溯
唐蕃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翁婿”逐渐演变为“舅甥”,这一变化背后既有语言习惯的作用,也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
对于“舅甥”这一关系,《尔雅》记载:“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同时提到“谓我舅者,吾谓之甥”,并引用了尧舜之间的关系作为例子。《孟子》记载:“舜尚见帝,帝馆甥于二室,亦飨舜。”东汉赵歧注:“尧以女妻舜,故谓之甥。”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将“婿”称为“甥”的说法已经存在。那么,在唐太宗与松赞干布交往期间,唐朝与吐蕃之间为何没有采用这种称呼方式呢?这可能基于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从汉语文献来看,“舅”与“甥”的原始含义并不直接指向现代意义上的岳父与女婿关系。依据芮逸夫的研究成果,“舅”的称呼在古时可以用来指代母亲的兄弟、妻子的父亲或是丈夫的父亲。而“甥”可以用来表示姐妹之子、女儿的配偶、女儿的儿子、姑母的儿子、舅舅的儿子、妻家的兄弟或姐妹的配偶。值得注意的是,“甥”有时也被写作“生”或者“出”,特别是当它被用来指称姐妹的孩子时,这一用法与指代母亲的兄弟的“舅”形成了一种对称关系。“舅甥”的原始意义实际上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舅舅与外甥”概念相吻合。
其次,唐朝早期较少用“舅甥”来指代“翁婿”。根据《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在贞观十四年(640年),当修礼官讨论丧服制度时,唐太宗指出:“……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纪有殊,理为未得。”侍中魏征和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对此回应道:“然舅之与姨,虽为同气,论情度义,先后实殊。”此外,《尔雅》对“妻之姊妹,同出为姨”也有解释。从唐太宗提到的“舅姨亲疏相似”以及魏征、令狐德棻所强调的“舅姨同气”来看,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舅”主要指的是与“姨”类似的角色——即妻子的兄弟和母亲的兄弟。
此外,藏文术语“dbon zhang(甥舅)”与“翁婿”的含义并非互相对应。这一点从唐蕃会盟碑正面左侧所刻的汉文碑文中可以得到证实:“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圣神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
正面右侧藏文碑文载:“(1)//bod gyi rgyal po chen po(2)'phrul gyI lha btsan po dang//(3)rgyal'I rgyal po chen po rgya rje hwang te(4)dbon zhang gnyIs//chab srid……”
碑文中采用藏文“dbon zhang”来对应汉文中的“舅甥”。关于藏文“dbon”的解释,林冠群先生指出,“dbon po”是“tsab po”的一种尊称形式,其基本含义涵盖了孙子、侄子、外甥或是父亲的兄弟(即叔伯),但似乎并不直接指代女婿这一角色。唐玄宗时期,唐蕃之间的所谓“舅甥”关系实际上反映的是妻舅与妹夫之间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藏语中的“zhang”确实包含了“妻舅”的意思,“dbon”却没有“妹夫”这层意思。在李唐王朝的文化背景下,当提到“舅甥”时,它同时涵盖了“妻舅”与“妹夫”两个概念。基于此,吐蕃王室按照唐朝的习惯称呼玄宗为“zhang”(即妻舅),自称为“dbon”(即外甥)。然而,在唐太宗统治期间,双方尚未建立起这种特定的关系称谓,因此那时的吐蕃没有必要遵循唐朝的传统自称“甥”。此外,吐蕃文化里也没有将女婿称为“dbon”的习惯,故松赞干布自称为“壻”而非“甥”。
根据现存的史料,唐朝首先提出了与吐蕃之间的舅甥关系。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当唐朝使者崔汉衡访问吐蕃时,论悉诺逻对崔汉衡说:“……其盟约,请以景龙二年(708年)敕书云:唐使到彼,外甥先与盟誓;蕃使到此,阿舅亦亲与盟。……”林冠群先生指出,这份诏书反映了早在景龙二年,唐中宗与吐蕃赞普之间就已经相互称呼为“阿舅”和“外甥”,但当时并未明确使用“舅甥关系”的术语来描述这种联系。而《册府元龟》所载唐玄宗亲征诏书,表明他对强调唐蕃间舅甥关系的态度是十分肯定的。制书云:“……小蕃远寇,假息游魂,爰自昔年,慕我朝化,申以婚姻之好,结为甥舅之国。……鸿恩大造,特加於蛮貊,狼子野心,遂同於枭獍。……”
唐玄宗下亲征诏的背景是,吐蕃于开元二年侵犯唐朝边境,从而打破了长久以来唐蕃之间维持的和平状态。《资治通鉴》记载:“初,鄯州都督杨矩以九曲之地与吐蕃,其地肥饶,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
开元元年(713年),九曲地区正式纳入吐蕃版图,为吐蕃提供了培养军事力量的有利条件。由于该区域紧邻唐朝边界,位于青海一带,吐蕃因此占据了战略上的优势,得以频繁袭扰唐朝边境。唐玄宗继位后,急需通过行动来巩固其统治地位与威望,在此背景下,提及双方之间的舅甥关系,则成为师出之名。
唐蕃之间的舅甥关系不仅是亲属关系,更是政治关系。先秦典籍《周礼》记载:“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
东汉郑玄注:“异姓,王婚姻甥舅。”《尚书》载:“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无替厥服。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
唐朝孔颖达正义:“昭德之致,正谓赐异姓诸侯,令其见此远物,服德畏威,无废其贡献常识也。”唐玄宗称吐蕃为“甥舅之国”,出自先秦典籍之表述。唐蕃为舅甥关系,但吐蕃不仅没有“服德畏威”,反而入寇唐境,显露其“狼子野心”。唐玄宗提及与吐蕃的舅甥关系,目的是谴责吐蕃不顾恩义,如此则亲征有名。
此后,吐蕃频繁提及并回顾其与唐朝之间的舅甥关系。开元十八年(730年),赤岭会盟前,吐蕃赞普墀德祖赞献书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
吐蕃提到,在金城公主下嫁之前,赞普已经与“先皇帝舅”建立了姻亲关系。在此之前,仅有文成公主远嫁至吐蕃,这番言论实际上是将唐蕃之间的亲属关系追溯到文成公主入藏。
针对吐蕃与唐朝之间的舅甥关系所体现的政治意图,林冠群先生指出,这种亲属联系实际上成为调节双方冲突与和平状态的一种策略。当吐蕃遭遇军事挫折或未能达成既定目标时,便强调这种特殊的亲戚纽带向李唐王朝展示其寻求和解的诚意。其之所以能够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唐蕃曾建立友好联系。据《旧唐书》记载,文成公主入藏后,吐蕃派遣了贵族子弟赴大唐学习《诗》《书》。年轻一代尤其是那些后来成为吐蕃重臣的子弟,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后,对唐蕃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自那时起,随着对儒家思想的深入学习,吐蕃在理政方面开始受到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唐玄宗提到这一层亲属联系后,吐蕃便效仿唐朝的做法,将舅甥之谊作为促进双边交流的一个重要理由并加以利用。
总体来看,唐朝与吐蕃之间的舅甥关系实质上是在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时确立的。到了唐玄宗统治时期,这一关系被进一步强调,用作支持唐玄宗亲自领兵对抗吐蕃行动的正当理由。自此之后,深受中原儒家治理思想影响的吐蕃高层官员开始频繁地运用这种亲属关系来调节唐蕃关系。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 民族与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