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妆容艺术
作者: 孙苏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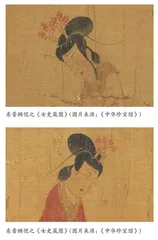
妆容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审美观念,还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息息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高度活跃,各民族交流融合。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该时期的妆容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风格,为中国古代妆容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魏晋南北朝时期妆容风格
白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流面妆。画法是用铅粉敷面,能使面部肌肤呈现出理想的白皙效果。由于玄学盛行,而白皙的皮肤令人有空灵飘逸的气质,所以当时人们大多崇尚白皙的肤色。同时,上层社会也推崇白皙的肌肤,贵族女性最先开始画白妆,民间百姓纷纷效仿,使得白妆在民间迅速流行开来。
额黄妆也属于当时的流行面妆。画法是用黄色颜料涂抹在额头。额黄妆的形状多样,种类有半月形、花朵形、云纹形、如意形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寺庙壁画中的佛像面部大多用金色来装饰,由此启发了人们绘制额黄妆。额黄妆的制作方式通常分为染画法和粘贴法。染画法是指用黄色颜料直接涂在额头上。所用的黄色颜料分为植物颜料和矿物颜料两种。粘贴法则是先把要用到的薄片类材料染成黄色,再剪成特定的形状,最后贴在额头上。因为剪出的纹样丰富多彩,所以又称为“花黄”。北朝民歌《木兰辞》中“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描述的就是这种妆容。
花钿是贴在额头眉间的装饰,起源于南朝,形状多样,色彩丰富,除常见的圆形、菱形、三角形外,还有桃形、蝴蝶形等。其材质丰富,金箔质地的花钿富贵华丽,通过捶打金片制成各种形状,边缘还会加以精细的雕刻。纸制花钿则更为轻便,普通百姓也可使用,通常用彩纸裁剪后染上色彩。螺钿花钿利用了贝壳的天然光泽与色彩,经过打磨、切割后粘贴在额头,别具一格。南朝《美女篇》中“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描绘了女子用黄色颜料画眉模仿月亮形状,用金箔剪成星星形状作为花钿装饰的情景。此外,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也有对花钿妆的描绘。
斜红妆通常在眼尾处用红色胭脂画出一条斜线,延伸到太阳穴,或在眉尾至鬓边位置。形状有月牙形、竖线、曲线、云气等多种样式。颜色常以红、橘色调为主。据说,魏文帝曹丕有个宠姬叫薛夜来。有一次,她不小心撞到了水晶屏风上,受伤的地方看上去像朝霞快要消散的样子。伤好留下疤痕后,曹丕还是很宠爱她。宫女们见状,都纷纷用胭脂模仿,在脸上画类似的痕迹,称作“晓霞妆”,后来“晓霞妆”又演变成了“斜红妆”。
面靥指在女子面部酒窝处,用丹青、朱红等颜料点绘出的各种形状装饰。最常见的是圆形,也有菱形、星形、月牙形、钱形等样式;也有将面靥制作成动植物或几何图案的,如桃花形、蝴蝶形、三角形、方形等。面靥多以红色调为主,除红色系外,也有使用黄色、绿色等颜料绘制面靥的情况。除了使用颜料外,也有把金箔、翠羽等材料裁剪成合适形状后制作面靥的情况。
面靥最开始并不是单纯的装饰,而是宫廷中的特殊标志。宫廷里妃嫔来月事,不能伺候帝王,就会在脸上点个小点作标记。后来这种做法传到民间,成了面部妆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不安定导致文化艺术多样,面靥便流行起来。此时的面靥从简单标记逐渐发展为丰富多样、极具艺术美感的装饰形式,成为当时女性妆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不同阶层的女性在面靥的呈现方式上也各有不同,这种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社会阶层的差异与文化的交流融合。
紫妆即用紫色的粉涂于面部,相传为魏文帝曹丕的宫人段巧笑所创,马缟的《中华古今注》提到“锦衣丝履,作紫粉拂面”。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记载,紫粉制作指把米粉和胡粉按约三比一混合,用葵子汁搅拌成淡紫色。要是颜色浅,就把葵子蒸熟,用生布绞汁再染粉。
紫妆流行或许因色彩互补。紫妆能中和泛黄的皮肤,令肤色更显自然白皙。另外,紫色在古代被视为高贵之色,紫妆的出现也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意识。紫妆可与当时流行的额黄、花钿、面靥等配合,妆容整体可呈现出艳丽、花俏的效果。
半面妆指仅在脸部一侧施妆。化妆的一侧,像常规妆容一样,进行敷粉、描眉、涂胭脂等步骤,打造出精致的面容效果。而未化妆的一侧则保留原本的肌肤状态,两边形成鲜明对比。半面妆突破了传统的对称美,形成强烈的视觉震撼。相传与南朝梁元帝的徐妃有关,《南史·后妃传下·梁元帝徐妃》记载,梁元帝萧绎自幼瞎了一只眼睛,徐妃每次得知梁元帝要来,便精心化半面妆来迎接他,借此讽刺梁元帝独眼,使得梁元帝“每见之必大怒而出”。这一行为既展现了徐妃的个性与对梁元帝的不满,也造就了半面妆这一独特妆容的传说。半面妆也从侧面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气相对开放,女性在妆容和服饰等方面敢于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展现出独特的审美追求。同时,半面妆也是当时女性展现自身身份地位及表达情感的一种特殊方式,她们以独特妆容来抒发内心情绪。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流行的眉毛样式主要分为广眉和长眉。广眉就是把眉毛画得又宽又浓,宽度可以达到3厘米左右,呈现大气、豪放的气质,这种眉妆可能受到了少数民族风俗的影响。长眉就是把眉毛画得细长,可以一直延伸到鬓角,眉毛的长度甚至超过了眼睛,这种眉妆表现出女性温婉秀丽的特质。画长眉的时候,除了要求纤细外,还要注意线条的流畅性,通常使用黛石来勾勒。这种眉妆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审美观念和社会风气密切相关。
除常见的黑色外,绿色、黄色等眉色也颇为流行。就拿绿色眉来说,《中华古今注》记载:“魏宫人好画长眉,令作蛾眉,惊鹄髻。齐王憎妇人画眉,令宫人作白妆黑眉。至后周,又令宫人作黄眉墨妆。”绿色眉色多以石绿为原料,经过研磨、调制后用于画眉。眉色的丰富多变,反映出当时人们在妆容上勇于创新、追求个性的特点,突破了传统眉色的限制,展现出独特的审美情趣。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审美的变化而开始流行樱桃小口。画法是用唇脂把嘴唇描绘成小巧圆润如同樱桃般的形状,一般只在嘴唇中间部位涂抹唇脂,以此方式来突出嘴唇的小巧精致。
当时唇脂颜色丰富,除常见的红色系外,还有紫色、粉色等色系。红色系唇脂又分为鲜艳的大红色、柔和的粉红色等不同色调。这些唇脂可能是把植物染料与动物油脂混合在一起制作而成的。不同颜色的唇脂用于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妆容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各政权为巩固统治,重视文化发展,为妆容文化创新提供了条件。例如,南朝各政权大力发展文化艺术,使得妆容文化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得以创新。同时,民族迁徙与融合加剧。少数民族豪放大气的妆容风格,如宽阔的眉形、鲜艳的色彩运用,对当时的妆容产生了一定影响,促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妆容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如北魏时期,鲜卑族与汉族融合,使鲜卑族的一些妆容元素融入汉族妆容中。
尽管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但局部地区和某些时间段内经济仍有发展。手工业进一步提高了化妆品制作工艺,如在铅粉制作过程中,通过改进提炼技术,使铅粉质地更细腻,色泽更白皙。颜料种类也更加丰富,染色技术的发展使得黄色、绿色等颜料能够大量生产,为额黄妆、绿色眉妆等提供了物质基础。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化妆品的流通,不同地区的妆容风格得以相互传播和借鉴。例如,通过丝绸之路,西域的一些化妆品和妆容风格传入中原地区,丰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妆容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阶层的一些名士开创了玄学思想,借助玄学和清谈,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脱,注重内在气质修养。这种空灵、超凡的思想外化在妆容上,便产生了对白皙肌肤的追求。同时,道教的兴起对当时的妆容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道教的相关元素也被运用到当时的妆容中。此外,佛教艺术中的色彩、造型等元素对妆容产生重要影响。佛像面部的金色装饰启发了额黄妆的出现,佛教壁画中人物面部的描绘方式也影响了当时人们对面妆的审美和绘制技巧。例如,壁画中人物面部线条的柔和处理以及色彩的淡雅运用,影响了女性面妆中对线条和色彩的追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妆容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多样的面妆、眉妆和唇妆样式,为唐、宋等朝代的妆容提供借鉴。唐代的花钿样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花钿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变得更加复杂精美,出现了如宝相花、瑞锦花等多种复杂花型,材质上也增加了珍珠、宝石等。宋代的眉妆在继承前代长眉特点的基础上,又有新变化和创新,如“远山眉”“倒晕眉”等,眉形更加纤细修长,色彩淡雅。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白皙肤色的追求在后世妆容中得以延续,成为中国古代妆容审美中的重要元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丰富妆容也是民族大融合和文化交流的体现。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互鉴碰撞出了各种具有时代特色的妆容。此外,当时的妆容文化还通过丝绸之路等途径传播到别的地区、国家,促进各文化之间的交流。例如,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区的妆容文化就受到了当时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丰富妆容也给绘画、雕塑等领域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例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和《列女古贤图》等,画中女子妆容丰富,反映了艺术创作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同时,雕塑艺术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受到了当时妆容的影响。例如,云冈石窟中的一些造像,其面部妆容体现了当时流行的白妆、长眉等特点,展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特的审美风格。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妆容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独特的风格特点,其妆容的多样化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这一时期妆容特点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后世妆容发展、文化交流融合以及艺术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梳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妆容,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社会风貌与文化内涵,明白妆容文化在历史中的传承变化,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独特视角。
(作者单位:云冈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