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文论观
作者: 穆奕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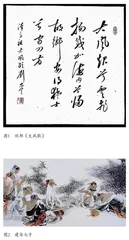
曹丕作为建安时期著名文学家,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理论观。其《典论·论文》一书作于称帝前夕,自问世以来就备受关注,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将文体划分为奏议、书论、铭诔与诗赋四类,并对其创作标准提出了相应要求,“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强调“诗赋欲丽”,将诗赋视为一项独立的文学创作,并为诗赋创作提出了美学评判标准,引领了当时的文坛创作。从此,“丽”成为诗赋创作的重要美学范畴,并在后世被众多文人所继承发扬。
“诗赋欲丽”理论的历史背景
在春秋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与“学在官府”的时代背景下,早期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等人,更注重以口述的方式将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影响众人。他们或广收门徒,或向众人陈述自己的思想,极少著书用文字的方式传播。同时,对于书写文学,他们已经发现了丰富语言表述的可行性,但更注重文学语言的功用,而非文字的创造性使用。在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书写工具的进步,书写文字变得更加轻松,人们开始注重书面文字的编写,由此诞生许多著作。此外,文学的传播方式经历了从古老的口耳相传到更为先进的文字记载的转变。《楚辞》与《诗经》的诞生,为世人呈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文学风貌,它们不仅丰富了文学的内涵,也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和灵感。
两汉时期,经济繁荣为文学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楚辞》的独特魅力催生了赋体文学的诞生,而汉代皇帝对汉赋的重视,推动了文人对诗赋态度的转变,使诗赋逐渐摆脱了过去的束缚,开始独立发展。随着大批文人投身赋体的创作,赋体迅速崛起,成为当时主要的文学创作模式。在这一时期,“诗”与“歌”的界限变得十分明显。通常情况下,“诗”特指《诗经》,其与礼乐教化紧密关联,在国家政策层面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诗经》的功用不断扩大,但是汉代的文人并未养成写诗的习惯。儒生们更倾向于从政治思想的角度解读《诗经》,将其视为表达个人政治观点的文学素材。同时,两汉时期的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将儒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儒学经典被过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变得空前紧密,文学的艺术特性被忽视,文学创作成为文人进入仕途的一种手段。当时的文坛普遍以“风化”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这导致文学无法迎来独立发展的时期,只能沦为儒家经学的附庸。西汉时期,从事诗歌创作的文人寥寥无几,很少有人尝试四言诗、五言诗的创作,韦氏父子是其中的特例。到了东汉时期,书写文学逐渐取代口耳相传的方式,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载体。汉赋也迎来了它的繁荣时期,大批汉赋的创作者开始在语言和形式上对汉赋进行创新。然而,书写文学与汉赋的发展并未掀起诗歌创作的风尚。与此相反,两汉时期歌唱的形式蔚然成风,上至统治者与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习惯于通过音乐来抒发内心的情感。刘邦的《大风歌》(如图1所示)就是在衣锦还乡后即兴抒情歌唱的杰作。直到班固的《咏史》问世,文人墨客才开始尝试创作诗歌。诗歌的创作逐渐与口头歌唱的方式相分离,并入书写文学范畴,并打破政治创作附庸的局限,有了成为一种独立文学样式的可能。
在建安时期,歌唱抒情的口头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文人鲜少以开口歌唱的方式创作。写诗的方式替代歌唱这一形式,与赋一同成为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的主流。曹丕的父亲曹操作为知名的文学家,创作出众多知名的文学作品,他的文风以慷慨豪迈著称。同时,“三曹”麾下聚集了大批文人,他们与“建安七子”(如图2所示)等人,时常聚在一起以诗赋相赠,竞相比较写诗作赋的才华,产出了大批诗赋作品,诗风一时盛行。这样浓厚的文学氛围为曹丕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他本人也养成了以诗赋创作的方式抒发内心情感、抱负的习惯。他随父亲曹操四处征战时,偶有所得便以诗赋的方式抒发情感,并形成独特风格,创作了《淋涡赋》《感物赋》等作品。
诗从两汉时期受经学制约到建安时期大放异彩,从专指《诗经》到成为独立的文学创作方式,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曹丕将诗赋归为一类,并将评价赋体之“丽”用于评价诗,离不开建安时期诗与歌分离后,写诗成为主流文学创作方式的前提。
曹丕提出“诗赋欲丽”理论的原因
当诗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时,创作诗时应遵循的标准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曹丕的“诗赋欲丽”理论,正是在这样的问题导向下提出的。
《墨子》一书对“丽”的概念作出说明:“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其中“丽”最初用来形容衣裳华丽夺目。两汉时期,在汉赋的影响下,“丽”的语义逐渐演变,用于形容汉赋的华丽精巧。汉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扬雄在其文论中多次运用“丽”来评析赋体文学。在评价司马相如的赋时,他提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著名论断。此外,据《汉书》记载,汉宣帝在论及辞赋时也曾以“丽”为标准,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由此可见,以“丽”作为赋体的追求已经成为汉人的共识,也体现出人们对文字之美的追求。这一审美倾向不仅反映了汉代文学创作中对形式美的重视,更折射出当时社会文化对艺术表现力的普遍追求。建安时期,“丽”这一评价用语扩大了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评价赋体,而是更广泛地用于评价文学作品,文人写作时也力求达到“丽”的标准。这一转变标志着文学批评标准的重大突破,从单一的文体评价发展为普适性的文学审美标准。曹丕受此启发,对当时文坛主流审美风向进行总结,提出了“诗赋欲丽”这一标准。
曹丕对诗赋需“丽”这一概念的追求,实则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文化追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汉朝时期,“丽”虽已用于评价赋体,但其背后仍蕴含着极强的政治色彩。那时,人们对诗赋的评价,往往侧重其政治教化功能,而对其美学特征多有规避。至建安时期,政权崩坏,儒学的束缚得以减轻,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丽”这一评价用语逐渐褪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转而具备了更多美学倾向。文人墨客们也纷纷从过去单一追求诗赋的政治教化功用中解脱出来,开始转向追求其“丽”的特质。这种转变,无疑为曹丕“诗赋欲丽”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现实土壤和依据。
建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与动荡的时代。政权的频繁更迭、社会的剧烈动荡以及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人们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中。这种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促使人们深刻反思生命的意义,个人意识逐渐觉醒,人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面对生命的脆弱与短暂,建安诗人们不仅感叹生命的无常,更将这种对生命的深刻认知转化为一种强烈的动力。他们渴望通过建功立业来拯救百姓于水火,同时也希望通过实现自我价值来满足精神上的追求。曹丕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了文学创作可以“立千载之功”,使得“声名自传于后”的观点。他认为,通过文学创作,人们可以实现真正的不朽,超越生命的短暂与脆弱。曹丕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对生命无常和世事变迁的深刻思考。对“文章不朽”的追求不仅提升了文学作品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内心对生命流逝的焦虑。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凸显出形式上的美感对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这一主张不仅是对“文章不朽”理念的深化,更是对创作者个人才能与价值的彰显。之后,追求“诗赋欲丽”成为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风尚。诗人们通过精雕细琢的语言形式,不仅展现了自身的才华,也使他们的作品得以流传后世,实现了声名的不朽。
“诗赋欲丽”理论的影响
曹丕在《典论·论文》(如图3所示)中,尝试将文体划分为四类,并对诗赋一类提出“诗赋欲丽”的审美追求,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汉代“重质轻文”的传统文学观念,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与审美价值,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美学倾向基础。从曹丕开始,中国古代文学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对儒家教化束缚的突破,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从功利向审美自觉迈进,这一转变为魏晋时期主流文学审美追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曹丕将诗赋归为一类,混杂了诗与赋的分别,但“诗赋欲丽”观点的提出,鼓励人们开启追求文学创作形式美的历程。人们将对形式美的追求付诸实践,并不断推进理论研究。西晋时期,陆机在继承曹丕“诗赋欲丽”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文学形式美的内涵,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文学主张,将“丽”的美学追求与情感表达、物象描摹相结合。与此同时,当时秉持文化保守立场的文人群体,对赋体文学铺张扬厉的特质也持肯定态度。南北朝时期,对于诗的审美观点讨论更进一步,文论上取得丰硕的成果。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作出总结,“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大略也。”
曹丕的“诗赋欲丽”主张,作为其文论观的核心内容,不仅是对建安时期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与升华,更是对文学本质与功能的深刻思考。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曹丕通过对文学形式美的追求,赋予了文学以超越生命短暂、实现不朽价值的意义,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